是的,我願意等上一輩子的時間,讓他從從容容把蝴蝶結紮好,用他五歲的手指。孩子你慢慢來,你慢慢來。
——龍應台《孩子,你慢慢來》
父母之愛子,則為之計深遠。
秉持著「不讓孩子輸在起跑線上」的原則,越來越多的中國家庭選擇在中小學就送孩子出國讀書。甚至還有一批孩子,一出生就被帶到了國外,成為土生土長的「外國人」。

在眾多熱門留學國家中,新加坡一向被認為是理想的留學目的地,不但是因為新加坡教育體系完善,教學質量高,為低齡留學生提供優質的雙語教學環境;

更重要的是,美國、加拿大、澳大利亞等歐美國家沒有專門的陪讀簽證,媽媽想去陪孩子一般要搬學生證或是工作證,而新加坡卻可以給陪讀媽媽提供合法的長期居留身份。
根據新加坡移民局規定,來新加坡留學的3-18歲的學生,其媽媽、外婆或奶奶中的一人可以申請陪讀准證,在新加坡合法、長期居留。

所以說,在新加坡陪讀的更多的是媽媽。
其實近年來,隨著低齡留學愈發成為一種趨勢,陪讀媽媽這一特殊群體也隨之逐漸進入人們視野。
電視劇《陪讀媽媽》就將目光聚焦在陪讀媽媽的身上,通過不同家庭的陪讀生活中的歡笑與辛酸相伴,展現孩子留學生活中陪讀媽媽們所遭遇的一系列問題。

藝術來源於生活,而生活,遠遠比藝術更加真實。每一個陪讀媽媽的身上,都有著屬於自己的故事。
在新加坡的陪讀媽媽們,到底過得怎麼樣?
01. 新加坡陪讀媽媽的困境
在新加坡的陪讀媽媽中,有這樣一群媽媽,她們本來在國內有著光鮮的工作或是打拚多年的事業。為了孩子,她們辭去工作,放下事業,告別家鄉,來到新加坡,選擇從零開始。
她們脫下了襯衫,穿上了圍裙。
小佳在2014年7月,帶著8歲的獨生兒子,從中國一線城市過來新加坡,就讀政府小學二年級。之前,小佳在國內某大型跨國企業管理層任職,是個不折不扣的女強人。她的丈夫也是大公司高層,屬於富裕、不差錢的家庭。

剛到新加坡時,一切都從零開始。因為不放心中介,幾乎生活上的所有事情都由小佳自己處理:找房子、換房子、銀行開戶、處理簽證……初來乍到,總免不了碰壁和吃虧。
此外,她還要照顧兒子的起居、監督他認真學習、輔導他的英語。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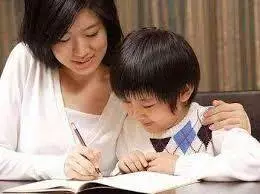
沒有了曾經在職場的光鮮,一心撲在兒子身上的她,過著家—學校—補習班三點一線的生活。
新加坡的學校放學時間早。為了培養兒子的特長,小佳還為兒子報了鋼琴課,每周兩次一對一輔導。
「千里迢迢來這了,就為了為孩子鋪條路。我辛苦一點沒什麼,花費高一點,也值得。」
讓她感到欣慰的是,兒子的成績非常好,考入了新加坡有名的初中;同時,兒子對鋼琴也很有天賦,已經在新加坡考過了八級。
像小佳這種情況,幾乎已經是大部分新加坡陪讀媽媽夢寐以求的。
第一,她不用為金錢擔心,被困於柴米油鹽中;第二,雖然磕磕絆絆,但是她幾乎可以獨立解決生活上遇到的各種問題,語言對她來說也不是難事;第三也是最重要的一點,她的兒子終歸不負所望,不枉她辛苦一場。

而更多媽媽的新加坡陪讀生涯則沒有這麼的順風順水,或多或少都會面臨一些生活上的困境。
首先要面對的,就是經濟上的壓力。
大部分家庭經濟條件一般惡陪讀媽媽們都希望能在新加坡找到一份工作,分擔家裡的經濟壓力。然而在新加坡,為了鼓勵陪讀的家長花更多的時間陪伴和幫助孩子適應新加坡,新加坡政府規定,陪讀媽媽必須陪讀滿一年才能申請工作準證。

在這一年期間,陪讀家庭需要負擔的費用是巨大的,幾乎沒有收入的陪讀媽媽承擔的壓力也是最大的。
2010年和丈夫離婚後,家裡並不富裕的小李帶著7歲大的女兒來到新加坡,女兒當時才剛剛讀一年級。
「陪讀第一年是最苦的,人生地不熟,也不能工作。還好我父母借了點錢給我。」
由於陪讀准證第一年是無法在新加坡工作的。為了補貼家用,小李只能冒險做一些小時工。有時候在飯店當服務員,站了4、5個小時,才拿到不到40新幣的工資。

不敢生病、不敢買東西、沒有任何娛樂活動、有活就接,任何髒活累活都干……小李就這樣熬過了第一年:
「當時真的是,刷盤子、服務員,連上門打掃衛生的小時工我都干過。」
跟她同年來到新加坡,有相似的陪讀經歷的媽媽小米,因為新加坡的生活壓力問題,已經在2016年帶著兒子回到了國內。據她描述:
「從剛到新加坡到後來,孩子的學費漲了、交通漲了、房租也漲了,眼看著錢快用完了,我沒辦法,撐不下去了。」
而小李的女兒已經在新加坡讀到高三了,她還在苦苦支撐。
經濟上的問題是最基礎的,也是最致命的。經濟問題之上,還有生活質量、語言、孤獨等等不可忽視的問題。
2018年7月,Lucy隻身一人帶著8歲的兒子Royle,登上前往新加坡的班機。
在朋友眼中,她一直是一個獨立而勇敢的陪讀媽媽,而如今,雖然已經時隔兩年,但是聊到最初紮根在新加坡的日子,曾經的無助、孤獨、矛盾,還是全部湧入Lucy的心頭:
「其實我並沒有那麼堅強。你可能想像不到,最初的一個多月,我哭過多少回。」
最大的不適應是源於生活質量的落差。
在北京早已經習慣了出門開車的生活,但是新加坡卻要乘坐公共運輸工具,地鐵、公交車。看著地鐵里熙熙攘攘的陌生人,有時她會突然不知道自己為什麼選擇這座城市:
有時候我會問自己,為什麼要放棄北京舒適的生活,舒適的家,而在這裡租房子擠地鐵?
生活上的巨大落差,讓她一次次的質疑自己曾經的選擇。那一日和Royle從地鐵出來趕去學校,突然間傾盆大雨全身濕透,那一瞬間,她再也不想故作堅強,眼淚順著雨水傾斜而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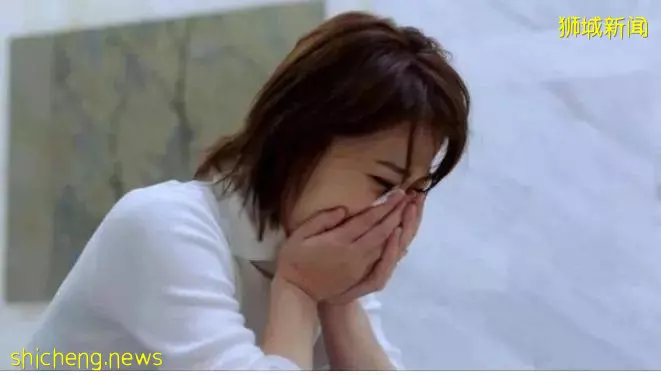
另一個難關就是語言。
「你能想像,第一次參加學校的活動,看到那些外國家長,我連一句Hello都說不出來的窘迫嗎?」
Lucy在回憶那些日子裡,語言給她帶來的前所未有的壓力。其實與學校和老師之間還算輕鬆,學校有會中文的協調員來幫助做溝通。但是有一些課程、學習資料,只能靠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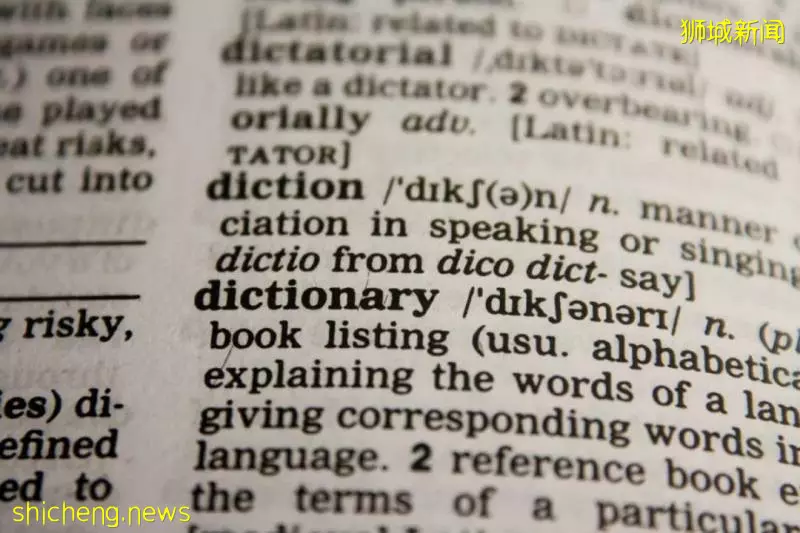
記得最開始給Royle報學校的那些興趣活動課(CCA),課程內容需要拿英文字典逐字逐句的翻譯了解,花費大量的時間不說,有時候理解得還不夠準確。
而在Lucy看來最大的障礙,還是與人打交道。很多時候想幫助孩子融入到學校、班級這個大集體里,家長也必須要努力參與到各種活動里。而且新加坡有這樣一個校園文化,父母參與學校活動、做義工志願者越積極,對於孩子在校內的發展越有幫助。可是英語不好,見到那麼多外國人,反而變得更沒有自信。
直到今天,語言問題仍然是Lucy的陪讀生涯中說不出來的痛。
孤獨,也是大問題。
對Royle來說,因為他年齡還小,在幼兒園很容易就認識新的朋友。但對Lucy來說,一下子脫離了自己的社交圈,在這裡沒有一個認識的人,開始是很難熬的。
白天兒子去上學,我就一個人呆在家裡,時間久了覺得自己都要發霉了。老公在中國要上班,工作很忙,我也不能一直找他。
Lucy苦笑著說。
但孤獨,似乎又是每個漂洋過海的新加坡陪讀媽媽都要上的一門必修課。
02. 陪讀,也「賠」了自己
通常來說,除了單親家庭之外,一般的孩子到新加坡留學,媽媽通常會來到新加坡陪讀,而孩子的爸爸在國內賺錢,負擔留學支出,父母二人分工會比較明確。
但是這樣下來,夫妻二人就必然聚少離多,陪讀媽媽也大多數都是孤獨的。
「老公跟我說去新加坡陪讀的時候,很多朋友表示羨慕我。原因?我老公是做生意的,有條件把孩子送出去讀書,接受雙語教育,還能讓我陪著孩子。」 今年只有30歲,面容依舊姣好的朵朵說道。
3年前,她和老公一起給孩子申請到了新加坡的學校,之後,老公讓她到新加坡陪孩子讀書。
朵朵的老公經營著一家公司,家境非常地殷實。朵朵平時在老公的朋友圈裡也認識不少富太太。在他們的圈子裡,有很多人讓老婆在國外陪伴孩子上學,過著衣食無憂的生活,而自己則在家裡另起爐灶帶著小三,過著浪漫的生活。

朵朵開玩笑問老公是不是也是這樣?嫌自己耽誤他了,才把她們娘倆送走了?
他笑笑說怎麼可能,都是為了孩子。
口口聲聲說為了我們娘倆,但他一次也沒來過看我們娘倆。
一到了晚上,回到了自己的房間,那空蕩、冰冷的雙人床讓朵朵找不到任何的歸宿感。

每當這個時候她就會拿起電話,撥打熟悉的號碼,而等待她的永遠是「我很忙」和電話被掛斷的盲音。
但是為了孩子,朵朵只能選擇忍耐。
…… 孤獨只是一方面,朵朵這樣的家庭自然是不用擔心錢的問題。對於普通家庭,即便爸爸的收入才是家庭的主要經濟來源,沉重的經濟負擔也使得很多陪讀媽媽不得不選擇在新加坡工作,甚至有些就此走上歧途,「賠」了自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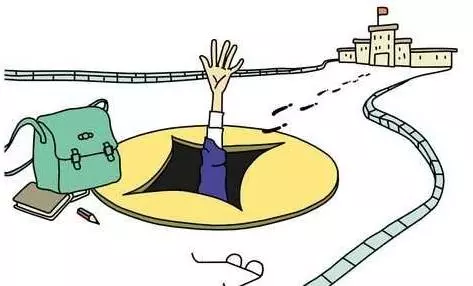
2008年,張姐帶著6歲的兒子來到新加坡求學。7年後和丈夫離婚,分得一筆不小的財產,於是在新加坡買公寓買車,也沒有去工作,只是全職專心陪伴孩子讀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