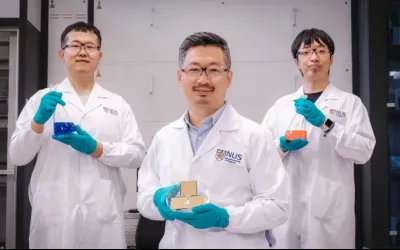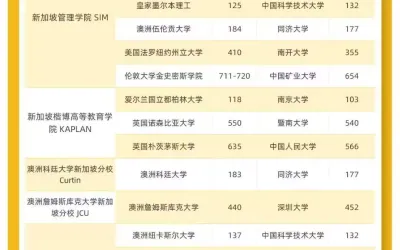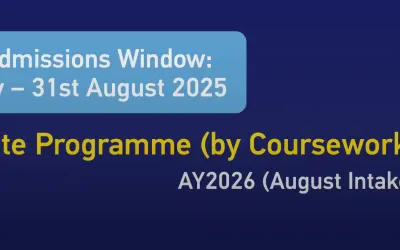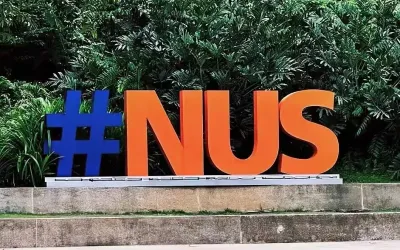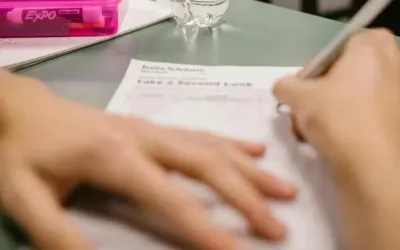今年3月5日,新加坡教育部宣布,本地所有中學將在2024年以前陸續實施科目編班全面計劃,不再有快捷與普通源流之分。
詳情請戳:

其實在2018年9月底,新加坡教育部就已經宣布了計劃廢除小二年底考試,以及部分小學和中學的年中考。
當時不少家長認為,儘管取消了部分考試,但部分習慣仍舊難以改變:
繁重的課後補習;小學離校考試(PSLE)是非常重大的壓力點;最重要的是,分流制度依然「根深蒂固」!
教育部當時是希望改革舉措引起社會思考:讓父母、學生或是教育工作者,能夠進行真正的、深入的反思,了解到什麼才是教育孩子更好的方式,像是學習的樂趣,培養以及激發好奇心,將會讓學生終生受用。

但具體落實下去必然遇到各種現實「壁壘」,所以關鍵還是取消之後的各項配套舉措能否跟上。
如今,中學階段分流制度的取消,降低對學業成績的過度偏重,全面培養學生的綜合能力。目的就是在各教育階段,打破了源流之間的界限!提供更公平的教育環境!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在去年展開了針對新加坡教育公平性的調查,調查顯示,26歲至65歲新加坡人當中,每10人就有約6人的教育程度比父母高,相對經合組織國家平均比例來得高,這也顯示出新加坡人的教育流動性在顯著提升。

OECD的調查報告從成人技能評估(Programme for International Assessment of Adult Competencies, 簡稱PIAAC),以及國際學生評估項目(International Student Assessment,簡稱PISA)兩項調查中獲取相關的數據。
教育一直在向上流動!
在教育向上流動方面,新加坡躋身世界前列,近十分之六的成年人獲得的資格高於父母。
在1940年代中至1950年代出生的成年新加坡人當中,父母教育程度高者完成高等教育,比父母教育程度低者高出55個百分點。

1970年代中至1980年代出生的新加坡人,父母擁有高教育水平者完成高等教育的比率,則比父母受教育低的國人高36個百分點。
這顯示,父母教育程度低的新加坡人完成高等教育的機會,過去幾十年來,顯著提高19個百分點。
在20世紀50年代,只有高中教育水平父母的子女只有不到20%的機會完成高等教育。
現在,這樣的人有大約60%的機會。對於至少有一名受過高等教育的父母所生的人來說,這個數字已從70%以上增加到90%以上。
「弱勢學生」表現其實很好!
另一方面,調查也發現,新加坡的弱勢學生的教育表現,對比其他國家的弱勢學生來得好,但對比自己國家內的頂尖學生,卻又有較大的落差。
經濟合作與發展組織(OECD)發布的報告發現,新加坡在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比例方面排名世界第三,僅次於澳門和香港。
在科學,數學和閱讀的客觀測試中得分很高。來自貧困家庭的15歲兒童中約有43%表示他們對這些核心技能的掌握程度很高,而經合組織國家的平均水平為25%。
經合組織2015年國際學生評估計劃也發現,在考慮到社會經濟地位後,新加坡大約一半的弱勢學生出現在國際頂級學位中,高於經合組織平均水平約30%!

但是,當涉及到「國家應變能力」時,這些學生的科學成績與自己國家的最佳表現者相比,只有十分之一符合這一標準。這低於其他24個國家教育系統中的比例,包括香港和芬蘭的教育系統。
針對OEDC的調查報告,新加坡教育部(MOE)表示:
來自低SES(社會經濟地位)家庭的學生相對於來自其他國家類似SES背景的同齡人而言表現是絕對可以稱之為不錯的。
與其他國家相比,這裡的弱勢學生所適用的「國家應變能力」的標準要高得多,因為在新加坡,優秀學生的表現實際上是非常出色的。
例如,在2015年比薩科學考試中,新加坡低收入家庭的學生中只有10%得分至少為631分。對於新加坡學生來說,631分被認為是比較科學的得分。
但在芬蘭,這個得分為599。因此,14%的社會經濟地位較低的學生能夠達到這個分數或更高。如果按照芬蘭的基準來算的話,大約17%的新加坡「弱勢學生」能夠達到599分及以上的分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