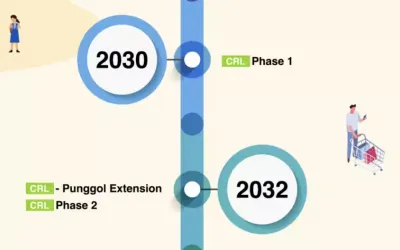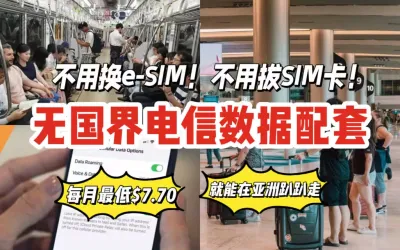刚来新加坡的前两周,我发现自己手机里几乎每天都有“走地鸡”的照片,因为它们太常在城市里出现了,在CBD办公区的石板路上,在组屋区的草坪上,常常就能看见走过一群鸡。

我觉得当时的我可比他们兴奋,毕竟这在上海的市中心几乎看不见活的鸡,更别提“走地鸡”了。

这些鸡毛发油亮、步伐坚定,像一支巡视午餐高峰区的安保队伍。它们不急不缓,甚至还穿过了马路——走斑马线那种。
这一幕让我恍惚了一下:新加坡的主人到底是谁?
时间久了,新加坡不只是花园城市,它是一座有些“野”的城市。
它的“野”不是张扬的猛兽,不是荒蛮的雨林,而是一种悄悄潜伏在你日常生活边角的、不请自来的生命力。
就像这几位,新加坡的野邻居们。
首先登场的,还得是红原鸡,被我一度称为“走地鸡”的那位。
它们看起来比家鸡更亮丽,尾羽弯曲像一把墨绿镰刀,眼神里带着一种倨傲。

我后来翻了NParks的资料才知道,这些红原鸡已被视作‘野生物种’,在新加坡各大绿带中自由生活,而公共管理也早已明确:请勿喂食,也禁止擅自带走。
新加坡自然协会认为它们已是野生种群,受法律保护。也难怪它们在CBD和组屋区的行为都如此从容不迫。
也许你会问,能抓他们吗?
答案当然是否定的,不过我之前看过一个视频,新加坡政府鼓励大家去捡鸡蛋,以此来控制它们的数量。
如果真的抓了鸡会怎样?
会触犯《野生动物法》,面临最高1000新币罚款,以及动物被没收的处罚。
我一直有个好奇,生活在城市里的鸡,晚上要去哪睡觉。
鸡上树。真的。
它们会在傍晚飞上附近的大树栖息,躲避地面的天敌。于是我如果晚上出门或者回家,都会习惯性地抬头看树,看今晚有没有“鸡上线”。
不过,鸡不仅上树睡觉,也上树打架,尤其是在CBD的鸡,午休时刻打嗝,过马路,也飞上树准备打架。
第二位出场的野邻居,我是在金声公园见到它们的。

我运气很好,第一次去就见到了它们。一只水獭从灌木中窜出,奔向五六只小水獭,一路滑行到水边,愉快地玩耍。
新加坡的水獭不止一群,它们是“家族制”,有“滨海家族”“璧山家族”“Zouk家族”等,不过它们更多时候被看成是水獭黑帮的爱恨情仇。

还有水獭粉丝在社交媒体上追踪它们的行踪和八卦:谁和谁打架了,谁又生崽了,谁在花园扒了鱼池。
你很难不被它们萌到。它们不野蛮,甚至有种“城市水居民”的体面感。

(图片来自ottercity脸书)
我想,如果说我们在CBD办公楼里是上班族,那他们就是水边的自由职业者吧,爱潜水,不打卡。
之前在日世界水獭日写过我与它们的相遇,具体可以参见文章《5.28世界水獭日,看见城市里“毛茸茸的邻居”》
第三位野邻居,我在植物园遇见了它们。
新加坡植物园的草坪上,除了散步的人、野餐的小孩,有时还会有一位“阳光诗人”。

那是一只马来水巨蜥(Malayan Water Monitor),静静地趴在草堆上晒太阳。

它不动,就像一尊长满鳞片的雕像,直到你靠近,它才“啪”的一下钻进灌木丛,留下一地树叶微颤。
我第一次见到它们,就是低头玩手机再猛然抬头的时候看见的。
我那一声尖叫,明显让我们两个都有些手足无措地愣住了。
这些蜥蜴是城市里被允许保留“野性”的存在,它们既不入侵,也不逃避,就像城市给自然开了一个窗口,它从里面伸出一只爪子,说:嗨,我们还在。
但是,要说最让我吓一跳的野邻居,那一定是乌鸦。
那天我走进客厅,看到阳台栏杆上站着一只黑漆漆的乌鸦,像哨兵一样望着我。

19楼,阳台,乌鸦?
在我没反应过来的时候,身体发出的尖叫先比我快一步。
不出意外地,乌鸦也被我吓了一跳,下一秒就飞走了。

我后来才知道,乌鸦他们会认人脸,研究表明乌鸦能记住伤害过它们的人的面孔,并长期怀恨在心,还可能叫同伴一起报复。
所以有一阵子,我有一点自我怀疑,虽然我尖叫了,我没有伤害它,它们应该不会记住我的脸吧?
后来每次见到乌鸦都绕道走,默念“我们不熟,我们不熟”。
我不是怕它,我是尊重它的记忆力。
和乌鸦长得很相似,不过眼睛是红色的一种鸟也很有趣。
我在《野邻居》这本书里读到这种鸟——噪鹃(Asian Koel)这种鸟,简直刷新三观。

这种鸟不自己孵蛋,而是趁乌鸦不注意,把自己的蛋下进乌鸦的巢里,还会把乌鸦蛋踢出去。
更离谱的是,它们的雏鸟会模仿乌鸦的叫声,提高“欺骗成功率”。乌鸦就这样傻乎乎地把不是亲生的孩子,一口一口喂大。
这让我又有了新的困惑:乌鸦都能认人了,怎么就认不出自家崽不是亲生的?
书中给的答案是:鸟类很多时候靠声音、动作、嘴巴张开的形状来识别“孩子”,而不是“长得像不像”。
噪鹃这一整套“寄生育儿法”是几万年演化出来的完美骗局。
看来乌鸦再聪明,也有它看不穿的盲点。
有时候我们也是这样。我们以为我们识得真心,其实只是听见了熟悉的声音,就误以为是“同类”。
我在书里读到,除了这些现身街头的野朋友,新加坡还有一些你听名字就会觉得“很博物馆”的朋友,比如:莱佛士叶猴(Raffles’ Banded Langur)。

这种毛色分明、动作优雅的猴子,生活在新加坡的自然保护区,数量稀少到几乎可以点名。
它们是以新加坡开埠者莱佛士命名的,就像很多本地动植物一样:
乌鸦、猕猴、小麂,甚至已经灭绝的乳白巨松鼠,都是当年莱佛士“科学狩猎”中的“命名对象”。

这个城市从一开始就和自然紧密勾连。你看它的绿带、连绵的水道、组屋之间的空隙——不是为了浪漫,而是一种带着现实感的生态设计:让野朋友有路可走。
新加坡的“野”从不在远方。
它在你家阳台、你每天经过的地铁站、你晚饭后散步的行道树上。
它也许不是狮子老虎,但它依旧自由、灵动、让人惊喜——甚至让你尖叫。
我们常说城市是文明的象征,但也许真正理想的城市,不是把一切“野性”清除干净,而是给它们留下生长的缝隙。
鸡可以飞上树,乌鸦可以记住脸,水獭有朋友圈,噪鹃会演戏,蜥蜴晒太阳……它们像一群没被通知搬走的老居民,静静提醒我们:
这片土地,从来不只是人类的。
PS:《野邻居》这本书超有趣,现在已经可以在新加坡的书店买到啦~推荐!

参考文献:
National Parks Board. (2022, November 15). Feathered neighbours: Wild chickens in our city. Channel News Asia.
https://www.channelnewsasia.com/singapore/wild-chickens-singapore-population-feathered-neighbours-focus-3027986
Singapore Statutes Online. (1965). Wildlife Act (Chapter 351). Government of Singapore.
https://sso.agc.gov.sg/Act-Rev/WA1965/Published/20001230?DocDate=19870330
叶孝忠(2025)。野邻居。新加坡:𨑨迌工作室 Wonder To Wander