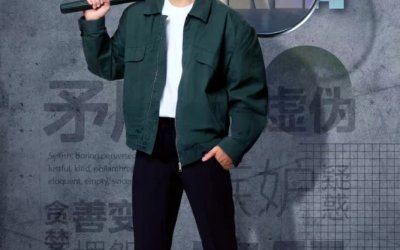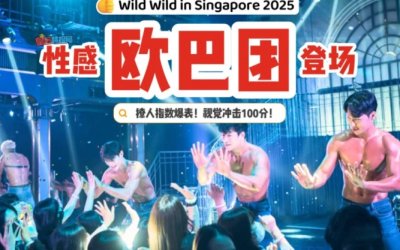《情断昆吾剑》剧照
“可惜不是潮剧发源地的剧团演出的”
2019年11月1日晚,《情断昆吾剑》在广州南方剧院演出结束后,微信名为“叮叮”的观众发了一条朋友圈,称赞演出精彩的同时,也感叹:“比较可惜的是这剧不是潮剧发源地的潮剧团演出的……发源地还是要加油。”
其实在新加坡,要传承传统戏曲的难度比中国更大。“新加坡毕竟是一个移民国家,教育的语言是英文和华文为主,造成家乡方言逐渐被遗忘,年轻人不会说了,家庭里面也用英文或者华文沟通,所以要传播潮州话是一个真正大的挑战。”但年过古稀的卓林茂却有一股壮心不已的豪迈,“我们都是以正面、积极的心态来看待这件事,如果每件工作都因为困难而不去做,那什么事都不用做了。所以这也促成我们有这个胆量来尝试这部戏。”
“墙内开花墙外香”的现象给黄剑丰的启发非常大。“国内的潮剧观众,喜欢吉祥圆满大团圆的结局,下乡去没法演这个戏,我觉得潮汕人这种审美模式可以改改。悲剧其实更有感染力,悲剧是将美好的东西打碎给你看,能引起人的思索和感触。潮剧的传统观众可以尝试更加包容一些。”
在潮汕本土,潮剧最大的市场是“老爷戏”。潮汕人普遍信仰“老爷”(潮汕话中泛指神明),几乎每个村子都有神庙,每逢“老爷”圣诞要做戏给神明观看,俗称“老爷戏”。由于有强大的信仰支撑,即便在全国传统戏曲最低迷的时代,潮剧团的生存也没有问题。值得关注的是,现在每逢乡下做戏,台下坐着的几乎都是60岁以上的老人。偶尔会有年轻人走过去,拍张照片发微信朋友圈,或拍个视频发抖音,然后便走开了。
“还是希望演出的戏能吸引年轻人来看,我说的年轻人是指40岁以下。”卓林茂这句话看起来是成功的关键。“中国跟新加坡的国情不一样,但是一个相似的地方,就是在汕头这样的城市,要吸引人来看戏是个挑战,乡下老一辈人还很多,他们欣赏传统的戏曲,新加坡也有一些戏班在演‘老爷戏’,现在看来都没前途了。这就造成业余的剧团(如南华潮剧社)认真做事、寻求创新变得越来越专业,专业的剧团习惯演‘老爷戏’,不知不觉会降低专业要求,反而走上了被市场淘汰的路。”
目前,南华潮剧社培养了近20名3-15岁的小演员,在当地演一些小戏。卓林茂介绍说,“全世界的电脑、电视、手机在提供不同样式的娱乐节目,也会造成影响。我们明确自己的目标、使命,然后尽量去做,我相信也能够把优良的传统传承下去。如果现在做戏,不去培养年轻人,十年之后不管你的戏多好还是没观众。通过《情断昆吾剑》之类的大胆尝试,希望吸引他们来看戏,不然他们去看动画片、看电影了。”
这一次走进校园,南华潮剧社邀请了马来族、印度族的学生跟华族的学生一起参与设计LED背景,使少数民族的学生也能了解什么是潮州戏、什么是传统戏剧。为了让不同语种的观众都能了解剧情,平时每次演出都有中英字幕。
新加坡人做事的大胆与包容让黄剑丰颇为感慨:“中国也提倡戏曲进校园,但我们是到校园里去演几个节目,或者站在讲台去做讲座。新加坡他们的戏曲进校园,是让学生一起来参与创作,具有互动性。不懂潮剧也可以参与,不会说潮汕话也可以参与,不是华族也可以参与。”
2019年,3月份《情断昆吾剑》在新加坡上演不久,京剧《新龙门客栈》4月底在上海演出,很快豆瓣上就有人将两部戏相提并论,探讨武侠跟传统戏曲的融合问题。黄剑丰认为,之所以潮剧用新武侠题材比较少,是因为新武侠小说进入内地的时候,刚好是潮剧的低潮期,而且当时武侠小说被当作“闲书”、“地摊书”,反而在东南亚比较流行,所以武侠题材的潮剧能在新加坡上演也比较好理解。
在黄剑丰看来,潮剧在本土创新乏力的另一个原因是潮剧对编剧这个角色不够重视。“潮剧以前是很冷门,但现在老人小孩很多人唱,卡拉OK也很多人会唱,市场其实繁荣。但外表的繁荣掩盖不了潮剧衰老的现状,唱的都是旧的。会唱的人很多,会演的人也很多,但会创作的人屈指可数。潮剧是潮汕文化的集中体现,说到底还是要靠文化来支撑,一个剧本就是一个文学作品,现在剧团普遍实行导演制或者演员制,从戏曲的渊源来看,剧本是一剧之本,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戏曲未成形的时候,演唱的是诗词,这些诗词必须由文人来写,再给到演唱者去唱,最典型的就是宋代的柳永,歌女们争着求他作词。一个好的剧本,其实就是一个诗剧,唱词如诗如画。”
此次《情断昆吾剑》虽然引发了专家和媒体对传统戏曲创新的讨论,不过黄剑丰坦陈,当初创作的本意不是推动潮剧发展,而更在意剧本的文学价值,至于能给潮剧发展带来影响那是意外的。
《情断昆吾剑》首演之后,新加坡当地便有人邀请黄剑丰创作其他题材的潮剧,南华潮剧社的卓林茂社长也承诺,他创作的剧本将优先排演。国内的粤剧、越剧都有人邀请黄剑丰创作剧本,他自己也从元杂剧《张羽煮海》中得到灵感,打算创作一个神话剧本,讲述潮汕人靠海而居、与海作斗争的故事,以及爱拼才会赢的拼搏精神,但早先写《情断昆吾剑》的教训让他对戏曲剧本创作比较谨慎:“先让我休息一下吧。”
南方人物周刊 陈斯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