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率而言,在大国及大国关系主导、现实主义思维占据主流的国际关系中,大国对特定小国的认知和行为是后者国际定位的决定性标尺。以此来看,地理禀赋同样是小国的“宿命”,它相当程度上界定了小国在国际体系中的地位、价值、角色及其行为选项。
第一,地理位置是小国国际地位和战略价值的关键标尺。地缘政治学探究的是空间的政治意义,认为地理因素对政治行为和国家权力至关重要。英国地理学家哈尔福德·麦金德(1861-1947)的“大陆心脏说”,美国海军军官、历史学家阿尔弗雷德·马汉(Alfred Thayer Mahan,1840-1914)关于海洋与国家力量关系的“海权论”,以及意大利的吉乌利奥·杜海特关于“制空权”的学说,分别从陆地、海洋和天空三个视角讨论了地理因素对于战略安全和国家权力的影响。其中,马汉认为任何地方的战略价值取决于“位置”或“态势”、“军事力量”和“资源”这三个基本条件,同时具备这三大条件的地方就会成为“战略要地”,并可能具有“首屈一指的重要作用”。战略要地意味着战略价值和战略关注。当代世界,无论从哪个角度看,地理因素对地缘政治都具有重大影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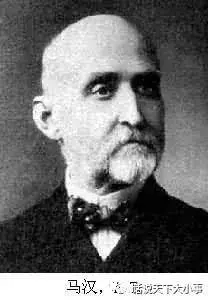
马汉
美国海军战略思想家马汉的海权论主张制海权对一国力量最为重要。海洋的主要航线能带来大量商业利益,因此必须有强大的舰队确保制海权,以及足够的商船与港口来利用此一利益。马汉也强调海洋军事安全的价值,认为海洋可保护国家免于在本土交战,制海权对战争的影响比陆军更大。
地理位置赋予了小国特定的战略价值。在大国视角中,位处全球战略要冲的小国往往具有更重要的战略价值。这样的地理位置一方面构成了经济发展的有利条件,另一方面也是吸引和利用大国的重要政策筹码。一些小国往往会“充分利用其经济能力或战略位置来影响大国”。地理位置优越的小国往往成为国际关系的“支点”,吸引著众多大国的战略关注;而那些远离世界政经中心的偏远小国则很难引起大国的战略兴趣,它们是被国际政治经济遗忘的角落。
特定的地理位置意味着不同的战略含义,并与全球战略安全和国家权力相关联。与世界权力中心、世界大国接近的小国,在海洋交通运输中具有枢纽作用的地方,与战略资源接近的国家都是大国关注的战略要地。战略位置与战略资源一起成为吸引大国关注的重要因素。在全球战略版图中,中东、东南亚、中美洲、北非等地区具有显著地位。譬如,东南亚位于太平洋、印度洋两大海洋及亚欧大陆与大洋洲两大洲之间,是世界海洋运输最重要的交通枢纽,东亚国家必需的中东石油进口的必经之路。在联合国秘书处列举的8个重要国际海峡中,3个是处于中东的无替代航路的重要海峡,即曼德海峡、达达尼尔海峡和霍尔木兹海峡;另外5个全都位于东南亚,它们是马六甲海峡、巽他海峡(爪哇和苏门答腊之间)、新加坡海峡、圣贝纳迪诺海峡(菲律宾东南部吕宋和萨马岛之间)、苏里高海峡(菲律宾的莱特岛和棉兰老岛之间)。这种“桥梁”式的战略位置对于战争与和平都是至关重要的,它既是“兵家必争之地”,也是确保经济运行的“生命线”。处于该地域的小国无疑具有更多的发展机会、更大的战略行动空间。
职是之故,相较深锁内陆及地理偏远的小国来说,那些位处世界政经战略枢纽的小国显然是大国和强国积极关注、利用和争取的对象。有吸引力的地理位置不仅能够引来大国的经济资源,而且有助于其对外战略的制定和实施。
第二,地理位置塑造著小国特定的外部环境。与大国显著不同的是,小国安全的主要威胁不会来自遥远的国家,而是毗邻国家和地区。在周边国家发展繁荣、稳定有序,周边环境安详和平,区域安全治理机制健全的地区,小国安全将得到更充分的保障。欧盟小国享有的长久和平,与欧盟整体上的良好安全环境密不可分。相反,在一个发展滞后,遍布失败国家的动荡地区,生存于其中的小国将不可避免承受更多的安全威胁。
地理位置也影响着小国与大国的关系。在任何体系中,地理和资源都是影响国家权力的重要因素,地理位置是小国发展同大国关系的重要背景。譬如,与大国毗邻通常带来了脆弱性,但小国在面临来自强邻巨大压力的同时,所具之战略位置和战略资源也在改善其地位。因此,相较其他因素,地理位置对小国外交的意义显得更加突出。
一方面,一个国家在全球战略版图中的地理位置规定了其战略价值,是吸引大国关注的重要因素,进而是它们发挥国际影响力的条件。1956年以前,英国一度将控制苏伊士运河作为自身的责任和使命。美国关注巴拿马海峡,德国则关心波罗的海出海口。
另一方面,处在地缘政治中心的小国往往成为大国对抗的焦点,因而处在危机四伏的外部环境中。在历史上,比利时、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以色列、丹麦、挪威、芬兰等小国都无法避免地缘竞争带来的巨大威胁。与此相对,爱尔兰、瑞典、新西兰、加勒比国家、南太平洋岛国则得益于远离大国纷争中心的边缘位置,而免遭征服或者干涉的危险。对小国而言,地理位置是福是祸,最终还是取决于国际体系的性质。
第三,地理位置是小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初始条件。在这个世界上,有的国家拥有许多邻国,而有的国家则没有邻国。在不同的情况之下,一个国家与其邻邦之间的地缘政治关系具有不同的意义。与多个国家相邻的小国,在外交上必然会倾向于考虑更多的安全威胁来源和多方位外交的发展态势。只与一个国家接壤的小国,双边外交就是外交的优先考虑。比如丹麦(与德国)、冈比亚(与塞内加尔)、莱索托(与南非)、摩纳哥(与法国)、卡达(与沙特)、圣马力诺(与意大利),与强邻之间的关系是这些小国外交政策不得不高度关注的因素。芬兰和瑞典的安全战略很大程度上受到毗邻大国苏联/俄罗斯的影响,不加入北约的战略考虑之一是避免成为俄罗斯与西方潜在冲突的牺牲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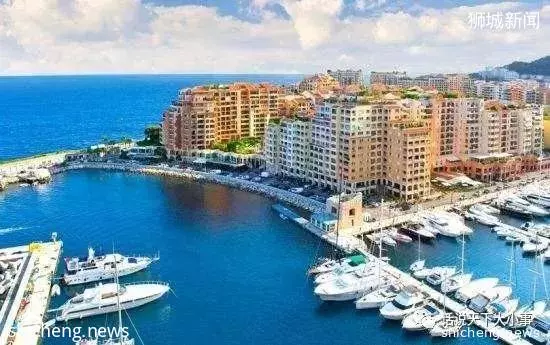
摩纳哥
摩纳哥是位于欧洲的一个城邦国家,也是世界第二小的国家(面积最小的是梵蒂冈),总面积为1.98平方公里。摩纳哥地处法国南部,除了靠地中海的南部海岸线之外,全境北、西、东三面皆由法国包围,为少有的“国中国”之一
地理位置深刻影响着小国的对外战略选择。小国不能塑造地缘环境,但地缘环境是影响小国对外战略选择的关键因素。远离世界政治经济中心的诸多岛国,如南太平洋岛国、加勒比岛国和印度洋岛国,虽然在经济发展上面临着不利的地缘环境,但在安全上也超然于大陆上国家间常有的纷争,对安全战略也就没有处心积虑的必要了。然而,大陆小国,尤其毗邻大国的小国往往会身不由己地介入到大国博弈之中,它们的外交战略选择就显得格外重要了。对这些小国而言,在对外战略选择时,地区环境和大国关系是不得不思虑的重要背景。
仍以新加坡为例。独特的地理位置既是新加坡对外战略的重要砝码,也是其“大国平衡战略”构思和实施的前提。平衡战略的要诀在于吸引诸多大国的战略关注,而大国的战略兴趣往往来自战略价值的多寡。新加坡的地缘战略价值不言而喻,是关乎其生存的重要优势。大国普遍认同新加坡的战略重要性是它发挥这一优势的前提。
李光耀指出:“芬兰如果被邻国苏联或瑞典侵略,列强可不必理会,因为这跟列强之间的势力均衡没有关系……可是如果没有了新加坡,那就对它们非常麻烦了。我们必须好好照顾这一点;我们的地方虽小,可是几乎全世界都公认这个小岛具有极大的战略重要性。”现实之中,新加坡奉行积极外交政策,广泛结交诸多大国,“鼓励世界上的主要强国知道它的存在”,并理解新加坡所具有的战略意义,在大国交织的利益网络和战略关注中凸现自己的价值,从而娴熟地操作大国之间的平衡策略。一言以蔽之,地理位置是新加坡对外战略制定的依托。
第四,国土形状对小国对外关系具有特殊影响。不同的领土形状对一个国家的社会文化、经济发展、国家治理甚至对外关系具有不可忽视的影响。与此同时,地理位置与领土形状的叠加效应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小国外交的基本取向。大多数国家的形状或形态可以分为五种类型:一体型(compact)、碎块型(fragmented)、狭长型(elongated)、孔眼型(perforated)以及凸出型(protruded)。不同领土形状具有不同的安全意义。一体型国家具有环形形状,是最容易管理的形态,有助于维持国家的统一,也比其他形状的国家更易于防卫。碎块型国家由许多海岛构成,这样的国家难以管理。狭长型国家对边远地区的管理非常困难。孔眼型国家的领土完全包围于一个或多个国家,只有通过这个(些)国家才能到达被包围的国家。如果两个国家存在敌意,那么被包围国家就难以与外部联系。凸出型国家有狭长的土地延伸出来,突出地带往往产生离心倾向。不言而喻,不同国土形状的国家,其政经策略、安全思维、外部认知及对外政策各有差异,最终也影响了它们的外交取向和战略手段。

智利
智利是世界上领土最狭长的国家,其国土南北长4332公里,东西宽90-40l公里,在地图上看起来就好象南美洲的“裙边”
以此观之,地理因素对行为体的影响与意义从来都是不争的事实。它对人类生活方式、社会政治文化和行为均具强大的建构性影响。在“小”的作用下,地理条件在小国政经发展中衍生出诸多突出效应。规模越小,这些效应就越显著。可以断言,绝大多数小国的政经发展与行为选择相当程度上取决于其所拥有的特定地理禀赋。事实表明,小国的地理“宿命”既不是危言耸听,也不是对小国主观能动性的无视。在现实性、竞争性国际体系下,地理效应是小国特性衍生的“副产品”。因为“小”,所以小国在生存发展中上得靠“天”,下得靠“地”。对小国来说,地理效应的表现方方面面,此理所必然,现实案例也俯拾皆是。相较大的国家,这难道不是小国的地理“宿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