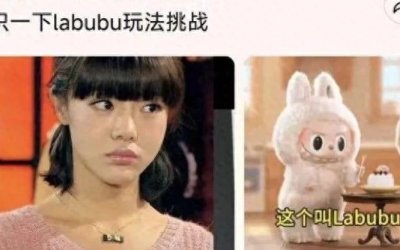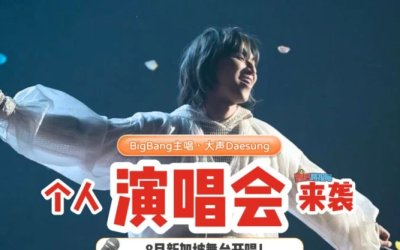新加坡跟我們淵源已久,在比較古的時候,就有很多福建人、潮汕人為了討生活下南洋,在彼岸之坡安家就業,到今天推薦的這兩部電影演繹的時期,早就過了不知道多少代,成為坡上人很久了。
不賣關子,電影名曰「我們的故事」及2,從上世紀六十年代,被趕出夫家回到娘家的一個女人「招弟」和她的孩子們講起。

那個時代,是新加坡的男性還可以討小老婆的時代。
招弟的丈夫去世,她帶著三個女兒和碩大的孕肚,被大老婆趕出家門。
在那個時候那個地方,生的女兒再多,只要沒生齣兒子,也就跟不能生育沒啥區別。
無奈之下,招弟只能回到娘家尋求幫助,而等待她的,是自私混帳的大弟弟和因為迷信犯沖讓她從小稱呼為「四叔四嬸」的親生老父老母。
在這樣的家庭生活,艱難可想而知。
肚子裡的遺腹子雙胞胎剛出生,招弟就被迫把襁褓中的女兒送人,只因村裡的神婆跟「四叔」叨咕,說女兒是災星會妨害家人,兒子是富貴命可以留下。
帶著剩餘的三女一子寄人籬下,招弟不得不承擔很多繁重的勞動。
為了謀生,她跟鄰居一起在街邊販賣豆漿。

那時候的坡上,今天是黑社會索要保護費,明天是城管驅逐小販,想做點生意賺錢真是兩頭夾逼。
但再難也得夾縫中生存,甚至有一天,招弟他們急中生智,慫恿黑社會履行保護功能,保護他們免受城管驅逐,竟然讓小混混跟稽查大隊打了起來,令人啼笑皆非。
當然啦,事情總是向著好的方向發展,後來的後來,小混混從良,招弟他們也被安排到農貿市場正規經營,生活漸漸有了起色。
小人物生活見證國家大歷史,這樣的片段在電影里還有不少。
比如,招弟家要拆遷房子,政府會給補貼,大弟弟阿坤聽說盯上了自己當初不要、一直被姐姐打理的豬圈,開始百般刁難、軟硬兼施,希望能分得更多的錢。
我查了一下資料,那是 1966年,新加坡國會通過了《土地徵用法》,為組屋建設運營、土地徵用等提供法律依據。明確規定政府有權在必要時,為公共用途強制徵用私有土地,不過會給予土地所有者補償。有點類似國內的拆遷戶,但賠償金額遠遠沒有那麼多。
當時新加坡剛建國不久,本地幾乎沒有人以新加坡人自居,他們大多數都說「我是福建人,我是馬來人,我是印度人」等等。
如果國民都這麼沒有歸屬感,那還建什麼國?
李光耀就發話了:「居者有其屋,有恆產者有恆心!」
於是促成了征地、組屋申購等一系列社會變遷。
想當初新馬分家,貌似民眾還有選擇權,可以自己決定成為馬來西亞還是新加坡公民。
馬來人鄂圖曼,選了華人比較多的新加坡,因為他覺得自己的熟人朋友都在這邊,割捨不掉。

這也為後來的種族紛爭埋線。
種族之間的屠戮向來殘忍,之前看電影《盧安達飯店》,嚇得我兩天晚上做噩夢。
不過這兩部電影中的種族對抗卻是淡化過程、美化結局,沒有血腥場面。
比如華人招弟和馬來人鄂圖曼,通過朋友的關係互相說和彼此的村子,避免了戰鬥,印度人稽查隊長去村裡安撫村民,也幫助減少了不少暴力衝突。
而這又為後面招弟的小弟弟阿喜與印度人的婚姻埋線。

招弟想到自己的父母極度迷信,就跟父親說,自己去菩薩面前,連續兩次求得的竟然是同一根上上籤,菩薩都認可的事誰敢不從?

在印度親家那邊,利用親家公多年公務人員的身份,讓他下意識背誦出李光耀民族團結的政策,意識到聯姻不可違。
誰能想到,這良緣能成,一邊靠的是迷信,用魔法打敗魔法,一邊靠的是李光耀的民族政策深入人心。
總之,這兩部電影,沒有迴避一些惡俗,比如重男輕女,把大兒子慣得不成器,一味剝榨女兒招弟,比如封建迷信,萬事問菩薩,迷信到一輩子讓女兒稱呼自己的親生父母「四叔四嬸」 ,直到將死之時才發現犯沖也無所謂,讓女兒叫回「阿爸」,令人恨中又有一層淚。

電影也沒有刻意美化人物或he,比如大弟弟阿坤廢柴混蛋,但對於新加坡政府的態度,卻很多是電影通過阿坤的吐槽完成的。
而女主人公招弟,任勞任怨為家為親辛苦操勞,拿到政府征地補貼時,本以為是苦盡甘來,卻患上癌症,不久就結束了含辛茹苦的短暫一生。
犧牲和奉獻,那也是一個東南亞華人婦女史詩般的人生,可能也是很多下南洋創業的新加坡華人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