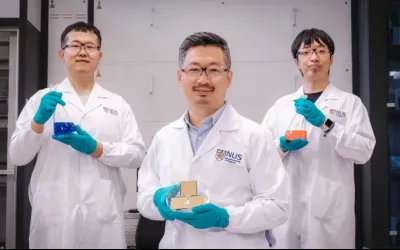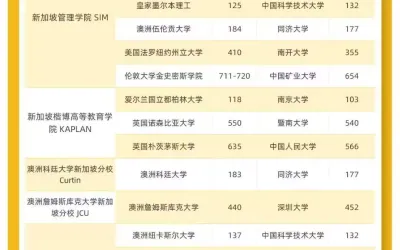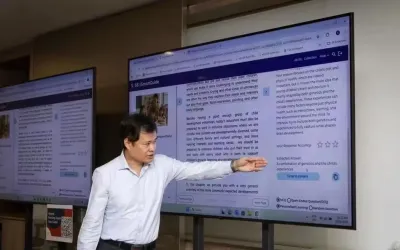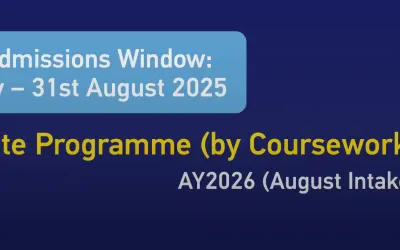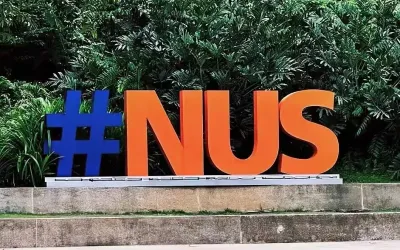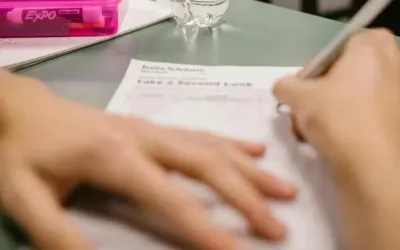新加坡統計局(7日)公布了本地受僱居民住戶的工作月入中位數。
數據顯示,本地受僱居民住戶的工作月入從2022年的1萬零99元,增長至去年的1萬零869元。
不過,每當這類數據公布,網絡上往往會有部分聲音質疑相關數據偏離了一般新加坡人所面臨的真實情況。
這些疑慮在某些情況下,或許與對相關數據的誤解有關。
紅螞蟻以下將針對幾個較常出現的經濟數據展開說明,希望大家未來能更精確了解相關數據背後所代表的含義。
為何用中位數而非平均數?
蟻粉應該不難發現,每當官方呈現收入之類的數據時,大多會用到中位數(median),而非大家更熟悉的平均數(mean)。
首先,我們必須先理解,在簡單的數學原理中,所謂的平均值(average)其實有三種不同的測量方式,其中較常見又屬平均數(mean)和中位數(median)。
以下是平均數和中位數的計算方式:
平均數:將所有數值相加,然後用總數除以相加數值的數目來測定(這也是大眾最熟悉的平均值(average)算法)
中位數:將所有數值從高到低排列,然後找到位於最中間的數值來測定
呈現本地居民的收入數據時之所以採用中位數,是因為中位數比較不容易受一組數據中極端值的影響。
舉例來說,紅螞蟻和身家達2000億美元的全球首富馬斯克的財產加在一起是2000多億美元,以平均數來說,就是2000多億美元除以2,因此紅螞蟻和馬斯克的資產平均數為1000億美元。
但這並不意味著紅螞蟻的身家有1000億美元,實際上是馬斯克超高的「極端值」墊高了身價平庸的紅螞蟻。
再舉個例子,如果將紅螞蟻和8個一般收入的打工族,以及全球首富馬斯克合共10人關在一間房間,計算房裡10人的財產平均數(mean),也很有可能得出大家平均有200億美元的結論。
同樣的,我們也知道這偏離了現實情況,因為馬斯克近2000億美元的資產是個異於常態的極端值,才大幅拉高了平均數。
因此,在這種情況下,就有必要以中位數計算,將紅螞蟻和其他打工族,以及馬斯克的資產按數值高低排列,取出位於中間的中位數來判定房裡10個人的財產現況,以得出比較符合現實情況的答案。
同理,堪稱新加坡「打工皇帝」的星展集團總裁高博德(Piyush Gupta)在2022年的收入高達1540萬新元,無疑也是個極端值,這時如果用平均數來呈現本地居民的收入,就有可能導致過於高估的情況,因此改用中位數,才能更精確反映本地打工族的收入實況。
以2023年本地受僱居民住戶工作月入中位數1萬零869新元來看,即意味著在新加坡有一半家庭的工作月入少於1萬零869元,一半家庭工作月入高於1萬零869新元。

本地家庭工作月入2023年的工作月入中位數為1萬零869新元。(海峽時報)官方數據的居民收入通常計入公積金和花紅
解讀當局有關國人收入的數據時也必須注意,相關算法並不僅限於我們每個月實際上能領到的工資(即所謂可以「帶回家」的工資),該算法同時也包括了公積金和花紅。
根據新加坡統計局的定義,所謂的家庭月收入具有以下幾個重點:
家庭收入是所有受僱家庭成員的工作收入總和;
上述收入也包括了花紅的12分之一(即把該年花紅平均分配到每個月);
上述收入包含僱主和雇員繳交的公積金。
因此,在解讀家庭收入時,也必須考量到有的家庭月收入雖然看似較高,但這可能源於他們的家庭規模較大,同時工作人口也較多。
此外,人力部所公布的居民個人月收入中位數,也同樣把公積金和花紅納入計算。
根據現行規定,我國55歲以下雇員每月工資的公積金總繳交率是薪水的37%,即僱主和雇員分別繳交17%和20%。
換句話說,當局數據中一名月薪5000新元的新加坡人,在扣除公積金後,每個月實際能拿回家的錢最多只會有3150新元,如果他/她在當年還有領取花紅,那每個月實際拿回家的金額可能還會更少。
根據人力部統計,2023年本地居民的個人工作月入中位數為5197元,即代表在新加坡有一半居民的工資少於5197新元,另外一半居民的工作高於5197新元。
下次如果「感覺」自己的薪資和全國中位數相比「誇張地低」,或許可以先提醒一下自己,有沒有少算了公積金和花紅的部分?
按照當局的邏輯,那筆錢你只是暫時沒拿到,但實際上最終都會進入你的口袋,所以當然會計入你的薪資所得。

官方有關個人和家庭收入的數據都有納入公積金繳納額和花紅。(商業時報)實際收入、名義收入傻傻分不清楚?
接下來再談談當局在公布薪資增減相關資訊時會用到的兩組詞彙——「實際」(real)和「名義」(nominal)。
這裡要先套句長輩很愛說的「想當年」:
想當年,一杯咖啡才多少錢;想當年,一盤雞飯才多少錢;想當年,一餐雜菜飯才多少錢……
通貨膨脹是經濟發展中不可避免的因素,因此,20年前的一塊錢,不會等同於今天的一塊錢,兩者的購買力是不盡相同的。
因此,國人薪資的增長幅度也得跟上通貨膨脹的速度,才可至少維持或改善生活條件。
當國人收入「名義上」增長時,這隻代表薪水數值的增長,但並不等同於國人的購買力增加;只有當國人收入「實際」增長時,才意味著購買力的增長,是名副其實的增長。
以新加坡統計局今早公布的數據來看,本地受僱居民住戶的工作月入從2022年的1萬零99元,增長至去年的1萬零869元,「名義上」增加了7.6%,看似很多,但考慮通脹後,「實際上」只增加了2.8%。
另一更直觀的例子是2023年的本地居民個人的工作月收入。
根據人力部數據,儘管2023年本地居民個人月收入中位數從2022年的5070新元增至5197新元,「名義上」增加了2.5%,但眾所周知,本地去年出現嚴重通脹,因此本地居民個人月收入中位數「實際上」反而下降了2.3%。
換句話說,去年國人所賺取的薪資帳面上來看雖是有所增長的,但實際購買力確實是下滑了。
因此,思考個人薪金究竟算不算有實際增長時,最簡單的判斷方法便是薪金增長的幅度,有沒有超過同時段的通脹率。

2023年是通脹嚴重的一年。(海峽時報)反映貧富差距現象的基尼係數
最後再談一下今天新加坡統計局也有公布的基尼係數。
基尼係數反映的是社會貧富差距的現象,以0到1表示,1代表社會收入分配絕對不平均,0則代表收入分配絕對平均。
數字越小,一個國家的貧富差距就越小;反之,數字越大,則代表該國的貧富差距越嚴重。
聯合國設下的警戒線為0.4,一個國家的基尼係數一旦超過0.4,即意味著貧富差距過大。
新加坡的基尼係數在2023年為0.433,較2022年的0.437來得更低,代表收入差距縮小。
乍看之下,我國的基尼係數高於聯合國設下的0.4警戒線,但必須注意的是,這只是在政府不進行任何干預下得到的數據,當局實際上會以政府轉移和稅制等手段,達到縮小國人收入差距的效果。
而納入政府轉移和稅務因素後,新加坡2023年的基尼係數實際上是0.371。
在新加坡,低收入家庭一般會獲得更多的政府相關補貼和援助,這類補貼和援助統稱為政府轉移。大家今年1月3日收到的社理會鄰里購物券(CDC Voucher),以及定期獲得的消費稅補助券(GST Voucher),便是例子。
此外,新加坡在稅制上也採取累進稅制,稅率會隨著納稅人收入的增加而升高,這意味著富人必須繳更高的稅,因此也可達到資源再分配的效果,協助改善收入不均的現象。
換句話說,下次在解讀當局公布的基尼係數時,不妨以納入政府轉移和稅收因素後的基尼係數為主,以更準確地了解我國收入差距現象的全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