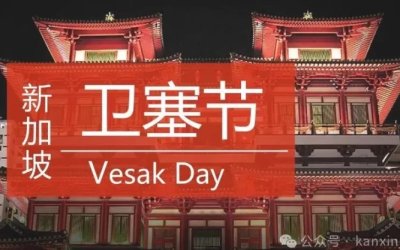彼黍离离,彼稷之苗。行迈靡靡,中心摇摇。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穗。行迈靡靡,中心如醉。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彼黍离离,彼稷之实。行迈靡靡,中心如噎。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悠悠苍天,此何人哉?
黍离之伤,有绵绵的故国之思,有不尽的凄怆之情。
2013年,新加坡世华文学研创会《新华文学大系》的短篇小说集出版。以这部文集为例,我们可以感知南洋大学作家群的辉煌——75位小说作家中,有19位有过南洋大学学习经历或身为南洋大学荣誉学士,占了四分之一,如果考虑到这些作家的年龄段集中于1934年(周粲)到1956年(南洋大学最后一届文学士彭飞)这二十二年间,那么这个比例还要扩大到近四成。可见在新马华人文化界中,南洋大学实则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
但是自1980年8月16日,南洋大学举行第廿一届毕业典礼之后,南洋大学终究难以摆脱时间的冲刷——当年毕业的最后一届学生,如今已经过了花甲之年。即使从1981年开始,校友们就开始组织“南大之夜”,即使 1992 年开始,“南大之夜”升格为全球南大校友联合会,即使如今时常掀起有关南洋大学复名、复办的讨论,但南洋大学其实在慢慢地、慢慢地沉下历史地表。

南洋大学的香火恐怕难以为继,但人们所缅怀的,不只是南洋大学这个实体,还有“南洋精神”。曾任南洋大学校长的吴德耀说,“南大所具有的特质是:别人不要做的,我们做;别人不能做的,我们能;别人无法容忍的,我们可以容忍。这种刻苦耐劳的精神就是南大精神。”。风沙雁则说,“南大精神,就是华族捍卫其民族教育权利的百折不挠的精神,这精神是源自华族寻求在新马扎下其文化和语文的完整的根的需要。”无论对“南洋精神”的解释在细微之处有什么不同,总之,它是“自强不息,力求上进”的精神。正因为“南洋精神”的存在,所以人们对南洋大学的感情已经远远超过了对一所大学应有的感情。
欧清池博士和吕振端博士在《新华文学大系·总序》中说,“如果后继无人,那么我们所编纂的大系将是新华文学长河终结的纪念碑”,此话何其悲凉!但是,我们不应对新华文学、新华文化完全失去希望,我们应当看到以东南亚华人群体们的渴望与坚持。
陈六使去世后,陈氏家族继续为公益事业捐资。2010年,陈六使后裔捐资192.2万在大陆设立了公益基金,陈六使的孙子陈锡远为诚毅学院图书馆捐资500万元,这个图书馆被命名为“陈文确陈六使图书馆”。

诚毅学院的陈文确陈六使图书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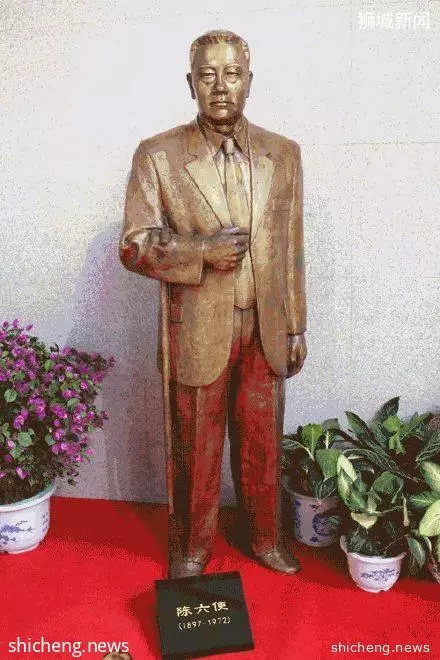
诚毅学院中的陈六使铜像
让我们以陈六使曾经说过的一句话结尾:
“华人曾有自己的文化,绝对不能淘汰,否则身为华人而无华人的文化,虽仍然为华人而不知自己的文化,这种人我们实不知何以名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