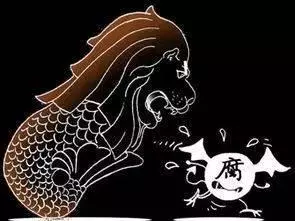
因为新加坡实行高薪养廉制度,官员退休后有一笔十分丰厚的公积金,且资历越老公积金越高,若被查出贪污受贿公积金则全部没收,所有的保障包括医疗费都没有了。这使得新加坡官员违法成本特别高。
规范权力运行执法严厉既表现为“有罪必惩”,也表现为“轻罪重罚”,过去就发生过因索贿50元未成而被判罚款6000元或6周的刑期替代的案例。
不仅于此,新加坡法律实施具有平等性,不论官员的职位多高、权力多大、功劳多大,都必须在法律范围内办事,否则都会受到严厉的处罚。
例如,李光耀的亲密战友、开国元勋郑章远,因被查出受贿50万新币,曾向李光耀求情但遭拒绝,后畏罪自杀。
格林奈曾任新加坡商业事务局局长,在任时一直从事与商业犯罪斗争工作,亲自处理过多起轰动全国的商业刑事案件。但因其先后两次对新加坡银行人士撒谎,引诱他们投资其妻的度假村项目,结果被判“欺骗罪”,受到坐牢、开除公职的处罚,失去了每月1.2万新元工资的职位,并被取消了50万新元的公积金和30万新元的退休金,从此不得再担任公务员,还被律师公会取消了律师资格。
1996年,李光耀父子因购房打折扣的传言,而被提交国会进行了3天的辩论,面对别人的诽谤,李光耀同样需要出庭接受法官的质问并自我澄清。

新加坡前总理李光耀(左)、妻子柯玉芝及儿子李显龙
正如本书所言,在法治建设的过程中,新加坡党和政府的高层领导尤其是李光耀本人把传统与现代性较好地结合了起来。
他在进行国家政权建设和政治斗争时,一方面运用国家政权的力量打击反对派和社会不稳定势力;另一方面在这一过程中尽可能依法行事,运用媒体保持一定程度的行动公开性和透明性,通过司法程序保持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在政治形势稳定后,则积极地进行现代法治建设。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新加坡对高层领导人的制约机制已经建立起来,其司法的独立性已经越来越大,执政党的领导人并不能随意对司法进行干预。
加之政治透明度越来越高,反对党、媒体和公民对政府官员的监督越来越有力,因而其法治建设的成果不可能由于一党长期执政或领袖个人的更替而被破坏。
“体制内”民主化
从经验层面来说,新加坡形成如今独具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与历时半个多世纪的“渐进式”民主化与“体制内”民主化的政治发展过程有关。
“渐进式”民主化是指对政治参与进行严格的限制,在此基础上逐步培育公民意识,并进行制度创新来扩大民主的过程。
与其他国家渐进式民主时断时续,或者有进有退的现象相比较,新加坡的“渐进式”民主化可贵之处在于持续推进,从未间断。
人民行动党在1959年执政后,新加坡经历了一个民主动荡期,这一时期各政党间斗争激烈,工人运动分裂,人民行动党通过镇压各种反对力量,于20世纪60年代末建立起一党独大的威权统治。
经过近三十年快速的经济和社会发展,中产阶级及其多元利益发展起来,进而推动新加坡民主在2011年5月的大选中取得了重要的进展。
在这次大选中,反对党的得票率不仅是自独立以来最高的,接近40%,而且在总共81个国会议席中有6名候选人当选,其中工人党取得了一个集选区的胜利,这相当于取得了一个地方政府的治理权。
这次大选被称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岭,在威权主义体制内孕育出民主的尖尖角。

新加坡大选
这种“渐进式”民主化在客观上有很大的积极效应。它在保证一党威权体制相对稳定的前提下逐步放松管制,释放社会政治、压力。
对民主的培育主要是允许反对党的存在与发展,使媒体越来越中立,允许民众投反对党的票和发表不同的言论,可以直接批评政府的政策。
其中新加坡的集选区制度是体现这一特色的重要的制度创新,它既抑制了政治参与的快速膨胀,也没有打压政治参与,而是通过提高政治参与的门坎来引导有序政治参与,在选民和反对党政治素质不断提高的情况下则促进了政治参与。
“体制内”民主化更是本书对新加坡政治发展道路的创新性发现。
当代世界民主转型的方式可以分为“体制外”和“体制内”两种范式或类型,前者即经典意义上的以“政党轮替”为标志的民主转型,也即以往大多数政体的转型方式,后者则是在民主化新趋势下形成的没有发生政党轮替的民主化方式。
李路曲教授认为,新加坡可称为“体制内”民主化的典型案——威权时期就一直执政的政党仍然执政、国家制度的基本形式没有发生重大变化的情况下,逐步发展起了多党竞争和公平的选举,并把民主治理发展到了较高的水平。
客观而论,相比大多数国家的民主化,“体制内”民主化的路径具有明显的稳定性。
其典型意义还在于,形成这种转型范式的主要因素具有相当的普遍性:
政治现代性积累和内化的程度是民主的基本条件成熟的决定性因素;
党国关系的疏离或紧密程度决定着民主化路径的稳定程度;
体制的复合性、包容性和制度化水平的高低决定着“体制内”民主化发展的程度。
从制度变迁的视角来看,这种结构性替代更加开放和多元,不但受到更为复杂的外部和内部因素的影响,而且应对这些因素的制度也更为开放和多元。
新的制度和新的环境不停地发生交换,进而产生差异化的新的结构性替代,最终结果是,转型不一定会带来剧烈的、断裂式的变迁。
近十年来,“体制内”民主转型已经不是从封建体制向近现代体制的转型,而是在经历了不同政治发展阶段上的数次不完全的转型后,从具有相当现代性的半传统、半现代体制向更现代的体制的转型,因而过去的那种尖锐而激烈的质性的制度对抗已经不复存在。
新加坡的经验表明,“渐进式”民主化与“体制内”民主化转型路径,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抑制转型所带来的无序或暴力,保持政治社会稳定和治理绩效。
执政党也无须因担心失去执政地位而过度地打压民主力量,可以较为主动地推动民主的进程,对各种政治力量来说是一种共赢。
新加坡范式:有节制的民主
美国史丹福大学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败:从工业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书中,系统地探讨了近代以来各政治共同体政治社会运作的机理,提出一个秩序良好的社会需要具备强政府、法治和民主问责三个基本要素。
福山像导师亨廷顿一样,批判了那种认为只要推进现代化就可以提高国家治理水平的论调,认为政治发展顺序非常重要。在进入现代化转型之后,应先建立强势政府而不是大众民主,尚未建立有效统治能力就进行民主化的政府无一例外的会遭受失败。
1980年代以来,“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卷许多发展中国家,但是只有少数国家或地区实现了政治稳定与社会经济的发展,大多数国家都没有实现稳定而有序的发展。
如何处理好政治秩序与政治发展的关系,是后发展国家进行有效治理的根本问题。
新加坡稳定有序的民主进程,对后发展国家有很大的借鉴意义,亦是对福山观点的有力支持。
“渐进式民主”与“体制内民主”的转型方式,可以持续地推进国家治理方式的变革,从而使经济、社会和政治都稳定地向前发展,既没有出现无序状态也没有出现中断或倒退。
虽然新加坡的民主测量指数还未达到欧美民主政体的标准,但是由于其国家治理水平较高,民众的民主权利实现程度也相对较高,新加坡的宪法尽管没有赋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权利,但人们可以充分地享受到宪法和法律所规定的那些不多不少的民主权利。
国防大学课题组在《新加坡发展之路》书中,对新加坡民主模式概括为:
“在保持经济长期快速增长、建成法治社会、构建以中产阶层为主体的社会结构基础上,稳妥、有序地推动了国家从少数人主持的精英政治向精英政治与人民民主政治相结合的方向发展,确保了国家的持续发展和长久繁荣。”
从这个意义上讲,新加坡的民主实质上是一种有节制的民主。新加坡选择这种有节制的民主模式,从深层次说,还是与李光耀早年对自由民主的审慎态度有关。
他在回忆录中谈到,民主治理的关键,首先必须有一群政治参与兴趣浓厚且时刻保持警觉的选民,由他们选举政治家管理国家事务,然后还要通过民意的力量约束他们选举出来的政治家。
其次,一个民主社会必须存在多个讲诚信、有能力的政党,使这个社会在更换领导人时有其他选择。
李光耀因此强调,一人一票的议会民主制,只有人民面临多项选择但能理性选举时方可实现良性运作,永远不会出现最理想的选择:
“好政府取决于由人民选举、对人民负责的代表明智、谨慎且有效地动用这些权力。
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须选择优秀的人担任政府职务。
如果一个民族因为找不到合适的人才运作民主制度,那么无论这个制度多么完美,终将消亡。”
李光耀的审慎与忧虑不是没有道理,作为一种比较成功的现代国家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经验虽然可以超越城市国家与文化界限,但历经半个多世纪的发展,其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特别是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新一代受过良好教育的选民人数不断增加。
他们不同于坚定支持人民行动党的老一代选民,不仅对物价上涨、工资贬值、交通拥挤、组屋申请难等民生问题方面较为敏感,而且也较反感人民行动党“高薪养廉”“高薪揽才”的精英主义。

新一代选民的自由与平等观念日益进步,对执政党认同感不强,反而较为同情反对党,重视对政府权力的监督与制约。
新加坡未来政治体制如何演变,如何平衡民主与民粹的关系,不啻为一个世纪性的制度难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