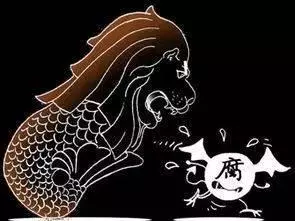
因為新加坡實行高薪養廉制度,官員退休後有一筆十分豐厚的公積金,且資歷越老公積金越高,若被查出貪污受賄公積金則全部沒收,所有的保障包括醫療費都沒有了。這使得新加坡官員違法成本特別高。
規範權力運行執法嚴厲既表現為「有罪必懲」,也表現為「輕罪重罰」,過去就發生過因索賄50元未成而被判罰款6000元或6周的刑期替代的案例。
不僅於此,新加坡法律實施具有平等性,不論官員的職位多高、權力多大、功勞多大,都必須在法律範圍內辦事,否則都會受到嚴厲的處罰。
例如,李光耀的親密戰友、開國元勛鄭章遠,因被查出受賄50萬新幣,曾向李光耀求情但遭拒絕,後畏罪自殺。
格林奈曾任新加坡商業事務局局長,在任時一直從事與商業犯罪鬥爭工作,親自處理過多起轟動全國的商業刑事案件。但因其先後兩次對新加坡銀行人士撒謊,引誘他們投資其妻的度假村項目,結果被判「欺騙罪」,受到坐牢、開除公職的處罰,失去了每月1.2萬新元工資的職位,並被取消了50萬新元的公積金和30萬新元的退休金,從此不得再擔任公務員,還被律師公會取消了律師資格。
1996年,李光耀父子因購房打折扣的傳言,而被提交國會進行了3天的辯論,面對別人的誹謗,李光耀同樣需要出庭接受法官的質問並自我澄清。

新加坡前總理李光耀(左)、妻子柯玉芝及兒子李顯龍
正如本書所言,在法治建設的過程中,新加坡黨和政府的高層領導尤其是李光耀本人把傳統與現代性較好地結合了起來。
他在進行國家政權建設和政治鬥爭時,一方面運用國家政權的力量打擊反對派和社會不穩定勢力;另一方面在這一過程中儘可能依法行事,運用媒體保持一定程度的行動公開性和透明性,通過司法程序保持一定程度的合法性。在政治形勢穩定後,則積極地進行現代法治建設。
而且,更為重要的是,新加坡對高層領導人的制約機制已經建立起來,其司法的獨立性已經越來越大,執政黨的領導人並不能隨意對司法進行干預。
加之政治透明度越來越高,反對黨、媒體和公民對政府官員的監督越來越有力,因而其法治建設的成果不可能由於一黨長期執政或領袖個人的更替而被破壞。
「體制內」民主化
從經驗層面來說,新加坡形成如今獨具特色的民主政治模式,與歷時半個多世紀的「漸進式」民主化與「體制內」民主化的政治發展過程有關。
「漸進式」民主化是指對政治參與進行嚴格的限制,在此基礎上逐步培育公民意識,並進行制度創新來擴大民主的過程。
與其他國家漸進式民主時斷時續,或者有進有退的現象相比較,新加坡的「漸進式」民主化可貴之處在於持續推進,從未間斷。
人民行動黨在1959年執政後,新加坡經歷了一個民主動盪期,這一時期各政黨間鬥爭激烈,工人運動分裂,人民行動黨通過鎮壓各種反對力量,於20世紀60年代末建立起一黨獨大的威權統治。
經過近三十年快速的經濟和社會發展,中產階級及其多元利益發展起來,進而推動新加坡民主在2011年5月的大選中取得了重要的進展。
在這次大選中,反對黨的得票率不僅是自獨立以來最高的,接近40%,而且在總共81個國會議席中有6名候選人當選,其中工人黨取得了一個集選區的勝利,這相當於取得了一個地方政府的治理權。
這次大選被稱為新加坡政治的分水嶺,在威權主義體制內孕育出民主的尖尖角。

新加坡大選
這種「漸進式」民主化在客觀上有很大的積極效應。它在保證一黨威權體制相對穩定的前提下逐步放鬆管制,釋放社會政治、壓力。
對民主的培育主要是允許反對黨的存在與發展,使媒體越來越中立,允許民眾投反對黨的票和發表不同的言論,可以直接批評政府的政策。
其中新加坡的集選區制度是體現這一特色的重要的制度創新,它既抑制了政治參與的快速膨脹,也沒有打壓政治參與,而是通過提高政治參與的門坎來引導有序政治參與,在選民和反對黨政治素質不斷提高的情況下則促進了政治參與。
「體制內」民主化更是本書對新加坡政治發展道路的創新性發現。
當代世界民主轉型的方式可以分為「體制外」和「體制內」兩種範式或類型,前者即經典意義上的以「政黨輪替」為標誌的民主轉型,也即以往大多數政體的轉型方式,後者則是在民主化新趨勢下形成的沒有發生政黨輪替的民主化方式。
李路曲教授認為,新加坡可稱為「體制內」民主化的典型案——威權時期就一直執政的政黨仍然執政、國家制度的基本形式沒有發生重大變化的情況下,逐步發展起了多黨競爭和公平的選舉,並把民主治理髮展到了較高的水平。
客觀而論,相比大多數國家的民主化,「體制內」民主化的路徑具有明顯的穩定性。
其典型意義還在於,形成這種轉型範式的主要因素具有相當的普遍性:
政治現代性積累和內化的程度是民主的基本條件成熟的決定性因素;
黨國關係的疏離或緊密程度決定著民主化路徑的穩定程度;
體制的復合性、包容性和制度化水平的高低決定著「體制內」民主化發展的程度。
從制度變遷的視角來看,這種結構性替代更加開放和多元,不但受到更為複雜的外部和內部因素的影響,而且應對這些因素的制度也更為開放和多元。
新的制度和新的環境不停地發生交換,進而產生差異化的新的結構性替代,最終結果是,轉型不一定會帶來劇烈的、斷裂式的變遷。
近十年來,「體制內」民主轉型已經不是從封建體制向近現代體制的轉型,而是在經歷了不同政治發展階段上的數次不完全的轉型後,從具有相當現代性的半傳統、半現代體制向更現代的體制的轉型,因而過去的那種尖銳而激烈的質性的制度對抗已經不復存在。
新加坡的經驗表明,「漸進式」民主化與「體制內」民主化轉型路徑,可以在相當程度上抑制轉型所帶來的無序或暴力,保持政治社會穩定和治理績效。
執政黨也無須因擔心失去執政地位而過度地打壓民主力量,可以較為主動地推動民主的進程,對各種政治力量來說是一種共贏。
新加坡範式:有節制的民主
美國史丹福大學的弗朗西斯·福山在2014年出版的《政治秩序和政治衰敗:從工業革命到民主全球化》一書中,系統地探討了近代以來各政治共同體政治社會運作的機理,提出一個秩序良好的社會需要具備強政府、法治和民主問責三個基本要素。
福山像導師亨廷頓一樣,批判了那種認為只要推進現代化就可以提高國家治理水平的論調,認為政治發展順序非常重要。在進入現代化轉型之後,應先建立強勢政府而不是大眾民主,尚未建立有效統治能力就進行民主化的政府無一例外的會遭受失敗。
1980年代以來,「第三波」民主化浪潮席捲許多發展中國家,但是只有少數國家或地區實現了政治穩定與社會經濟的發展,大多數國家都沒有實現穩定而有序的發展。
如何處理好政治秩序與政治發展的關係,是後發展國家進行有效治理的根本問題。
新加坡穩定有序的民主進程,對後發展國家有很大的借鑑意義,亦是對福山觀點的有力支持。
「漸進式民主」與「體制內民主」的轉型方式,可以持續地推進國家治理方式的變革,從而使經濟、社會和政治都穩定地向前發展,既沒有出現無序狀態也沒有出現中斷或倒退。
雖然新加坡的民主測量指數還未達到歐美民主政體的標準,但是由於其國家治理水平較高,民眾的民主權利實現程度也相對較高,新加坡的憲法儘管沒有賦予人民充分的民主權利,但人們可以充分地享受到憲法和法律所規定的那些不多不少的民主權利。
國防大學課題組在《新加坡發展之路》書中,對新加坡民主模式概括為:
「在保持經濟長期快速增長、建成法治社會、構建以中產階層為主體的社會結構基礎上,穩妥、有序地推動了國家從少數人主持的精英政治向精英政治與人民民主政治相結合的方向發展,確保了國家的持續發展和長久繁榮。」
從這個意義上講,新加坡的民主實質上是一種有節制的民主。新加坡選擇這種有節制的民主模式,從深層次說,還是與李光耀早年對自由民主的審慎態度有關。
他在回憶錄中談到,民主治理的關鍵,首先必須有一群政治參與興趣濃厚且時刻保持警覺的選民,由他們選舉政治家管理國家事務,然後還要通過民意的力量約束他們選舉出來的政治家。
其次,一個民主社會必須存在多個講誠信、有能力的政黨,使這個社會在更換領導人時有其他選擇。
李光耀因此強調,一人一票的議會民主制,只有人民面臨多項選擇但能理性選舉時方可實現良性運作,永遠不會出現最理想的選擇:
「好政府取決於由人民選舉、對人民負責的代表明智、謹慎且有效地動用這些權力。
要想建立高效的政府,你必須選擇優秀的人擔任政府職務。
如果一個民族因為找不到合適的人才運作民主制度,那麼無論這個制度多麼完美,終將消亡。」
李光耀的審慎與憂慮不是沒有道理,作為一種比較成功的現代國家治理模式,新加坡的經驗雖然可以超越城市國家與文化界限,但歷經半個多世紀的發展,其也面臨著新的挑戰。
特別是從上世紀80年代開始,新一代受過良好教育的選民人數不斷增加。
他們不同於堅定支持人民行動黨的老一代選民,不僅對物價上漲、工資貶值、交通擁擠、組屋申請難等民生問題方面較為敏感,而且也較反感人民行動黨「高薪養廉」「高薪攬才」的精英主義。

新一代選民的自由與平等觀念日益進步,對執政黨認同感不強,反而較為同情反對黨,重視對政府權力的監督與制約。
新加坡未來政治體制如何演變,如何平衡民主與民粹的關係,不啻為一個世紀性的制度難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