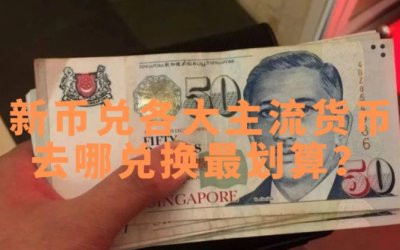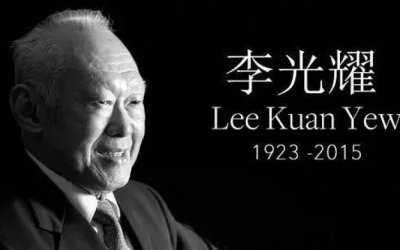编者按:新加坡即将迎来一次看似无风无浪、实则暗流汹涌的大选。执政长达60年的人民行动党(PAP)从未真正输过,但这一届选举,却将是其新一代领袖黄循财的试金石。在全球秩序剧变、民生压力激增、在野势力蠢蠢欲动的背景下,表面的“稳如磐石”背后,掩藏着选民情绪的悄然转变。本文尝试剖开这座“模范城市国家”的政治肌理,看清政权更迭前夜的不安与可能。
核心提要:
1.选情稳中藏变,得票率成风向标:本次大选虽无悬念地由人民行动党继续执政,但黄循财能否以高票赢得“政治继承权”,成为检验其号召力与党内团结的关键。跌破60%的得票线,将被视为民意警告。
2.制度设计引发在野党不满:在野党痛批选举制度不公,从高额押金到超短竞选期、不断调整的选区划分都被质疑为“制度性封锁”。对制度信任的缺口,正逐渐转化为选票行为的微妙游移。
3.经济压力蔓延至选票意向:物价飞涨、组屋高企与生活成本压力,令不少新加坡人产生“纸面富裕感”下的实际窘迫。尽管政府派发补贴,选民是否买账,或将反映在选票上。
4.在野党虽弱,却有议会扩张空间:即使在野阵营无法撼动PAP执政地位,但选区布局变化与公众情绪波动,为他们争取更多议席提供了可能。工人党与进步党成为最具代表性的观察对象。
5.危机政治话术面临挑战:执政党一再诉诸“全球动荡论”与“稳定压倒一切”的话术,但选民对此叙事的耐心正在耗尽。黄循财时代是否能跳出李氏家族的危机论老路,尚待观察。
一场风平浪静的大选,还是一场无声的抗议?
新加坡政坛素有一句老话:乱世之中,选民求稳。这句政治箴言,曾为人民行动党(PAP)在长达六十载的执政生涯中屡试不爽。但今时不同往日,眼下人们关注的,不再是PAP能否取胜,而是它还能赢得几分风光。
5月3日,全国选民将走进投票站,选出新一届国会。新任总理黄循财,是六十年来第四位国家领导人,也是在李光耀家族之外继李显龙之后的又一位总理。他此役力求争取压倒性支持,引领这个高度依赖全球贸易的小国,应对一个动荡不安的新世界。次选举共有97个议席开放角逐,其中5席因无竞争对手自动当选,投票为强制义务。
胜选不代表认同:PAP的“选票焦虑症”
表面看似大胜,也未必高枕无忧。2020年,PAP虽夺下89%的议席,却只拿下61%的选票,创下历史低点,引发党内深度反思。此后,该党收紧部分外籍劳工准入政策,放宽年轻人购屋资格,并废除禁止男同性性行为的旧法条,却仍执意两次提高消费税。

那场选举揭示了一个不容回避的趋势:人民行动党的得票率在过去二十余年中持续下滑,虽然2015年短暂回升;而“自动当选”的选区也大幅减少。如今反对党阵营,正以更积极的姿态布局全国。正如前PAP议员辛格所言:“这将是一场标志性选举。若得票率跌破六成,便是PAP必须转变的信号。”
倘若执政党成绩不理想,最有望崛起的便是工人党。他们主张让年轻未婚者更容易获得组屋,对最富有的1%征收财富税,并设定15%的企业最低税率。

而PAP想再续过去六十年的辉煌,已非易事。当今选民更渴望多元声音,政治血统的加持亦不再神圣。新加坡,这个从殖民港口一跃成为金融和贸易重镇的国家,正在步入不确定的新纪元。
吃饭、养老、未来感:选民的不安谁来安抚?
人民行动党为国家赢得了物质上的奇迹:世界一流的生活水准、现代高效的医疗与交通系统、以及覆盖九成国民的住房政策。但这一切无法抵御全球浪潮来袭。
眼下,高企的食品、房地产和汽车价格,让民众倍感压力。黄循财则大手笔动用国家储备资金,扩展社会保障网,为餐饮、交通、养老等方面注入补贴——而这,是否足以稳住政权地基,还有待选票揭晓。
尽管人民行动党(PAP)在疫情期间投入大量财政资源加强社会保障,新加坡选民面临的现实压力仍未缓解。与2020年上一次大选相比,目前消费价格平均上涨了17%。这种通胀激增的局面,令人回想起2011年PAP得票率跌至历史低点时的情况——那也是因民生问题激起选民不满的一年。公共住房价格也飙升,组屋成本节节攀升。

对手不是不努力,是选制太“巧妙”
在野阵营由大约十个不同政党组成,虽然力量分散,但他们正希望在上届选举取得的有限战果上更进一步。反对党普遍认为,PAP在设定选举规则方面拥有“结构性优势”。
角逐15个议席的反对党“红点同心党”领导人拉维·菲利蒙指出:“选举制度本身的设计存在严重不公。”"在野党批评的焦点包括:选举缺乏独立机构监管,候选人参选需缴纳五位数新元押金(每人13,500新元,相当于普通工薪族两个月薪资),以及全球最短之一的竞选期——今年仅限九天。
更具争议的还有选区划分方式。新加坡的选区划界常在每届大选前发生巨大变动,有些选区甚至直接被“消失”。今年,就有部分选民在过去五次选举中已进入第四个不同的选区。选举局表示,选区调整是根据人口迁移与新区开发作出的合理反映。而反对党则称之为“选区操弄”(gerrymandering)。
这正是资深反对派人物徐顺全(Chee Soon Juan)所面临的困境。自1992年起,徐多次参选未果,一直在西部的武吉巴督(Bukit Batok)选区深耕,向选民宣传、在熟食中心派发传单。他2016年首次代表该区参选时赢得约39%选票,2020年更将得票率提高至45%,仅略逊于PAP候选人。

然而,今年3月的一个周日,当徐顺全站在媒体面前宣布再次参选时,情绪明显低落。就在不到两周前,他精心准备多年的单议席选区武吉巴督,已被合并入一个较大的集选区,从选区地图上消失了。
“我们没有其他选择了。”徐无奈地将战线北移,六周后将在新选区出战。“这样的划界过程不透明,而且极度令人沮丧。你几乎得从头再来。”
GRC制度:保障多元,还是排他护城河?
在新加坡,集选区(Group Representation Constituencies,简称GRC)制度长期以来为反对党所诟病。在这些多议席选区中,每个政党需组成最多五人的团队参选,才能角逐议席。每位候选人需缴纳13,500新元押金,使得组织完整候选队伍的成本高昂。
此外,选区划分工作由由总理办公室任命的公务员组成的委员会负责,选举局本身也隶属于总理办公室,而该委员会主席正是一位总理秘书。反对党质疑这种结构本身存在“监督缺失”和权力集中。
对此,政府与执政党回应称,集选区制度的初衷是保障议会的多元种族代表性,确保少数族群权益受到充分体现。至于高额押金与短暂竞选期,政府表示此举旨在筛选“真正有意愿认真参选的人”,同时不会构成真正的门槛。
“自独立以来,新加坡一直举办自由与公正的选举,”政府在回应彭博社提问时表示,“集选区制度保证了议会始终具备多元种族代表性,避免政治走向族群对立。”
对于PAP而言,集选区还提供了另一个优势:可让经验丰富的政坛老将“带飞”新人候选人。新手只需作为团队一员参选,即可借势上位。本届选举中,已有一个五人集选区无人竞争,PAP自动获得全部五席。在其他多数集选区中,PAP也继续采取“资深带新人”组合策略,试图在平稳过渡中保持优势。
危机论还能续命多久?
在野党同时也批评政府在选举年份大幅增加开支,认为这实质上是“用钱换选票”。前总统候选人、现任新加坡前进党(Progress Singapore Party)主席陈清木(Tan Cheng Bock)更直言,执政党一再强调全球贸易战的冲击,是“在用恐惧操纵选民”。
而总理黄循财则坚称,这些新增财政开支只是“临时援助措施”,占整个预算的比例很小。他在多个场合公开强调,全球贸易战所带来的不确定性正急剧上升,可能对高度依赖贸易的新加坡构成实质威胁。政府近期已将2025年经济增长预期从原本的1%-3%下调至0%-2%。

“我们曾经所熟悉的、可预测、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正在消失。”52岁的黄循财在4月初发出警告,“我们正迈入一个更加动荡的时代——各种冲击将更频繁、更难预料。”
执政党显然不是毫无忧虑。在特朗普掀起全球关税风暴之前,从法国、阿根廷到印度,多国选民早已在选票中对现任政权表达不满。
即便如此,即便“反现任情绪”在新加坡达到顶峰,在现有制度下,反对党也难以凭一己之力打破PAP在国会的超级多数地位。眼下实力最强的工人党,仅在不到三分之一的选区提出候选人。
不过,黄循财在公开场合释放的信息很清晰——他并未掉以轻心。
“看看过去一年世界各地的选举结果你就会明白——现任执政党不是被推翻,就是遭遇重大挫败。”他本月表示,“我们绝不能想当然地认为,只因人民行动党已执政数十年,就一定能自动赢得选民支持。”
(本文译者:李林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