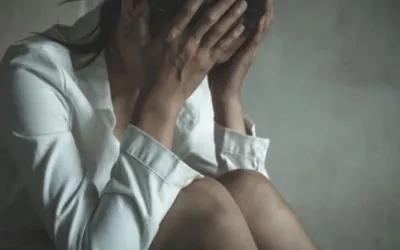美国总统特朗普近期对全球多国征收全面关税的举措,正在引发远超经济领域的连锁反应。新加坡总理兼财政部长黄循财(Lawrence Wong)4月8日在国会发表重磅演讲,直指美国此举可能颠覆二战后建立的全球贸易秩序,并警告称“不稳定的保护主义比保护主义本身更危险”。
他强调,新加坡将联合国内企业与工会成立专项行动小组应对冲击,同时呼吁通过多边框架解决争端。
美国关税政策违背“对等”原则
新加坡表达强烈失望

黄循财在国会演讲中首先驳斥了美国以“贸易对等”为由加征关税的合理性。他指出,新加坡与美国之间存在自由贸易协定,且新加坡从美国进口的货物远多于对美出口,若严格遵循“对等”逻辑,美国不应向新加坡征收关税。
然而,美国仍单方面对新加坡施加10%的关税,黄循财直言:“这不是对朋友应有的行为。”他进一步分析称,美国关税政策的矛头本应指向对美贸易顺差国家,但新加坡并非此类经济体。
数据显示,美国在服务贸易领域(如软件、教育、金融)对全球多数国家保持顺差,而货物贸易逆差仅反映美国消费者的购买偏好,并非不公平竞争的证明。
深层矛盾:美国对世贸体系的不满
黄循财认为,美国此举源于其对中国加入世贸组织后的长期不满,认为中国通过补贴企业和限制市场准入“不公平竞争”。但他强调,中美争端应通过世贸组织框架解决,而非单边行动破坏多边规则。
关税冲击全球经济
新加坡成立专项小组应对
美国关税政策已引发全球市场震荡。黄循财透露,新加坡将成立由副总理兼贸工部长颜金勇领导的“贸易韧性行动小组”,成员包括工商联合总会、全国雇主联合会和职工总会,其核心目标在于协助企业和员工有效应对当前的不确定性。

黄英贤总理表示,在美国关税宣布后,新加坡的经济机构迅速行动,与多家跨国企业及当地企业取得了联系。从反馈来看,即便是那些并未直接受到关税冲击的企业,也普遍担忧客户需求会随之减弱。受此影响,一些公司在评估关税的全面影响期间,搁置了新项目的推进计划。
短期影响与风险预警
经济增速下调:新加坡政府正重新评估2025年1%-3%的经济增长预测,可能因外部需求萎缩而下调。
行业冲击:制造业、批发贸易、交通和金融等外向型领域首当其冲,部分企业已暂停新项目投资。
就业压力:经济放缓可能导致裁员增加,工资增长停滞。
黄循财表示,2025年财政预算案中的措施(如邻里购物券、水电费回扣)已为家庭提供短期缓冲,与此同时,政府也通过社区关怀计划(ComCare)为弱势群体提供针对性的援助措施。但长期需警惕全球保护主义蔓延。
世贸规则遭破坏
小国面临边缘化危机
黄循财指出,美国关税政策直接否定了世贸组织“最惠国待遇”原则,该原则要求成员国平等对待所有贸易伙伴。
美国的这一轮关税上调可能只是全球进一步上调关税的开始,若其他国家效仿美国,基于规则的贸易体系将瓦解,而小国因缺乏议价能力将沦为大国博弈的牺牲品。

历史教训:1930年《斯穆特—霍利关税法》的阴影
黄循财总理提到 1930 年美国通过《斯穆特 - 霍利法案》全面提高关税,当时许多国家提出抗议,部分国家还进行了贸易限制和关税报复,这一行为加深并延长了大萧条。
对比当下,他指出如今的风险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大。若美国新关税完全颁布,其关税水平将高于《斯穆特 - 霍利法案》时期。而且,与 1930 年代相比,现今贸易在美国和全球经济中所占比重更大,供应链联系也更为紧密。所以,当下贸易流动的任何中断,都将对世界产生更广泛的连锁反应。
美国新关税或为谈判工具但影响深远
一些人认为新关税是美国在其他领域取得让步的谈判工具,如同 1971 年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对进口商品征收 10% 附加费,以此迫使德国和日本货币贬值,达成目的后关税取消。
虽然目前各国有短暂谈判窗口,有可能使美国降低一些税率,但黄循财总理强调必须现实看待。
他指出一旦贸易壁垒上升,往往很难撤销,即便最初设置壁垒的理由不再成立。而且,如此剧烈举措所产生的不确定性会抑制信心和增长,要恢复到以前的状态将极为困难。
尤其是美国此次 10% 的统一税率看似没有谈判余地,像是固定的最低关税,不考虑各国贸易差额或与美国现有贸易安排。
改革而非颠覆
多边体系的出路
黄循财重申,全球经济体系需改革而非推翻。新加坡正与理念相近国家合作,推动世贸组织机制现代化,解决补贴、数字贸易等新议题。他呼吁美国重返多边谈判桌:“单边行动只会让所有人付出代价。”
本周东盟经济部长将举行特别会议。他指出:“他们将围绕东盟进一步合作展开讨论,探索加强东盟内部贸易的方式,同时发出东盟坚定致力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的强烈信号。东盟也会与理念契合的伙伴,在互惠互利的领域强化联系。”
在东盟区域之外,黄总理表示已与英国新首相斯塔默取得联系,并且在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还将与其他国家领导人进行通话。众多国家都期望能与新加坡在经济、数码以及绿色经济等方面拓展合作。
面对美国的保护主义政策,新加坡将积极寻求与其他伙伴并肩协作,共同应对当下的挑战。一方面,努力确保多边体系持续保持韧性;另一方面,为未来可能出现的全新且不同的全球体系筑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