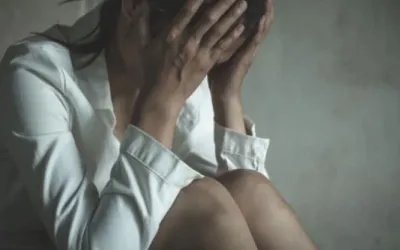美國總統特朗普近期對全球多國徵收全面關稅的舉措,正在引發遠超經濟領域的連鎖反應。新加坡總理兼財政部長黃循財(Lawrence Wong)4月8日在國會發表重磅演講,直指美國此舉可能顛覆二戰後建立的全球貿易秩序,並警告稱「不穩定的保護主義比保護主義本身更危險」。
他強調,新加坡將聯合國內企業與工會成立專項行動小組應對衝擊,同時呼籲通過多邊框架解決爭端。
美國關稅政策違背「對等」原則
新加坡表達強烈失望

黃循財在國會演講中首先駁斥了美國以「貿易對等」為由加征關稅的合理性。他指出,新加坡與美國之間存在自由貿易協定,且新加坡從美國進口的貨物遠多於對美出口,若嚴格遵循「對等」邏輯,美國不應向新加坡徵收關稅。
然而,美國仍單方面對新加坡施加10%的關稅,黃循財直言:「這不是對朋友應有的行為。」他進一步分析稱,美國關稅政策的矛頭本應指向對美貿易順差國家,但新加坡並非此類經濟體。
數據顯示,美國在服務貿易領域(如軟體、教育、金融)對全球多數國家保持順差,而貨物貿易逆差僅反映美國消費者的購買偏好,並非不公平競爭的證明。
深層矛盾:美國對世貿體系的不滿
黃循財認為,美國此舉源於其對中國加入世貿組織後的長期不滿,認為中國通過補貼企業和限制市場准入「不公平競爭」。但他強調,中美爭端應通過世貿組織框架解決,而非單邊行動破壞多邊規則。
關稅衝擊全球經濟
新加坡成立專項小組應對
美國關稅政策已引發全球市場震盪。黃循財透露,新加坡將成立由副總理兼貿工部長顏金勇領導的「貿易韌性行動小組」,成員包括工商聯合總會、全國僱主聯合會和職工總會,其核心目標在於協助企業和員工有效應對當前的不確定性。

黃英賢總理表示,在美國關稅宣布後,新加坡的經濟機構迅速行動,與多家跨國企業及當地企業取得了聯繫。從反饋來看,即便是那些並未直接受到關稅衝擊的企業,也普遍擔憂客戶需求會隨之減弱。受此影響,一些公司在評估關稅的全面影響期間,擱置了新項目的推進計劃。
短期影響與風險預警
經濟增速下調:新加坡政府正重新評估2025年1%-3%的經濟增長預測,可能因外部需求萎縮而下調。
行業衝擊:製造業、批發貿易、交通和金融等外向型領域首當其衝,部分企業已暫停新項目投資。
就業壓力:經濟放緩可能導致裁員增加,工資增長停滯。
黃循財表示,2025年財政預算案中的措施(如鄰里購物券、水電費回扣)已為家庭提供短期緩衝,與此同時,政府也通過社區關懷計劃(ComCare)為弱勢群體提供針對性的援助措施。但長期需警惕全球保護主義蔓延。
世貿規則遭破壞
小國面臨邊緣化危機
黃循財指出,美國關稅政策直接否定了世貿組織「最惠國待遇」原則,該原則要求成員國平等對待所有貿易夥伴。
美國的這一輪關稅上調可能只是全球進一步上調關稅的開始,若其他國家效仿美國,基於規則的貿易體系將瓦解,而小國因缺乏議價能力將淪為大國博弈的犧牲品。

歷史教訓:1930年《斯穆特—霍利關稅法》的陰影
黃循財總理提到 1930 年美國通過《斯穆特 - 霍利法案》全面提高關稅,當時許多國家提出抗議,部分國家還進行了貿易限制和關稅報復,這一行為加深並延長了大蕭條。
對比當下,他指出如今的風險在某些方面可能更大。若美國新關稅完全頒布,其關稅水平將高於《斯穆特 - 霍利法案》時期。而且,與 1930 年代相比,現今貿易在美國和全球經濟中所占比重更大,供應鏈聯繫也更為緊密。所以,當下貿易流動的任何中斷,都將對世界產生更廣泛的連鎖反應。
美國新關稅或為談判工具但影響深遠
一些人認為新關稅是美國在其他領域取得讓步的談判工具,如同 1971 年美國總統理察・尼克森對進口商品徵收 10% 附加費,以此迫使德國和日本貨幣貶值,達成目的後關稅取消。
雖然目前各國有短暫談判窗口,有可能使美國降低一些稅率,但黃循財總理強調必須現實看待。
他指出一旦貿易壁壘上升,往往很難撤銷,即便最初設置壁壘的理由不再成立。而且,如此劇烈舉措所產生的不確定性會抑制信心和增長,要恢復到以前的狀態將極為困難。
尤其是美國此次 10% 的統一稅率看似沒有談判餘地,像是固定的最低關稅,不考慮各國貿易差額或與美國現有貿易安排。
改革而非顛覆
多邊體系的出路
黃循財重申,全球經濟體系需改革而非推翻。新加坡正與理念相近國家合作,推動世貿組織機制現代化,解決補貼、數字貿易等新議題。他呼籲美國重返多邊談判桌:「單邊行動只會讓所有人付出代價。」
本周東協經濟部長將舉行特別會議。他指出:「他們將圍繞東協進一步合作展開討論,探索加強東協內部貿易的方式,同時發出東協堅定致力於推動區域經濟一體化的強烈信號。東協也會與理念契合的夥伴,在互惠互利的領域強化聯繫。」
在東協區域之外,黃總理表示已與英國新首相斯塔默取得聯繫,並且在接下來的幾個星期,還將與其他國家領導人進行通話。眾多國家都期望能與新加坡在經濟、數碼以及綠色經濟等方面拓展合作。
面對美國的保護主義政策,新加坡將積極尋求與其他夥伴並肩協作,共同應對當下的挑戰。一方面,努力確保多邊體系持續保持韌性;另一方面,為未來可能出現的全新且不同的全球體系築牢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