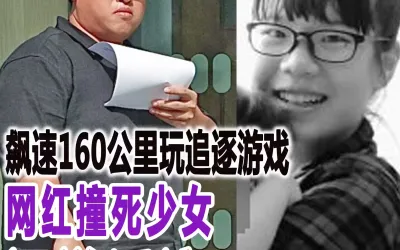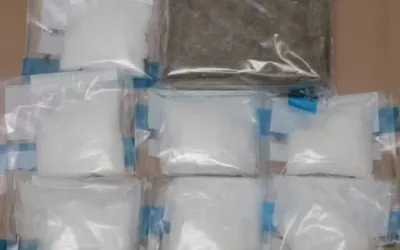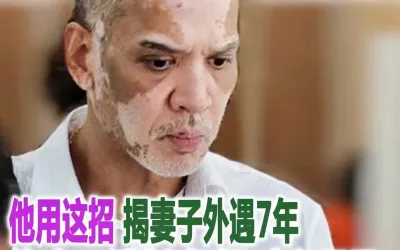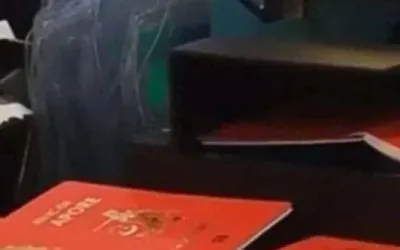黄玉山提到,位于海军部(Admiralty)地铁站附近的新型住宅形态——海军部村庄(Kampung Admiralty),为了满足养老需求,医疗养老机构被引入站城一体空间中。但政府只给这些机构运营者30年牌照,目的是应对将来可能出现的人口结构变化。
“这样做的好处是,让运营商也能提前了解到30年后可能出现的状况,提前做好准备。毕竟,如果他们没有根据实际情况作出改变,也可能会面临顾客减少、营收恶化的情况。”
步行城市,打通“最后一公里”
然而,并不是每个城市都能效仿新加坡的高投入模式。而且,新加坡轨道交通在通达性上,依然存在改善空间。
在新加坡,高投入是其维持城市高水平发展的先决条件。为改善地铁运营和提供更好服务,LTA近几年逐渐将地铁营运资产从SBS与SMRT两家公司回收,以新地铁融资框架(New Rail Financing Framework)方式,将更多主动权握在自己手上。
据麦景昇介绍,LTA不希望运营公司太过考虑盈利导向的运营方式,因为新加坡地铁也开始面临老化问题,由于顾及成本,运营公司通常不愿支付巨额费用来维修或提升相关设备和系统。目前,新加坡地铁的目标仅仅是实现“车票收入覆蓋运营成本”。
即便在这种高投入情况下,新加坡轨道交通的连接性仍没有做到尽善尽美。
在新加坡旅游,打车仍然是更便捷的交通方式。在新加坡生活数十年的顾清扬也承认,在“最后一公里”问题上,新加坡仍有改善空间——他每天从家到学校上班,在地铁上花费的时间与从地铁站走路到学校花费的时间几乎相当。
根据2013年《陆路交通总体规划》,到2030年,新加坡将力求每10户居民中有8户居住在距离地铁站步行10分钟以内的区域。与此同时,地铁里程数将从现在的240公里增至360公里。显而易见,这项新规划在着手解决“最后一公里”问题的同时,也意味着新加坡需要投入更多资金。
造成这种问题的一个原因是,在解决到达性问题时,新加坡主要是从地铁本身来考虑,骑行、步行系统仅是补充。尽管步行城市的目标已被写入新一轮城市总规中,但在新加坡实际操作中,这种对路权的再分配,还处于试点阶段。

图片来源:摄图网
比如,在为数不多位于主城区的试点——明古连(Bencoolen)地铁站附近,仅一个街区采用了车道让位于骑行与步行道的规划,不仅前后缺乏连接,且路段内自行车与共享单车供给也有限。
新加坡社科院经济学副教授Walter Edgar Theseira指出,这已经引发新加坡的反思——长期以来,新加坡只通过规划地铁线路来解决连通性问题,私营公交、慢行系统等方式被局限在很小的范围内。
基于此,步行城市的目标对于新加坡而言,将是一个庞大工程。在现有明古连试点的础上,新加坡还将开辟更多步行和骑行专用路径,从而形成覆蓋全新加坡的网络。
在麦景昇看来,通过打造慢行系统增加TOD辐射范围的同时,也能在全社会强化一种新思维方式。“这是一个信心的问题。”他说,“地铁成网后能够产生‘网络效应’(network effect),市民出行的第一反应就是轨道交通。由此出发,全社会在寻求发展时,会更加关注TOD这种更可持续的模式。”
眼下,新加坡政府也开始引入更多地产商和规划者共同进行TOD城市开发,解决财政高投入高补贴问题,让地产商在通盘规划时有更大灵活性和自主权。
此外,新加坡还尝试用更多方法进一步提高地铁使用率。比如,与横贯南北的轨道优先走廊相匹配的是,机动车道被移至地下,地面则用于公交车、自行车与行人通行。更加“行人友好”的环境下,轨道交通的重要性也会得到空前提升。
把轨道交通刻进城市“基因”里——这是许多与麦景昇一样的规划者,对新加坡未来的共同期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