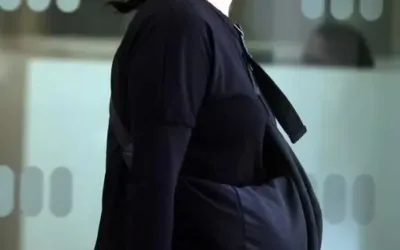黃玉山提到,位於海軍部(Admiralty)地鐵站附近的新型住宅形態——海軍部村莊(Kampung Admiralty),為了滿足養老需求,醫療養老機構被引入站城一體空間中。但政府只給這些機構運營者30年牌照,目的是應對將來可能出現的人口結構變化。
「這樣做的好處是,讓運營商也能提前了解到30年後可能出現的狀況,提前做好準備。畢竟,如果他們沒有根據實際情況作出改變,也可能會面臨顧客減少、營收惡化的情況。」
步行城市,打通「最後一公里」
然而,並不是每個城市都能效仿新加坡的高投入模式。而且,新加坡軌道交通在通達性上,依然存在改善空間。
在新加坡,高投入是其維持城市高水平發展的先決條件。為改善地鐵運營和提供更好服務,LTA近幾年逐漸將地鐵營運資產從SBS與SMRT兩家公司回收,以新地鐵融資框架(New Rail Financing Framework)方式,將更多主動權握在自己手上。
據麥景昇介紹,LTA不希望運營公司太過考慮盈利導向的運營方式,因為新加坡地鐵也開始面臨老化問題,由於顧及成本,運營公司通常不願支付巨額費用來維修或提升相關設備和系統。目前,新加坡地鐵的目標僅僅是實現「車票收入覆蓋運營成本」。
即便在這種高投入情況下,新加坡軌道交通的連接性仍沒有做到盡善盡美。
在新加坡旅遊,打車仍然是更便捷的交通方式。在新加坡生活數十年的顧清揚也承認,在「最後一公里」問題上,新加坡仍有改善空間——他每天從家到學校上班,在地鐵上花費的時間與從地鐵站走路到學校花費的時間幾乎相當。
根據2013年《陸路交通總體規劃》,到2030年,新加坡將力求每10戶居民中有8戶居住在距離地鐵站步行10分鐘以內的區域。與此同時,地鐵里程數將從現在的240公里增至360公里。顯而易見,這項新規劃在著手解決「最後一公里」問題的同時,也意味著新加坡需要投入更多資金。
造成這種問題的一個原因是,在解決到達性問題時,新加坡主要是從地鐵本身來考慮,騎行、步行系統僅是補充。儘管步行城市的目標已被寫入新一輪城市總規中,但在新加坡實際操作中,這種對路權的再分配,還處於試點階段。

圖片來源:攝圖網
比如,在為數不多位於主城區的試點——明古連(Bencoolen)地鐵站附近,僅一個街區採用了車道讓位於騎行與步行道的規劃,不僅前後缺乏連接,且路段內自行車與共享單車供給也有限。
新加坡社科院經濟學副教授Walter Edgar Theseira指出,這已經引發新加坡的反思——長期以來,新加坡只通過規劃地鐵線路來解決連通性問題,私營公交、慢行系統等方式被局限在很小的範圍內。
基於此,步行城市的目標對於新加坡而言,將是一個龐大工程。在現有明古連試點的礎上,新加坡還將開闢更多步行和騎行專用路徑,從而形成覆蓋全新加坡的網絡。
在麥景昇看來,通過打造慢行系統增加TOD輻射範圍的同時,也能在全社會強化一種新思維方式。「這是一個信心的問題。」他說,「地鐵成網後能夠產生『網絡效應』(network effect),市民出行的第一反應就是軌道交通。由此出發,全社會在尋求發展時,會更加關注TOD這種更可持續的模式。」
眼下,新加坡政府也開始引入更多地產商和規劃者共同進行TOD城市開發,解決財政高投入高補貼問題,讓地產商在通盤規劃時有更大靈活性和自主權。
此外,新加坡還嘗試用更多方法進一步提高地鐵使用率。比如,與橫貫南北的軌道優先走廊相匹配的是,機動車道被移至地下,地面則用於公交車、自行車與行人通行。更加「行人友好」的環境下,軌道交通的重要性也會得到空前提升。
把軌道交通刻進城市「基因」里——這是許多與麥景昇一樣的規劃者,對新加坡未來的共同期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