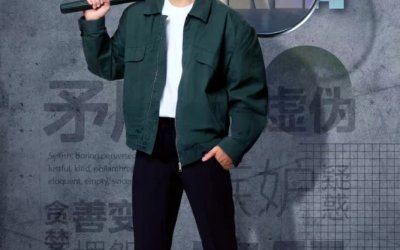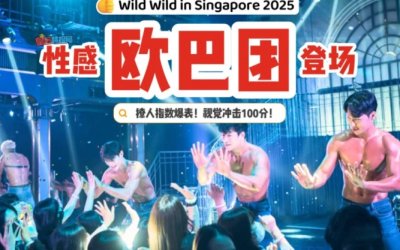1965年,有记者问,新加坡是否会和与马来西亚不合的印度尼西亚建立外交关系时,李光耀饶舌地答道:我们希望同马来西亚友好,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必须和所有对马来西亚不友好的国家也不友好。马来西亚的朋友可以是我们的朋友,但马来西亚的敌人不一定就是我们的敌人。他的潜台词是:“首先必须记住的是新加坡是个小国,不能在建构东南亚的历史进程中有多大贡献。老虎们打架时,小羊参加进去是自找麻烦。”

对中政策是一个典型的例子。1975年与来访的泰国首相库立会谈时,李光耀透露自己的担忧和难处:“我所关注的是,中国在马来亚和印尼共产党成立纪念日发给他们的贺词。这些贺词在吉隆坡和雅加达激起强烈的反感和憎恶,我不希望因为自己和周恩来有同样的血统,而使这种情绪转而针对我。”
李光耀竭力洗清新加坡“第三中国”,或是“第五纵队”的嫌疑。70年代,他与印尼总统苏哈托见面,专门向他解释新加坡华族观众在印尼与中国的羽毛球赛中为中国队喝彩一事。“我说久而久之新加坡华人在思想意识上将会变成新加坡人,这样的看法他接受了。”在决定同中国互设商务代表办事处之前,李光耀亲自向苏哈托通告了情况。他强调这不过是为了促进贸易,不等同于外交层次上的代表性,以获得印尼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李光耀向印尼承诺:新加坡不会赶在印尼之前同中国建交。说到做到,“印尼在1990年8月与中国恢复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国建立外交关系”。
李光耀搁置了与马来西亚、印尼的政治矛盾,但是,当他的政府在世界范围内寻找商业机会、试图扭转生存危机时,另一个事关生死的问题是他所不能回避的:对于那些在东南亚上方投下影子的大国,新加坡的立场究竟是什么?
战后民族国家普遍存在一股反对大国、排斥大国影响的思潮。大多数东南亚政治家相信,在一个全新的时代里,他们可以决定自己国家的命运。但李光耀有不同的看法:“在新加坡独立不久,我们认定,小国不能依靠自身的经济、政治和军事力量生存,从一开始我们就决定加入国际体系,把我们的未来托付给国际体系。”
新加坡人将他们实用主义的商业逻辑并行不悖地用在了外交上。1976年,拉惹勒南外长在曼谷有过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讲话。他说:“我们认为大国的存在以及他们之间的竞争是国际政治中永恒的事实,只要民族国家存在,就会有国家实力的层次区别,一些国家比另一些国家更强大,所有国家都竞相扩大自己的势力和影响。我们不赞成现在的流行观点,认为大国力量是邪恶的、危险的、不道德的,其实大国在这些方面表现得并不比小国多多少,大国与小国的唯一不同是在必要的时候,大国有足够的资源和技术实施他们的诡计。大量事实证明,一些不大的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威逼、威胁、伤害比它们更弱的国家时也是毫不犹豫的。新加坡接受大国存在以及大国在东南亚竞争的现实……如果在本地区没有大国的竞争,我们可能要面对更难处理的权力争夺。”
新加坡打算如何做?拉惹勒南说:“如果跨国公司来新加坡只是单纯地为了赚钱,那么它们一点都不危险;如果它们带着政治目的来,那就是危险的。为什么以及什么时候跨国公司会由赚钱转向玩政治呢?在它们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时候。所以我们必须公平对待它们。”同样道理:“在国际政治中,我们避免卷入大国争斗,而是主张所有大国都存在于本地区。如果你说要这个大国在这里,其他大国走开,那么你就不可避免地被卷进大国政治。”
新加坡摆明开门做生意的态度。且不论“冷战”时期,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像李光耀那样在大国之间游刃有余。
1967年,英国宣布最迟将于70年代完成从苏伊士以东的撤军,美军开始轰炸北越,东南亚地区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新加坡会被美国吞没吗?1962年,李光耀第一次造访莫斯科。为了应付新局面,他外交举措之一就是在1968年6月与苏联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1968年苏联海军第一次在东南亚地区游弋,并途经新加坡海峡进入印度洋。拉惹勒南公开表示:“新加坡欢迎包括苏联和日本在内的地区外势力在新加坡和东南亚的利益增长。”“如果本地区只受制于一个大国,新加坡会面临严重的麻烦。”
1971年第18届英联邦政府首脑会议在新加坡开幕,恰逢两艘苏联战舰从马六甲海峡通过。与会代表在会议厅就可遥望战舰通过海峡的情景。面对代表们的质询,李光耀很平静地回答:“任何人都应该知道马六甲海峡是公海的一部分,同时也是国际航运的主要航线之一。当美国的第七舰队通过此处时,没有人会对它产生咄咄怪声。然而,我实在不明白:为何两艘苏联海军船只经过此处时,就引起大家的啧啧惊叹?”
而在1969年赴美时,李光耀则极力劝说尼克森将“越战”坚持下去,让美国各界刮目相看。事实上,他本人并不喜欢美国。李光耀在回忆录中说,他认为美国人缺乏经历古老文明熏陶的高雅素质,过于急功近利,鲁莽急躁,雄心勃勃。在他看来,美国不了解东南亚,华盛顿背弃吴庭艳的做法毫无原则可言。1965年8月,夫人柯玉芝生病,李光耀想通过美国领事馆请一位美国医生来新加坡做手术。美国人居然没有帮这个忙。李光耀为此愤愤不平。
可他认清了现实,新加坡需要美国和苏联在东南亚的相互制衡。美国走了,别的国家会来,“因为真空终得填补”。“如果由一个粗鲁得多的、施加压力更大的国家来填补的话,东南亚小国的生活将更加大大地不舒服。”为此,新加坡要求美国继续对菲律宾和泰国履行《马尼拉条约》中的安全防务上的承诺,主张美军继续留在泰国,还建议美国成立印度洋舰队,以保证美苏之间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力量平衡。
他多次在演说中强调:“美国在越南进行干预,是在给东南亚国家争取时间,东南亚国家的政府必须充分利用这个时机,解决我们社会中存在的贫穷、失业和财富不均等问题。”在“越战”期间,新加坡接受驻越美军每周3次、每年约2万人到新加坡的消遣娱乐。美国军舰和航母对石油的消耗量如同一座大型城市的电厂,地面战场喝起油来同样如饥似渴。其中大部分石油供给都来自新加坡的炼油厂。对于那些正考虑来新加坡投资的美国企业来说,“越战”传递的信息更重要:“它们……有信心,相信美国政府会继续留在东南亚,它们的资产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没收或蒙受战争的损失。”
包括基辛格在内,与李光耀交往过的人都钦佩他的敏锐。1969年李光耀访问美国,与尼克森总统谈到中美关系,极力支持美中关系正常化,因为中国日渐强大,不能忽视它的存在。他对尼克森分析说:“两国(中美)之间并没有什么与生俱来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纠纷。中国最理所当然的敌人是苏联,两国有着一道长4000英里的共同边界,边境形势只是到近百年来才变得对中国不利,双方有大笔旧账要算。美中两国的边界线是人为的,就划在台湾海峡的海域上,这是暂时性的,会随着时间消失。”
这番话背后包含的是李光耀对未来的另一判断:美国在东南亚势力减退的趋势不可扭转,中国才能在东南亚制衡苏联。1976年,李光耀首次访华。他提出:“新加坡认为中国越强大对新加坡越有利,中国同美、苏的力量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果不其然,1978年,苏联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对于中国次年的“对越自卫反击战”,李光耀击节叫好,认为“它扭转了东亚的历史”,“教训越南也就是教训苏联,是对越南侵略行为的有效警告”。至80年代后期,苏联倾颓,新加坡再次热切拥抱美国,那是李光耀式大国平衡术的再次运用。
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创始院长格拉汉姆·埃里森在《李光耀论中国与世界》一书中总结李光耀的成功:若把思想家分成刺猬型和狐狸型两类,那么,李光耀无疑属于后者。他聪明,甚至有些狡诈,非常实际。他知道世界正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也知道如何让新加坡适应变化著的世界。
1973年5月,李光耀以新加坡共和国总理的身份第一次访问印尼时,印尼一家报纸这样评论:“新加坡和雅加达之间区区一小时的飞行航程竟如此漫长,李光耀要在遍访英国、美国、欧洲、日本、台湾,在全球各地绕了一圈之后,才抵达印尼进行正式访问。”李光耀说:“报章社论说得一点也不错。我必须先证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马来西亚经济的情况下生存,我们不是只会依赖邻国的寄生虫。”
至80年代,新加坡在经济和国际政治舞台上的善舞已经令邻居们刮目相看。在东盟内部,新加坡成为推动区域一体化的领袖之一。人人都想复制新加坡式的成功,走上全球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