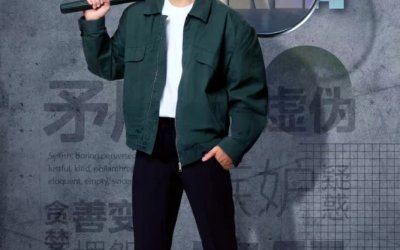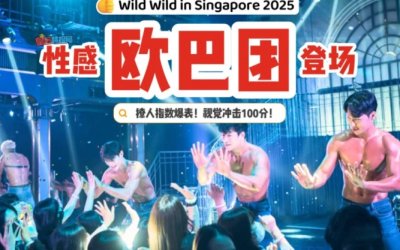跨国公司令新加坡搭上了世界贸易每年增长8%到10%的高速列车。70年代,《时代》周刊等美国最著名的媒体都开始讨论新加坡,热切赞扬它的辉煌成就。通用电气公司在这里开设六家不同的工厂,生产电气与电子产品、电动机等,是70年代末新加坡雇用劳工最多的企业。美国跨国公司为新加坡奠定了庞大的高科技电子工业的基础,使新加坡在80年代转变成一个电子产品主要出口国。海事工业主靠了日本跨国公司的资本和技术。日本造船工程公司、三菱重工等相继在新加坡设厂从事造船事业。炼油工业得益于壳牌、无比、美孚、英国石油公司等的投资。70年代,新加坡已经是世界上最重要的石油加工和出口中心。
“在石油危机爆发之前,新加坡的经济能够随着蓬勃发展的世界贸易起步,真是幸运。”李光耀在自传《经济腾飞路》的一开始就如此感慨。新加坡全面接受了跨国公司的资本、技术、企业家、管理和市场的“套装货”。这种深刻的依赖最终使新加坡成为国际生产链的重要一环。用李光耀的话说:“没有跨国公司,我们就没有工作,没有住房,甚至没有整个新加坡。”

新加坡有限公司
20世纪60年代,新加坡工人党领袖在一次大选时指责李光耀被“利润”所迷惑,李光耀直截了当地反击:“如果把‘利润’看成肮脏的字眼,新加坡就会灭亡。”
李光耀在自传《经济腾飞路》中详细回忆了好些外交经历。他观察世界的视角颇值得玩味。1973年的英联邦渥太华会议,孟加拉国总理拉赫曼的私人客机给李光耀留下深刻印象。他琢磨:“客机还留在原地,空置了八天,白白浪费,没有一点收入……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以贫困的一面打动世人的心,让大家看到他们迫切需要援助。我安于乘坐普通的商用客机,借此为新加坡保住多年享有的第三世界国家才享有的条件。”1979年,在赞比亚,夫人柯玉芝只买到一颗孔雀石蛋做纪念。李光耀提醒自己:赞比亚是单一商品的经济体,“卡翁达总统最关心的是政治——黑人对白人的政治,不是赞比亚取得增长的经济因素”。1990年2月,苏联总理雷日科夫访问新加坡,向新加坡副总理王鼎昌开口借一笔5000万元的贷款来购买新加坡的消费品。李光耀要王鼎昌别答应他:“苏联总理搞到这等地步,要开口向小小的新加坡商借5000万元贷款,可见必定已经耗尽了所有大国提供的信用贷款。苏联所负的国债是毫无价值的。”
西方嘲笑李光耀建立了一个保姆国家:政府几乎粗暴地管理公众生活的方方面面,甚至于规定男性不许留长发。“他们可以笑我们,可我深信最后开怀大笑的人会是我们。”李光耀有自己的理由,“新加坡过去算不上是个有教养的文明社会。我们准备在最短的时间内争取实现这个目标,对此并不感到惭愧。”“声音有多大?用哪一种语言?你是否可以随地吐痰?假如我们没有这样干预,而又没有积极去执行这些措施的话,我们就没有今天的成就。”1983年,国家发展部长建议禁止食用口香糖,因为人们把吃过的口香糖塞进大门和信箱的钥匙孔,或粘在电梯按钮上,随意吐在地上和走廊上,导致“打扫的开支增加,也损坏清洁设备”。最终新加坡干脆禁止了口香糖的销售。
“新加坡有限公司”——人们这样戏谑李光耀和他管理的国家。这一玩笑倒是说出了新加坡商业立国的本质。就像一名企业家,对于李光耀和他的政府来说,衡量一切政策的标准是效率和效果、成本和收益。而所有政策都指向一个具体的目标——回到1968年的那次访美,李光耀考察了美国人如何衡量商业风险。他得出的结论是:“他们追求政治稳定、经济稳定、金融稳定和良好的劳资关系,以确保为世界各地的顾客和子公司供应产品的生产活动不受干扰。”
观察李光耀和他的同侪们重构的新加坡政治和社会秩序,这一商业逻辑为一切的基准。
1971年,李光耀在“共产主义与民主制度”研讨会上讲话,对政治、经济和安全三项的重要性进行排序:“没有稳定的政治局面以及合理和现实的政治领导。那就不可能谈到经济发展。……失业的人数就一定很多,危险的内部安全局面也就一定跟着产生。”“如果我们的政治局势继续保持稳定……那么新加坡会有快速的经济发展。”
保持政治稳定是项特别棘手的工作。除了经济可能带来的隐患,新加坡人口组成复杂,华人约占总人口的70%,马来人占15%,印度人占7%,各自信仰佛教和道教、伊斯兰教和印度教。语言上有英语、汉语、马来语和泰米尔语四种官方语言。加之国家处在整个东南亚民族矛盾的大环境下,新加坡的多元文化随时可能被政治裹挟,激发民族分裂和潜在的暴乱。
如何治理新加坡,使之完成过程被极度压缩的现代化,李光耀并不准备因循旧例。他出身在华人上层家庭,原本预备过安逸、稳定的精英生活。1941年,英军战败投降日本,英国统治构成的秩序不复存在。他后来回忆,日本统治之下的生活,让他看到了权力的意义,“权力、政治和政府是密切相关的”。李光耀在剑桥大学法学院求学期间,汤因比的《历史研究》是最受欢迎的课外读物,学生几乎人手一本。汤因比认为,文明的发展是一个“挑战—应战”的过程,人类面对环境发出的挑战,做出相应的反应,其应战的方式与成效决定了文明的盛衰。
李光耀和他的同侪决定运用权力,以最高的效率应对国家所面临的挑战。他们的最优化选择显然不是英国人留下的民主。首任外交部长拉惹勒南说得明白:“‘民主就是要反对党’的观念对于那些视今天的繁荣和稳定为理所当然,并且以为这种局面会永世存在的人们是有吸引力的。它不是生存的政治,而是繁荣永无止境的政治;是那些不懂得新加坡历史的人的政治,这些人不曾站在深渊边缘、不曾有过因灾难随时可能出现的担心和焦虑经历。”
在李光耀看来,新加坡没有适合多党制生存的文化,尤其反对党之所以反对政府的决策,“并不是他们另有什么高见,而只是为了搞垮政府……不但提不出健全的计划来促进发展,往往只能施舍想像中的财富,在人民当中造成虚幻的希望,造成好像英国和许多第三世界国家那样的混乱”。
建国至今,李光耀建立的人民行动党一直牢牢把持着议会。他巧妙地调控反对派。政党活动有严格的法律规定,例如用于选战的经费来源必须登记注册,各党选战标语牌的地段、方位、距离、时间、地点都有具体的限制。选区的划分根据有利于执政党获得更多票数的原则来安排。如果某一选区的反对党势力较大,有可能在下一次选举中取得多数,选举委员会就会把这个选区分割为几个选区,或把其中一部分与其他选区合并,用这种不断进行大幅度的选区划分与重新组合的办法分散反对党的选票资源。
有时,他采用更加直接的办法。在选举时,李光耀曾以半带威胁的口吻说:“选出在野党议员的选区的居民应觉悟到,他们无法得到政府的服务。”他曾把早年与其合作、后来对其统治构成威胁的社会主义阵线领导人林清祥拘禁20多年,驱逐出新加坡。1981年,惹耶勒南作为工人党的代表成为当时议会中唯一的反对党议员。他拒绝在政策上与执政党达成妥协。于是,李光耀不断将他送上法庭。在80年代的几次诉讼中,惹耶勒南被判定有非法挪用工人党的资金和做伪证罪。他失去了律师从业资格,再加上几次数额较大的赔偿,终于彻底失去了参政所需的金钱与名誉。
东南亚各国的历史并不缺乏权力人物。不同的是,就像修理市容、教化民众一样,李光耀用权力为新加坡立规矩,将这个弹丸小国紧紧绑缚在经济全球化的高速列车上,决不允许它存在脱轨的可能性。
从1968年开始,顺应跨国企业的要求,政府相继通过《就业法》、《工业关系法(修正)》、《劳动工会法(修正)》,对涉及劳动纠纷、集体谈判、招工与晋升等问题都做出明确规定。工会的权力受到严格限制,凡未经许可而采取罢工或其他抗议行动的则视为非法。法律禁止基本公共事业部门的工人举行罢工,同情罢工者也被视为非法。政府取代工会在劳资矛盾中扮演调停人。从1970年至今,新加坡很少发生大规模的工人罢工事件。
1969年5月,吉隆坡发生种族暴乱之后,亲马来人的《马来前锋报》对新加坡政府采取公开敌视的态度。李光耀回忆:“为了制止《马来前锋报》继续在新加坡煽动种族情绪,我们修改条例,规定所有报纸必须在新加坡出版、在新加坡设立编辑部,才有资格申请在本地印刷和销售的准许证。”1974年,新加坡政府颁布了《报纸与印刷媒体法》,严格规定了媒体的股权分配界限,明确了报道禁忌。
1983年,李光耀为国家人力资源的储备担忧。他在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极具争议的讲话。他说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像他们一样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对于任何一个西方民主国家政治家来说,这种讲话的政治代价都是毁灭性的。但李光耀成立了社交发展署,用专题研讨会、讲座、电脑课程,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旅行的方式当红娘。1984年,政府颁布了新的生育政策,对具有高等教育文化程度的育龄夫妇改行鼓励生育的政策,同时鼓励文化水平低的夫妇减少或保持国家规定生育数。
对李光耀来说,政治正确是没有意义的。他并不回避自己是马基雅维里的崇拜者。“我认为,太在意民众支持率的领导人是软弱无能的领导人。”“在受人爱戴和令人畏惧这两者之间,我始终认为马基雅维里的思想是对的。如果谁都不怕你,那就毫无意义了。”真正重要的是,当一叶扁舟的新加坡航行在全球化的海面上时,能够躲过每一次足以令它粉身碎骨的惊涛骇浪,成功借力每一轮东风。
从1965年独立到1990年李光耀卸任总理,新加坡经济跨越了数个节点。60年代末到70年代初,新加坡以低价值劳动密集型产品,改造了过分依赖转口贸易的单一结构。70年代末,新加坡出现劳动力短缺。政府立刻在1979年着手经济调整,开启“第二次工业革命”,进行出口产品升级,集中发展电子、电脑、精密仪器加工、机械、医药等高附加值产业。用李光耀的话说:“新加坡的未来在于我们的脑子,而不仅在我们的手。”
1985年,新加坡经历了20年来最严重的经济衰退,GDP增长下降到了1.7%。情况来得出人意料,这年3月,政府官员还预测能有5%的增长。政府迅速分析问题出现的内部原因:新加坡营业成本高,特别是劳动力成本高启,削弱了新加坡的国际竞争力。政府随即采纳经济委员会开出的药方,实行弹性工资计划等措施,很快扭转了局面。
这次经济低迷还让李光耀认识到过度依赖部分出口工业的弊端,他将经济发展重点转向利用优越的地理位置和贸易技能发展空运、通信、物流、航运和货运设备等服务业,由此带动了商务和金融服务业的发展。为了规避风险,新加坡运作亚元股市,建立了国内资金市场,摆脱了对纽约市场的依赖。
所有决策的制定和推行效率都令人惊叹。李光耀后来这样总结新加坡高速发展的经验:“1965到1981年的这十几年,是新加坡最好的年头。在这一段时间里,新加坡享有历来最高的经济和社会进步。也正好是在这些年里,我们政治稳定,在国会里没有好斗、吹毛求疵的反对党。”
国际体系的弄潮儿
在“新加坡有限公司”这艘航船上,船长李光耀以严明的纪律打理自己的船队。但相比内乱,来自海面的危险更大。
如何理解新加坡的安全处境?1965年12月,新加坡第一届国会开幕前,马来西亚驻新加坡步兵旅的阿尔萨戈夫准将坚持要求由他的机车警卫队护送李光耀到国会。李光耀很惊讶,“因为他表现得仿佛自己是新加坡军队的总司令,随时准备接管这个岛国”。他在心中审度局势:“东古(马来西亚总理)必定是要提醒我们和那些将会出席国会开幕式的外国使节们,新加坡仍然在马来西亚的掌握之中。如果我责骂阿尔萨戈夫准将放肆,他会向吉隆坡的上司报告。他们必会采取其他步骤向我表明,真正掌握新加坡大权的是谁。因此我觉得最好是默默同意。”于是,新加坡共和国国会第一次开会时,总理是由马来西亚军队“护送”到国会大厦的。
任何轻举妄动和意气用事都将令新加坡倾覆。在李光耀时期,国家对外政策的制定权只把持在三个人手中:总理李光耀、外长拉惹勒南和国防部长吴庆瑞。从1965到1979年,在国会的记录中,关于对外事务的讨论平均每年只占总记录的2.22%。1974年以前,新加坡外交部只负责收集信息而不参与决策,李光耀会在拉惹勒南默许下直接给驻外大使下命令。拉惹勒南外长回忆起这段经历:“在新加坡,人民的意见是无关紧要的……制定外交政策根本不是玩政治足球。也许这就是我们没有在外交上陷于困境的原因。……我们必须尽可能少犯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