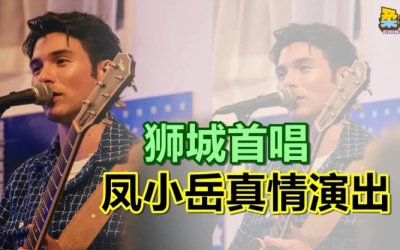1965年,有記者問,新加坡是否會和與馬來西亞不合的印度尼西亞建立外交關係時,李光耀饒舌地答道:我們希望同馬來西亞友好,但這並不意味著我們必須和所有對馬來西亞不友好的國家也不友好。馬來西亞的朋友可以是我們的朋友,但馬來西亞的敵人不一定就是我們的敵人。他的潛台詞是:「首先必須記住的是新加坡是個小國,不能在建構東南亞的歷史進程中有多大貢獻。老虎們打架時,小羊參加進去是自找麻煩。」

對中政策是一個典型的例子。1975年與來訪的泰國首相庫立會談時,李光耀透露自己的擔憂和難處:「我所關注的是,中國在馬來亞和印尼共產黨成立紀念日發給他們的賀詞。這些賀詞在吉隆坡和雅加達激起強烈的反感和憎惡,我不希望因為自己和周恩來有同樣的血統,而使這種情緒轉而針對我。」
李光耀竭力洗清新加坡「第三中國」,或是「第五縱隊」的嫌疑。70年代,他與印尼總統蘇哈托見面,專門向他解釋新加坡華族觀眾在印尼與中國的羽毛球賽中為中國隊喝彩一事。「我說久而久之新加坡華人在思想意識上將會變成新加坡人,這樣的看法他接受了。」在決定同中國互設商務代表辦事處之前,李光耀親自向蘇哈托通告了情況。他強調這不過是為了促進貿易,不等同於外交層次上的代表性,以獲得印尼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李光耀向印尼承諾:新加坡不會趕在印尼之前同中國建交。說到做到,「印尼在1990年8月與中國恢復邦交,同年10月,我到北京,新加坡也跟中國建立外交關係」。
李光耀擱置了與馬來西亞、印尼的政治矛盾,但是,當他的政府在世界範圍內尋找商業機會、試圖扭轉生存危機時,另一個事關生死的問題是他所不能迴避的:對於那些在東南亞上方投下影子的大國,新加坡的立場究竟是什麼?
戰後民族國家普遍存在一股反對大國、排斥大國影響的思潮。大多數東南亞政治家相信,在一個全新的時代里,他們可以決定自己國家的命運。但李光耀有不同的看法:「在新加坡獨立不久,我們認定,小國不能依靠自身的經濟、政治和軍事力量生存,從一開始我們就決定加入國際體系,把我們的未來託付給國際體系。」
新加坡人將他們實用主義的商業邏輯並行不悖地用在了外交上。1976年,拉惹勒南外長在曼谷有過一次令人印象深刻的講話。他說:「我們認為大國的存在以及他們之間的競爭是國際政治中永恆的事實,只要民族國家存在,就會有國家實力的層次區別,一些國家比另一些國家更強大,所有國家都競相擴大自己的勢力和影響。我們不贊成現在的流行觀點,認為大國力量是邪惡的、危險的、不道德的,其實大國在這些方面表現得並不比小國多多少,大國與小國的唯一不同是在必要的時候,大國有足夠的資源和技術實施他們的詭計。大量事實證明,一些不大的國家為了自己的利益,威逼、威脅、傷害比它們更弱的國家時也是毫不猶豫的。新加坡接受大國存在以及大國在東南亞競爭的現實……如果在本地區沒有大國的競爭,我們可能要面對更難處理的權力爭奪。」
新加坡打算如何做?拉惹勒南說:「如果跨國公司來新加坡只是單純地為了賺錢,那麼它們一點都不危險;如果它們帶著政治目的來,那就是危險的。為什麼以及什麼時候跨國公司會由賺錢轉向玩政治呢?在它們受到不公平待遇的時候。所以我們必須公平對待它們。」同樣道理:「在國際政治中,我們避免捲入大國爭鬥,而是主張所有大國都存在於本地區。如果你說要這個大國在這裡,其他大國走開,那麼你就不可避免地被卷進大國政治。」
新加坡擺明開門做生意的態度。且不論「冷戰」時期,即使在今天,也很少有人能像李光耀那樣在大國之間遊刃有餘。
1967年,英國宣布最遲將於70年代完成從蘇伊士以東的撤軍,美軍開始轟炸北越,東南亞地區權力結構發生了重大變化。新加坡會被美國吞沒嗎?1962年,李光耀第一次造訪莫斯科。為了應付新局面,他外交舉措之一就是在1968年6月與蘇聯建立大使級外交關係。1968年蘇聯海軍第一次在東南亞地區游弋,並途經新加坡海峽進入印度洋。拉惹勒南公開表示:「新加坡歡迎包括蘇聯和日本在內的地區外勢力在新加坡和東南亞的利益增長。」「如果本地區只受制於一個大國,新加坡會面臨嚴重的麻煩。」
1971年第18屆大英國協政府首腦會議在新加坡開幕,恰逢兩艘蘇聯戰艦從馬六甲海峽通過。與會代表在會議廳就可遙望戰艦通過海峽的情景。面對代表們的質詢,李光耀很平靜地回答:「任何人都應該知道馬六甲海峽是公海的一部分,同時也是國際航運的主要航線之一。當美國的第七艦隊通過此處時,沒有人會對它產生咄咄怪聲。然而,我實在不明白:為何兩艘蘇聯海軍船隻經過此處時,就引起大家的嘖嘖驚嘆?」
而在1969年赴美時,李光耀則極力勸說尼克森將「越戰」堅持下去,讓美國各界刮目相看。事實上,他本人並不喜歡美國。李光耀在回憶錄中說,他認為美國人缺乏經歷古老文明薰陶的高雅素質,過於急功近利,魯莽急躁,雄心勃勃。在他看來,美國不了解東南亞,華盛頓背棄吳庭艷的做法毫無原則可言。1965年8月,夫人柯玉芝生病,李光耀想通過美國領事館請一位美國醫生來新加坡做手術。美國人居然沒有幫這個忙。李光耀為此憤憤不平。
可他認清了現實,新加坡需要美國和蘇聯在東南亞的相互制衡。美國走了,別的國家會來,「因為真空終得填補」。「如果由一個粗魯得多的、施加壓力更大的國家來填補的話,東南亞小國的生活將更加大大地不舒服。」為此,新加坡要求美國繼續對菲律賓和泰國履行《馬尼拉條約》中的安全防務上的承諾,主張美軍繼續留在泰國,還建議美國成立印度洋艦隊,以保證美蘇之間在太平洋和印度洋上的力量平衡。
他多次在演說中強調:「美國在越南進行干預,是在給東南亞國家爭取時間,東南亞國家的政府必須充分利用這個時機,解決我們社會中存在的貧窮、失業和財富不均等問題。」在「越戰」期間,新加坡接受駐越美軍每周3次、每年約2萬人到新加坡的消遣娛樂。美國軍艦和航母對石油的消耗量如同一座大型城市的電廠,地面戰場喝起油來同樣如饑似渴。其中大部分石油供給都來自新加坡的煉油廠。對於那些正考慮來新加坡投資的美國企業來說,「越戰」傳遞的信息更重要:「它們……有信心,相信美國政府會繼續留在東南亞,它們的資產有所保障,不怕被人沒收或蒙受戰爭的損失。」
包括基辛格在內,與李光耀交往過的人都欽佩他的敏銳。1969年李光耀訪問美國,與尼克森總統談到中美關係,極力支持美中關係正常化,因為中國日漸強大,不能忽視它的存在。他對尼克森分析說:「兩國(中美)之間並沒有什麼與生俱來的或者根深蒂固的糾紛。中國最理所當然的敵人是蘇聯,兩國有著一道長4000英里的共同邊界,邊境形勢只是到近百年來才變得對中國不利,雙方有大筆舊帳要算。美中兩國的邊界線是人為的,就劃在台灣海峽的海域上,這是暫時性的,會隨著時間消失。」
這番話背後包含的是李光耀對未來的另一判斷:美國在東南亞勢力減退的趨勢不可扭轉,中國才能在東南亞制衡蘇聯。1976年,李光耀首次訪華。他提出:「新加坡認為中國越強大對新加坡越有利,中國同美、蘇的力量更加平衡,新加坡就更加安全。」果不其然,1978年,蘇聯支持越南入侵柬埔寨。對於中國次年的「對越自衛反擊戰」,李光耀擊節叫好,認為「它扭轉了東亞的歷史」,「教訓越南也就是教訓蘇聯,是對越南侵略行為的有效警告」。至80年代後期,蘇聯傾頹,新加坡再次熱切擁抱美國,那是李光耀式大國平衡術的再次運用。
哈佛大學甘迺迪政府管理學院創始院長格拉漢姆·埃里森在《李光耀論中國與世界》一書中總結李光耀的成功:若把思想家分成刺蝟型和狐狸型兩類,那麼,李光耀無疑屬於後者。他聰明,甚至有些狡詐,非常實際。他知道世界正發生翻天覆地的變化,也知道如何讓新加坡適應變化著的世界。
1973年5月,李光耀以新加坡共和國總理的身份第一次訪問印尼時,印尼一家報紙這樣評論:「新加坡和雅加達之間區區一小時的飛行航程竟如此漫長,李光耀要在遍訪英國、美國、歐洲、日本、台灣,在全球各地繞了一圈之後,才抵達印尼進行正式訪問。」李光耀說:「報章社論說得一點也不錯。我必須先證明新加坡完全可以在不依靠印尼和馬來西亞經濟的情況下生存,我們不是只會依賴鄰國的寄生蟲。」
至80年代,新加坡在經濟和國際政治舞台上的善舞已經令鄰居們刮目相看。在東協內部,新加坡成為推動區域一體化的領袖之一。人人都想複製新加坡式的成功,走上全球化之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