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几天,我们转发了著名画家、作家陈丹青2014年在新加坡那一场题目为《母语与母国》的演讲报道。这场讲座吸引了600多人,所谈内容涉及语言和文化,语言和社会,语言和政治,在当时的新加坡引发了许多人的讨论。
许多读者感兴趣,很好奇是谁办了这么一场演讲。
熟悉新加坡文化圈的,应该都听说过“无界限讲堂”(官网连结http://www.unthinktank.sg/UTT/en/aboutus.html)。即便不熟悉无界限讲堂,恐怕不会不知道林少芬。

远的如上世纪的林子祥红舌狗黑啤酒电视广告(http://www.welovead.com/cn/works/details/793zjtww)中的经典台词——“你,怕黑吗? 黑有什么好怕的? 怕黑,那你不是白白地活着吗?“,近的如2014年新加坡潮州文化节(官网连结http://teochew.sg/%E6%BD%AE%E5%B7%9E%E8%8A%82-2014/%E6%96%87%E5%8C%96%E4%BC%A0%E6%92%AD/),都出自林少芬手笔。
根据《联合早报》报道,“无界限讲堂”是由本地广告才女林少芬创办的10AM所推出的,目的是为新加坡人呈献具深度的跨界演讲。
陈丹青2014年《母语与母国》就是无界限讲堂的开山之作。
像这样的大型活动,需要多方支持。根据无界限讲堂官网介绍,主办单位和支持单位如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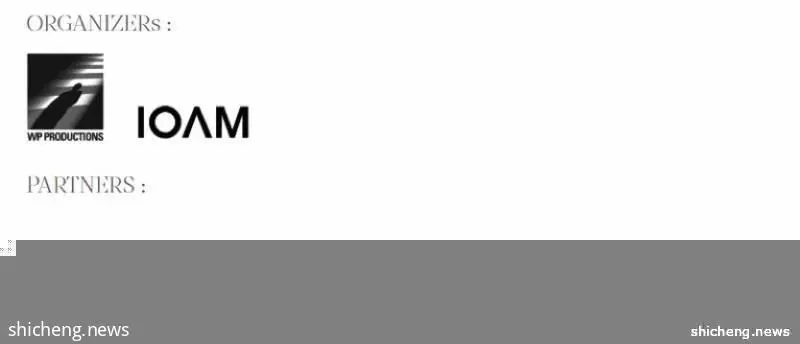
无界限讲堂办过的其他跨界讲座包括:

《光阴的故事 台湾新电影》2016年11月12日,主讲:王耿瑜

《另一个中国》2015年10月31日,主讲:陶杰、许知远

《我们这一代》2015年4月26日,主讲:肖全

《大梦无敌 我们缔造了历史》2014年6月8日,主讲:魏徳圣、齐柏林、周青元。
新加坡主流媒体曾对无界限讲堂的这些讲座写过不少深度报道,读者们可以点击阅读:http://www.unthinktank.sg/UTT/en/media.html
最后,我们再来重温一下2014年3月16日陈丹青的演说内容,文字由无界限讲堂整理(为了团结和谐的大局和我们的长治久安,部分敏感文字只好作了技术处理,你懂的;特此向无界限讲堂和陈老师表示歉意):
大家好,我第一次来到新加坡,飞机飞过来时,往下看,以为会遇到几架搜救(注:马航MH370)的飞机。海面波浪非常细腻,远远看下去像皮肤一样,上面一小朵、一小朵云。然后就降落了。降落以后呢,非常快我就发现,太好看的一个岛,一个城市。
我不会讲演,每次都请邀请方给题目,看看能不能说。彭导就说新加坡华人对华语的教育,华语的前途,有各种担忧——我的无知和轻率就上来了:我想,好啊,我也在海外待过,我也说华语,跟母国有种种纠缠的关系,那就讲“母语和母国”。多么轻率啊,直到来了新加坡才被警告:“你踩了雷区,要慎重对待,要不然你会伤人,也伤你自己。”
此前我成个老油子了,这回有点紧张,新加坡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众笑)刚才等在后台,看视频,看到诸位的大会开始了,好严重,像是开十八大的样子,一套一套介绍……但这也是新加坡的好,有点儿像日本,干什么事都如临大敌,结果来了个傻逼,不知轻重,谈什么“母语和母国”。
(众笑)
昨天差不多没敢出去走,宅在宾馆房间写发言稿。前天倒是参观了孙中山待过的小房子,当年孙先生在那儿聚众谋反——现在的说法是“dian fu国家#罪”(众笑)——照片里他跟一帮本地老华侨坐着,都长得很有样子,在那儿合计谋#反。
我是广东台山人,我的父亲这次也一起来看看新加坡。我们非常服气,没话说。早听说新加坡多么干净、多么现代化,眼见为实。我走了几圈,找不到一个地方让我觉得这里没弄好,那里又不对。没有——我来自一个丑陋的疯狂的城市,就是北京;我又生在曾被过度赞美的,但现在也非常丑陋的城市,上海,所以我有对比。每次到日本,很沮丧,我想,什么时候中国也有个城市能够跟日本比比——随便日本的哪个城市——想来想去,想不出。
二战前的东京,没法子跟上海比,很土,从前的东京人要飞到上海才能赶上应时的好莱坞电影。诸位一定知道现在的东京,也去过东京。这次在新加坡,我发现终于有座城市,住着很多中国人的城市,可以对日本说:“我们也很好,还比你大!”
可是父亲告诉我,半个多世纪前,或者更早,台山老家的人,最好是到美国,到旧金山,比较穷的,会跑到南洋,其中包括新加坡。我们祖村里有个人从新加坡回乡,穿的衣服跟他走的时候一样。他老婆气死了,就在门口打他:“你怎么混成这个样子?!”
南洋华侨曾经很苦的。我相信在座各位的祖上肯定很早过来,天翻地覆。二战以来,1965年以来,70年代以来,在座很多跟我同辈的人,一定目击了这个国家怎么变成今天的样子。
接下来试着谈谈我的不知轻重的题目:“母语和母国”。
我先要说,当我想到这个题目时,有个低级错误:我自己曾经是海外华人,要来新加坡,就把这里的听众也想成海外华人。我很谢谢这两天当地朋友警告我:这里是“新加坡华人”,不是“海外华人”,完全两个概念。
所以我先退回自己在纽约的身份。我在大陆被称为“海归”,所有仍在国外的华人群体,被称为“海外华侨”。大陆还有个“侨办”,我们都是侨办的工作对象。所有海外华侨,说母语,或者不说母语,用母语批评母国,或者赞美母国,都会牵扯到剧烈的感情问题、情绪问题,有时候会打起来。因为母语问题,就是语言问题,语言问题,就是政治问题。在所有国家,在所有历史阶段,语言问题从来不会超越政治。
我1982年出国。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新世纪,海外华人的变化非常大。我刚去时,很少很少大陆人,主要是广东人,其次是台湾人。今天完全不一样了。大家去过纽约就知道,华人小区再也不是从前的广东台山帮,中原大陆各省份的人都有。大家知道“FL功”。FL功要是在纽约街上示威,骂中国,就有东北大汉,女大汉,上去就打,暴打,警察都扯不住。
这是今天的“海外华侨”。可是换在30多年前,我亲眼看见唐人街的广东青年过春节时,舞龙灯、耍狮子,舞到大陆开办的店面,会用狮子头伸进去拱几下子,同时戏谑地说:“打#倒#中#共!打#倒#中#共!”现在呢,每到十月一日,唐人街挂出许多五星红旗。
所以三十年来中国大陆的变化,直接影响海外华侨的变化。此下我要非常审慎地区分,这么一大群海外华侨——北美南美的,西欧东欧的,日本的——不包括新加坡华人。
我来试试看会不会说走嘴。大家知道,大-陆是个不能随便说话的地方。在这儿不知道能不能稍微随便一点。如果不能,大家当场告诉,我赶紧打掉几个牙齿,讲完后,再装回去。(众笑)
刚才说了,语言问题是政治问题。著名的文学作品,都德的《最后一课》,大家知道。大家也知道,英国人在所有殖民地推行英语教育,德国人在占领区推行德语教育,绝对是政治问题。像早期东正教俄国和希腊语的关系,西班牙和整个南美国家的语言关系,也都是政治关系。中国就早一点了,中国的语言政治开始得很早,可能是全世界最早的,两千多年前,秦始皇就实行“车同轨,书同文”。此后有五四运动、白话文运动,乃至今天在蒙、藏、新疆推行汉语教育,全都是政治。
我起先不知道这些。我生在大陆,只会说国语。我的第一语言其实是上海话,之后在江湖上混,会说几个省的方言。直到出国前,我没有母语意识,也没有母国问题,一切都理所当然。可是一出去,就发现我从小讲的普通话,在不同区域的华人圈,上演不同的剧情,这些剧情,就是母语和母国的不断错位。
我先到旧金山,见了一堆从未见过的亲戚。糟糕,几天内不能交流,他们生在那里,全说英文和台山话,可我只会说国语,最让我着急的是,我无法告诉他们,这几十年,一家人在大陆经历了什么,他们也无法让我懂他们在外面经历了什么。
救星来了,是我一位表舅妈。表舅妈是缅甸华侨,小时候曾经拿着花去欢迎过周恩来总理,她能说国语——这倒有点儿像新加坡华人,说的是普通话——那几天我跟在她后面,所有讲话的场合,靠她翻译:中国人替中国人翻译。
结果我要飞去纽约了,语言靠山没了,我很慌。1982年,大家想想看,中国大陆还土得要死,完全是第三国家,我蓬头垢面,穿了条自己做的牛仔裤,排在机场的队伍里,表舅妈知道我慌了,就在人群里找,一找,找到一对台湾夫妇。哎呦!新救星来了,说国语。一路上五个钟头,我们聊到纽约。
可是这么一交谈,语言错位又来了:他们说的是“国语”,我说的是“普通话”,我很感慨:国语、京剧,国术、国医、国画,都是民国语言,我头一次当面听一位中国人很坦然地说,他讲得是“国语”,在大陆,没人说自己讲“国语”的。
到纽约后,我除了少数大陆朋友,此外的交际便是台湾华人,理由很简单,就是彼此懂国语,说国语。
可我很快又发现“国语”的错位。有一次在饭店看到一位壮姑娘给我们端菜,随口问“您从哪儿来呀”,她背过身去,高声回答:“自-由-中*国!”这句话,80年代初很多台湾人会对大陆过去的人说,口头语是:“你们大-陆”,“你们中#共”,我们的口头语呢,是“你们台湾”。跟台湾朋友初次见面,我们会说“解放后”,他们立即纠正,说,那是“沦陷后”(众笑)。我说“北京”如何,他们会说“No,对不起,陈先生,我们只说‘北平’,不说‘北京’”。我的祖父是国民党军官,黄埔七期的学生。1989年我终于去台湾见到爷爷了。我随口说起他曾经参加过的“淮海战役”,爷爷在那里被俘过,他说,那是“徐蚌会战”。1992年,祖父终于被我父亲拉回大陆定居了,父亲带着爷爷参观黄埔军校,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园,也是随口提到旁边的“广州烈士纪念馆”要不要去看看。爷爷大怒:“什么广州起义,那是广州暴动!”(众笑)。
那时爷爷很年轻,在广州当宪兵队长。张太雷先生,不知道大家听说过没有,共产党早期的地方领袖,三十多岁年纪,在广州暴#动,死了不少人,以后有个“广州烈士纪念馆”。
所以,明明祖孙之间,明明两张中国脸,明明说的是普通话,但是,不断错位。
我有一位作家朋友,名叫阿城,他有个非常精辟的,朴素的结论。他说,大陆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台湾是,中华民国;香港是,清朝。(众笑)
非常准确。想想看,香港,没有被国民党统治过,目前回归了,我不想说她被共产党统治,好像开了五十年的支票,不会变,但至少我们说这句话时,香港真的是清朝。证据呢,据说直到七十年代,香港九龙街区的告示,头一句话,叫做“尔等臣民”,还是朝廷口气。如果这是讹传,那么香港电影大家都看,《无间道》看过没有?两张超英俊的脸,一个是刘德华,一个是梁朝伟,拿枪盯着脑袋,说“我是当差的”(粤语发音)。
“当差”,是清朝话,不是民国话,更不是共和国话。共和国说“我是人民警察”,民国话怎么说,我不知道,“老子警察局的”,或怎么样,但不会说:“我是当差的”。香港直到新世纪,还在讲:“我是当差的”。
台湾呢,是另一套说法。“本党同志”,“庄敬自强”,等等等等,大家要是熟悉台湾语言,就知道那是国民党败走台湾带过去的语言。九十年代我在台北中国时报报社走廊,还看到员工奖惩名单,跟电影里民国时期的格式一模一样。
大陆不必说了。凡是大陆出来的我这一辈,都记得各种口号标语,共*产*党是个语言党,非常会创造语言。五十年代,我小时候,百货公司顶层巨大的标语,“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六十年代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七十年代是“造反有理”;八十年代呢,是“摸著石头过河”;九十年代变成“三个代表”;到了新世纪,“和谐社会”;现在呢,“中国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