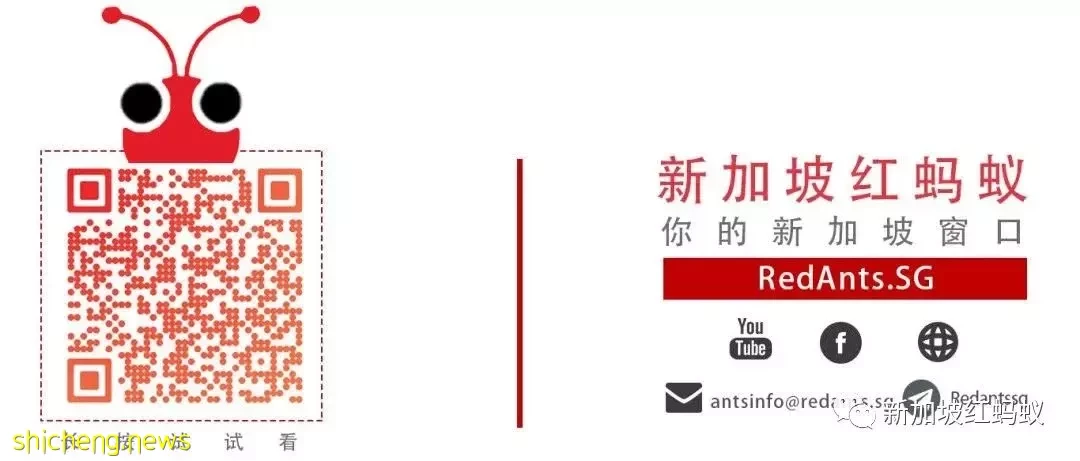國家法院外觀。(聯合早報)
作者 侯佩瑜
新加坡法庭頒布的媒體禁制令(gag order),主要是要求媒體不准報道任何可泄露受害人身份的資料。這是為了保護受害人,免受公眾審查。
如果是性侵案,媒體禁制令涵蓋的範圍通常也涵蓋被告的身份。
新加坡律師公會會長陳錦海在亞洲新聞台的一篇文章中,解釋了媒體禁制令的來由、存在的意義以及引起的爭議。
根據「公開的正義」(open justice)法律原則,被告接受公開審訊,證據就會公開聽取,法院的判決結果也會公開宣布。
這為公眾對司法體系的信心奠定了基礎,讓公眾有了知情權。
在新加坡,媒體早期甚至會報道離婚案件。夫妻的全名會公開列在報章上,包括他們婚姻破裂的導因:被遺棄、無理行為、出軌(第三者的名字也會公開)等。
陳錦海說,報道這些案件的理由很簡單:因為離婚案是在法庭上審理的,訴訟的審理過程是公平也是公開的。
公眾有權看到司法體系的運作,因此可以旁聽法庭的公開審訊。而且所有的審訊,無論是否在公開法庭受理,都會事先在法庭布告欄上公布。
媒體有權以「正義之名」向讀者披露案件的細節。這些案件不僅涉及離婚,也涉及刑事。罪行越是恐怖,公眾就越想讀。

新加坡國家法院。(聯合早報)
但有時在這個「公開的正義」過程中,有可能會處理得過火。報章會刊登受害者的照片、對他們所遭受的罪行進行聳人聽聞的描述,也會如實報道惹人熱淚的證人證詞。
隨著時間推移,人們開始思考正義是否需要以這樣的方式來報道和公開,基本有兩大考量。
1、出於對受害人的保護。
正義要求受害人不畏懼出庭作證。如果他們說出真相,不會對他們或他們所愛的人造成任何影響。不過如果涉及犯罪組織的案件,一旦他們的身份被揭露,就需要擔心自己和家人的人生安全受到威脅。
2、避免受害人遭受反覆傷害。
第一次的傷害是加害者給予的,多數受害者都是這樣。有些受害者會遭到第二次傷害,那就是在法庭上指證被告,再度轉述事發經過時。
對於貪污或搶劫案的受害人來說,這已經夠慘了。普通人會因為身為受害者出庭作證所帶來的不必要負面宣傳而感到極度尷尬。
如果被告所犯下的罪行給受害者帶來了恥辱,那就更糟糕了。
性侵就是一個典型的例子。性侵受害者不希望被公審或以媒體報道的方式讓公眾了解自己受辱的經過和細節。他們不希望別人記住自己人生中的污點。(編按:在這個網際網路時代,還有可能因為人肉搜索或被網民評頭論足,讓受害者遭受第三次或第四次傷害。)
因此,在「公開的正義」法律原則下就出現了例外情況:媒體禁制令應運而生。
在新加坡,控方可以申請媒體禁制令,禁止人們發布任何可能有助於確定受害者身份的信息。法庭則擁有決定是否批准禁制令的權利。
如果公開被告姓名,會導致受害者被認出,媒體禁制令還可以擴大涵蓋被告的姓名。這種情況通常發生在被告虐待親近的人,例如家庭成員、同學或同事等。
一些禁制令甚至不准公開被告的工作場所或學校。 即使被告最後被定罪,媒體禁制令依然生效,不能公開他或她的名字,主要是為了保護受害者的身份。但其實這也同時「保護」了加害者的身份,他們刑滿出獄後,也會帶著這個隱藏身份回歸社會。
這讓一些公眾感到不解以及擔心,因為大家都想知道隔壁是否住著性犯罪者。但我們的社會運作的原則是,如果他已經為罪行付出了代價,就不能受到歧視,應該擁有重新開始的機會。
需要重申的是:
媒體禁制令是保護受害者,不是保護加害者。 還未定罪的被告身份不應被公開

一些被告出庭時,為避免被媒體拍照,會「全副武裝」打扮,包得密密實實。(海峽時報)
根據本地司法體制的原則,任何人在沒有被定罪之前,都必須假定為無罪。
如果在還未下判前就公開被告身份,就會讓他們受到不必要的公眾關注,即使他們後來罪名不成立。
轟動一時的伊莉莎白醫院麻醉疼痛專科顧問醫生楊紹南案件,就是一個例子。 楊醫生在2017年被控非禮女子,後來因為女子證詞的一些細節有所出入,控方在審訊期間向法官申請撤銷控狀,楊醫生於2021年10月終獲無罪釋放。
楊醫生事後受訪時說,這場持續了四年的審判對他、他的家人、朋友、工作人員和病人來說都是一場折磨。他一路走來非常辛苦,受到羞辱,甚至被醫院解僱。 公開被告身份,有助於更多受害人站出來指證?

(網際網路)
但也有受害者,為了讓更多受害人挺身而出,願意解除媒體禁制令,公開自己的身份。 譬如,英國頂尖大學留學生蔡義晉(音譯,Chua Yi Jin Colin)在三年內偷拍至少11名女性朋友沖涼和如廁。
由於受害人都是被告的朋友和同學,法庭一開始為了保護受害者,發出了媒體禁制令,勒令所有人不得公開任何可能泄露受害人身份的資料,包括這名被告的身份。
其中一名女子懷疑自己也是受害人,找上了本案的受害人來確認。但因為有禁制令,受害者只能三緘其口。
該名受害人說: 「我假裝不知道,並建議她如果真的覺得自己可能是受害者,就去找警察或尋求專業幫助。這件事讓我感到很內疚。」
另一名受害者說,當她看到被告在社交媒體上發出與女性朋友的合照時,她很擔心她們卻無法提醒她們。
換句話說,禁制令在某種程度上也阻礙了受害者伸出援手去幫助或提醒其他受害人。
該案件的11名受害者於是一致同意解除被告身份的禁令。法官最終批准撤銷媒體禁令,被告的身份才得以曝光。
但,這在法庭案件中屬於非常罕見的例子。
陳錦海說,為了讓更多受害者站出來,就需要公開被告人的身份,但同時又要保護受害者,真的很難平衡兩者。
在決定是否撤銷媒體禁制令時,控方和法官必須評估案件是否可能有其他受害者。
他總結說, 「關於媒體禁制令的爭論永遠不會有結論,因為禁制令和『公開的正義』法律原則有衝突。法庭程序應該是透明的。不法分子應該被點名,不僅因為我們想羞辱他們,還因為我們不想被他們傷害。」
「每當禁制令被發布時,總有人懷疑是陰謀論或掩蓋事實。如果報道了一些令人震驚的事情,但關鍵細節卻沒有公開,就會有人對司法體系感到不滿。尤其是在這個網際網路時代,信息流動如此迅速。」
「媒體禁制令就像強效藥物。它們是必要的,但必須小劑量使用。否則,會產生令人不快的副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