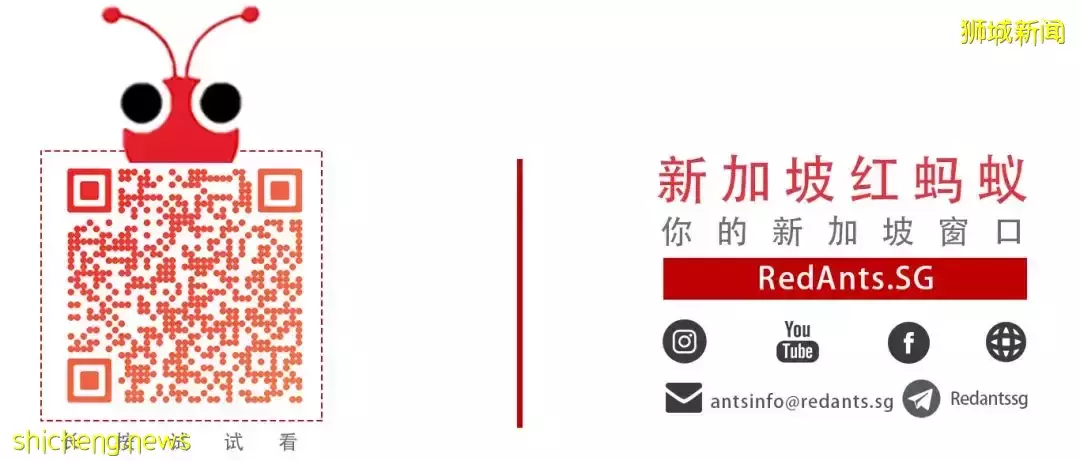執業律師示意圖。(海峽時報)
作者 李國豪
新加坡六名准律師作弊卻遭疑似「從輕發落」的事件持續延燒。
此事件在公眾輿論掀起千層浪,本地兩大中英文媒體前天(20日)也各有精彩論述,闡述本地民眾為何對六名准律師作弊的後續處理方式如此不滿。
以下為紅螞蟻綜合整理,此次事件所引發的四大爭議。
一、學生作弊尚且嚴懲,律師專業考試作弊竟然被容忍?
在《聯合早報》前天的一則讀者來函中,作者直言,六名准律師暫不獲准取得律師資格,以及為避免影響他們前途,而不公開姓名的處理方式,讓他深感「不可思議」。
該文作者質疑,律師專業考試為何能容忍考生作弊。他說,就其求學記憶所及,考試作弊,輕則記大過,重則開除,名字、罪狀和懲罰,都會在布告欄上公告。
「如果能容忍如此的作弊,不禁讓人懷疑我們的專業人士當中,有多少是這般通過考試,沒有被發現而獲得專業資格的?理應擁有高尚品格受人尊重的專業人士,形象是否也因此蒙上一層莫須有的陰影?」
作者也認為,這些准律師早就已到了性格定型的年紀,怎麼還能期望他們誠懇反省錯誤,讓公眾不必擔心未來會所託非人?
「如果他們能這般通過考試而獲得專業資格,不但對那些以正當途徑獲得成功的同僚不公平,對一般公眾也是很嚴重的心理負擔,因為我們不知道,所託付的專業人士,是否能夠讓人信任和尊重。」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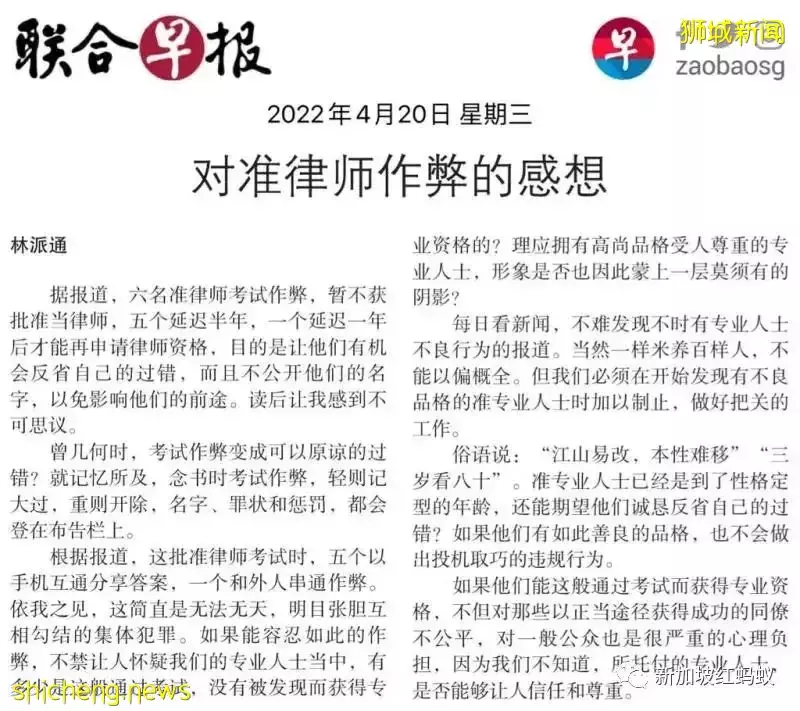
(聯合早報)
二、對其他誠實應考的律師不公平
《海峽時報》的一篇評論分析說,在新加坡成為執業律師,前後需費時超過五年。准律師們都必須費盡千辛萬苦才能獲取律師資格。

(海峽時報)
如今,六名准律師公然作弊卻依然保有能在一年半載後成為律師的機會,這對其他兢兢業業誠實應考的同儕不公平。
正因如此,六人以作弊方式,試圖抄捷徑的行為才更為人所不齒。

2019年新晉律師集體宣誓儀式。(海峽時報)
三、缺乏誠信的准律師日後能否盡責維護法律?
《海峽時報》指出,儘管六名准律師是基於以下原因,而獲得第二次機會:
在法律上並未犯下罪行;
六人隨後已在重考中取得合格成績,學術能力毋庸置疑。
但對公眾而言,這些准律師缺乏應具備的誠信,無疑是極度嚴重的問題。
「六名准律師在考試中作弊——諷刺的是其中一份試卷還與倫理道德有關——的不誠實行為,在一些人看來,已足以令他們失去(律師)專業資格。因為維護司法正義,正好是律師專業的職責所在。」
四、准律師的前途是前途,其他年輕人的前途就不是前途?
作弊被揭發後,六名准律師除了只是「暫時」不被允許獲取律師資格,甚至還獲得了「隱姓埋名」的待遇,以免在他們事業起步階段就留下污點。
輿論因此質疑,這樣的處置方式對其他年輕人是否公平?
《海峽時報》也提出一道尖銳的問題:若其他專業考試也出現作弊行為,當局是否也會一視同仁?
「這不禁令人懷疑,如果今天是實習教師或實習警察在國家教育學院或內政群英學院的考試中被抓到作弊,他們是否會被允許延續職業生涯?」

(新加坡警察部隊)
該篇評論的記者也提到,作弊事件的後續處理,讓他聯想到去年5月,那名謊稱確診冠病,結果被提控發布假信息的19歲青年。
該名青年最終被判9個月緩刑以及40個小時的社區服務。
和「隱姓埋名」的六名准律師不同,法庭沒有禁止公開該名青年的姓名,其照片也被各大媒體廣傳。
另外,他的母親據報也曾以兒子有大好前途,且對犯行充滿悔意為由向法官求情。
相較之下,雖然作弊事件的判詞中,並未提及作弊的准律師是否有悔意,但可以肯定的是,六人中的其中一人,一直拖延到作弊的16個月後,要上庭前的兩天才總算道歉認錯。
今天,這起事件又出現一些新的「爆料」。
據《今日報》報道,兩名曾在2020年參加被稱為「Part B」律師專業考試的律師透露,當年的考試因疫情而轉為線上進行,且無有效機制防止作弊。當時在長達八天的考試中,考生只須「居家考試」,監考方也未要求考生打開鏡頭,證明他們並未與其他人聯繫。
但是在2021年的考試中,當局已加強了部分監管措施,要求考生在應考電腦上安裝可以封鎖網絡和通訊軟體的軟體,而且在考試前必須用視訊鏡頭拍攝整間房間的360度環景,同時必須在鏡頭前展示桌上及桌子底下的物件,並證明手機已關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