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傑明·富蘭克林有一句名言——「這個世界上沒有什麼是確定的,除了稅收與死亡」。
稅收無疑是現代社會生活中避無可避的負擔。在許多國家,稅收甚至還以遺產稅的形式,成了死亡的一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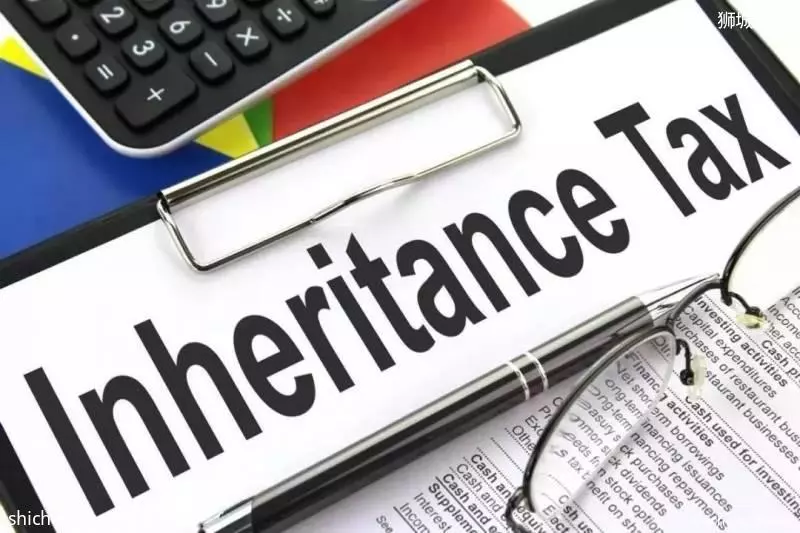
全球徵收遺產稅的國家雖然很多,但亞洲國家卻沒有多少。除少數幾個國家外,亞洲的遺產稅率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對於一個所謂「高資產凈值個體」人口增長最迅猛的地區,這一形勢對捐贈和慈善事業的水平顯然有著重要的影響。
最新的胡潤全球富豪榜顯示,截至2018年,全球共有2,694名億萬富翁,同比增加了437位。換言之,在一年的時間裡,這個世界上每天都會誕生超過1位億萬富翁。
中國的富豪數量增長尤為顯著。在中國,億萬富翁的人數從2017年的571人躍升至819人,遠遠超過了美國。而就在兩年前,中國和美國的億萬富豪人數還基本持平:分別為534和535人。
胡潤數據顯示,全球超級富豪持有的總財富在2018年增長了31%達10.5萬億美元,相當於全球GDP的13.2%,幾乎是六年前的兩倍。這意味著,極少數人的手中,掌握著超出想像的巨額財富。
教授簡介
Sumit AGARWAL
新加坡國立大學劉德光傑出講座教授
商學院金融系主任
美國·威廉康星大學經濟學博士
研究領域:房地產金融、行為金融學、家庭理財、金融法規等

捐贈誓言
我們大可以認為,大多數億萬富翁享有的財富其實遠超他們的生活所需。因此,許多億萬富翁自願簽署了「捐贈誓言」(Giving Pledge),承諾會將一半或以上的財產捐贈給慈善機構和社會事業。其中不乏科技界的知名人物,如比爾·蓋茨,馬克·扎克伯格和伊隆·馬斯克等。
然而,這些捐贈者絕大多數都來自歐洲和北美。具體來看,182名捐贈者中只有10人來自亞洲。
當然,亞洲富豪中也有例外,比如印度的Azim Premji和香港的李嘉誠——這兩位白手起家的企業家,都建立了基金會以支持教育和解決其他社會問題。但總的來說,亞洲的財富水平雖然在飆升,但慈善事業和大規模捐贈仍然維持在相對較低的水平。
這背後的原因是什麼?
毫無疑問,複雜的經濟、社會和文化因素在起作用。例如,在剛剛步入繁榮的國家或者尚在發展的國家中,富人們仍然保有貧困時的記憶,並會因此對自己和子女的未來經濟福祉缺乏安全感。
但我認為,另一個重要因素則是亞洲遺產稅的缺位和稅率過低,這允許個人在死後將所有或大部分財富留給家人。
新加坡、香港、馬來西亞和印度都完全取消了遺產稅,而中國和印度尼西亞則從未徵收過這一稅種。2016年,泰國引入了一種相對保守的徵收辦法。
日本和韓國是為數不多的例外。兩國對高價值的房產會徵收50%-55%的遺產稅。因此,平均來看,韓國和日本有著較高的捐贈水平。
除了韓日兩國外,大多數亞洲主要經濟體都專注於建立低稅率制度,以鼓勵創業和吸引投資。在此過程中,他們放棄了徵收遺產稅,也失去了讓超級富豪分享財富的一種途徑。
鼓勵捐贈
在20世紀40年代,美國的遺產稅曾高達77%。超級富豪紛紛慷慨解囊,為大學、醫院、美術館和圖書館等提供資金。其中,洛克菲爾家族和蓋蒂家族(the Gettys)都是非常出名的例子。
還有富豪將巨額資金捐贈於對致命疾病的研究(如「蓋茨基金會」),或解決如人權等社會問題(如喬治·索羅斯創立的「開放社會基金會」)。

其中有些人進行捐贈是為了讓自己的事跡流傳不朽,還有人則是為了獲得個人滿足感。
但是,我們在亞洲卻不曾看到過類似的捐贈水平。而且,雖然該亞洲的財富逐年增長,但捐贈水平卻始終停滯不前,增長水平幾乎可以忽略不計。
隨著全球經濟和財富的中心轉移到亞洲,是時候思考利用稅收建立起更有影響力的捐贈文化了。
保守派可能會持有不同意見:如果要求富豪們捐贈給慈善機構,這些人的後代就可能會放棄投資於其他有利於社會的項目中。
這雖然有一定道理,但是,我的建議並非是簡單倡導慈善捐贈,而是通過捐款免除部分遺產稅,從而達到激勵的目的。在這種情況下,富豪的後人們仍然可以自主決定是否要從稅後收入中拿出一部分投資新項目,或是捐給慈善機構。
實際上,各國也不需要對全體國民徵收高遺產稅,以免對社會制度造成突然且不必要的衝擊。稅率可設定在20-25%的範圍內,並且配以較高的起征標準——例如,僅適用於價值超過1億美元的遺產。

我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對小型激勵如何帶來行為上的重大變化進行了研究。例如,通過用小獎品激勵孩子,讓他們敦促父母節約用電,能夠對電力消耗產生不小的影響。
更直接的證據是,美國研究人員發現,當2010年暫停遺產稅徵收一年時,當年的慈善捐贈減少了三分之一以上,金額高達60億美元左右。
由此,我們有理由相信,亞洲的富豪也能像世界其他地方那樣,在一定的激勵之下慷慨解囊。
遺產稅的引入無疑有助於激勵和推動富人利用其財富造福於社會事業。
文章英文版Why it’s time to talk about death and taxes原載於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Think Business,點擊左下角「閱讀原文」查看
作者:Sumit Agarwal 新加坡國立大學劉德光傑出講座教授
翻譯:楊嘉銘
*本文觀點來自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國立大學商學院機構觀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