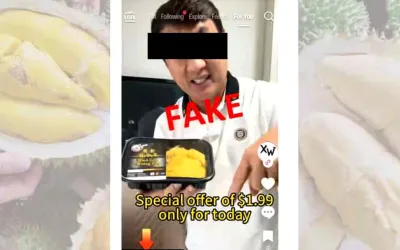國會議長陳川仁籲請海南會館和瓊州天后宮領導人相互妥協退讓,認真尋找妥協方案,他還「自告奮勇「地表示有意充當調解人。(聯合早報)
國會議長陳川仁近日在海南會館165周年晚宴上,以主賓身份發表演講,籲請海南會館和瓊州天后宮領導人相互妥協退讓,認真尋找妥協方案,他還「自告奮勇「地表示有意充當調解人。

瓊州大廈一樓門面原本貼著的「海南會館」四個大字8月底被撤下。(潘家海提供)

瓊州會館。(聯合早報)
在這起拉扯多年的社團糾紛中,身為海南人的陳川仁事實上也在調解一事上碰過一次釘子。他這次的表態,勇氣可嘉。
他在演講中說,海南人的這場風波令人感到丟臉。
「唯一令人寬慰的是,海南人不是唯一鬧糾紛的社群,但這絕對不是好事。」
他這句聽來像是自我調侃的話,在坊間引起了不小的反彈,成為飯桌上的話題。
「身為政治人物,怎麼可以這樣說話!」
陳川仁「出師未捷」,已是一身紅螞蟻。
社團的爭爭吵吵,個中緣由不是外人所能完全理解。有關的族群人士無可奈何,也只能自嘆丟臉。其實,類似事件在新加坡早有先例。
鳳山寺與南安會館的恩恩怨怨
位於莫哈默蘇丹路(Mohamad Sultan Road)的鳳山寺與南安會館,是先有廟後有會館。廟與會館的關係也並非風平浪靜,兩者之間曾經有過糾紛,只不過它們之間的恩怨來得快,去得也快,也很快被人遺忘。

鳳山寺在1978年被古蹟保留局列為國家古蹟。(聯合早報)
南安人在19世紀開始移民南洋的時候,帶來了家鄉南安的信仰,在1836年在丹絨巴葛一帶設立鳳山寺,供奉廣澤尊王。至1907年,英國殖民政府徵用鳳山寺的所在地,給予搬遷賠償。當時的鳳山寺總理林雲龍(即林路,抗日烈士林謀盛父親)和幾位南安族人負責選址,在現址重建鳳山寺,歷時5年完工。
南安族人接著在1927年正式成立新加坡南安會館,南安人的宗教網絡和鄉親網絡終於結合在一起,鳳山寺和南安會館開始了一而二,二而一的關係,但在法律上,廟產誰屬仍是個灰色地帶。
1932年10月,當時的南安族群領袖,侯西反、王可術、林箕當、謝烏抐等人入稟高等法庭,起訴林金慶、蔡三重、林深澤等鳳山寺領導。法官從歷史文獻、石碑勘查,終於判定鳳山寺屬全體新加坡南安人所有,並由華民政務司在1933年委任南安族群的社會領袖李光前為第一屆信託委員會主席,其他六名委員包括產權糾紛的兩派人士。
1936 ,南安聞人黃奕歡接替李光前,任鳳山寺產業信託委員會主席,到了1973年,鳳山寺的管理才正式由南安會館執監委員接手,至90年代,鳳山寺的帳目進一步納入會館帳目下,新加坡南安族人的寺廟和會館終於完成了雙結合的歷史過程。

2019年4月8日,南安會館會長陳奕福與署理會長梁佳吉清明節來到武吉布朗墳場,為鳳山寺創辦人梁壬癸墓地的修復工程進行謝土儀式。(聯合早報)
這起當年在華人社會中相當受關注的會館與族人廟宇的產權糾紛和平結束,一時成為佳話。
今天會館的紛爭訴諸法庭,程序遠比早期社會的程序複雜,耗時、耗力、耗資和消耗族群的凝聚力,有關族群大眾搖頭嘆息,「不欲觀之」。
南安會館和鳳山寺整合的歷史中曾經的一段短暫糾紛,在今天仍值得華社重新溫習一下。當年英殖民時代的華民政務司可以調解的事,今天的政治領袖想管又不敢管,敢管又不知如何管,對照歷史,還真是一個笑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