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四岁女童江雨惠(洋名“梅根”)自3岁起遭遇持续13个月的严重虐待。
施虐者包括她的生母符丽萍(29岁)及其男友王世祥(38岁),两人皆有毒瘾。
虐待方式极为残忍,包括殴打、剥夺食物、羞辱、暴晒、睡在不适当的地方,甚至羞辱性地带到公共场合示众。女童最终因暴力殴打、饥饿及长期折磨,于2020年2月22日不幸身亡。2025年4月3日,生母被判监19年,她的男友囚30年鞭17下。
梅根并没有白白地牺牲。
这个震惊社会的案件引发广泛关注,舆论围绕着涉案的家长、学前中心、社会服机构、幼儿培育署、儿童保护服务处、警方、甚至是邻居能否及时阻止悲剧发生的讨论点上。
而且,这些机构几乎都一一站出来暗指彼此在处理这起惨案的漏洞,因此社会及家庭发展部4月11日晚上再发文告说,案件中的Healthy Start学前中心和彼岸社会服务(Beyond Social Services),以及幼儿培育署、儿童保护服务处和警方所采取的行动,都将再被检讨。
梅根就读的Healthy Start学前中心隶属彼岸社会服务,专为经济困难、较少亲人陪伴的六岁以下儿童提供协助与服务。
社工应被授予更多执法权限?

因不喜欢梅根弄脏屋内,两人要她待在卧室外的阳台兼花槽,也指示梅根睡在阳台木板下的隔间。(法庭文件)
过去10年,至少八起虐童案是在儿童被虐至死后才曝光,受害者的年龄从两周到11岁不等,当中包括在2020年2月去世的梅根。
社会及家庭发展部4月8日发文告说,2019年3月,梅根就读的学前中心发现她身上的明显伤痕,并向幼儿培育署提交事件报告。
然而,由附属社会服务机构的社工所准备的报告中,未能充分描述伤势的严重程度,导致相关机构未能及时采取有效的干预措施。
2019年3月至9月间发现伤痕,之后就没再发生,母亲符丽萍谎称瘀伤是由骑车事故和体罚导致,过后也配合让外婆照顾并且和社服机构保持联系。社工于是将此事评估为过度体罚而非持续虐待。
梅根9月退学后,附属的彼岸社会服务多次尝试联系母亲符丽萍但不果。
幼培署10月第二次接到通报,得知梅根已退学。社工说明已向儿童保护中心求助,并询问幼培署梅根是否转读其他学前中心。但幼培署回应说,找不到梅根在其他学前中心的登记记录,并建议如担心她的下落,应报警处理。
但这个获救窗口一直关闭,因为梅根的外婆担心报警会破坏与女儿的关系。
这起案件让我们必须直面另一个残酷的问题:
社工在面对儿童可能遭受虐待的情况时,是否手中握有足够的工具和权限来保护他们?
一位从事社会服务近20年的资深社工林律霞,在《联合早报》撰文指出,在实际工作中,社工往往面临“绑手绑脚”的困境。
即使发现家暴或虐童的风险线索,也无法贸然介入,因为现行制度要求他们必须“先评估、再汇报”。
而在搜集资料时,必须尽量在不惊扰施暴者,或影响和案主或相关家庭的关系的前提下进行。
在构成“通报门槛”了,才能知会有关当局,譬如反家暴热线。
在很多情况下,不是所有的通报都会得到当局正视,社工往往会被告知要进一步跟进或搜集更多资料和信息。
“如果相关当局因为认为证据不足或信息不够,就不会介入调查或处理,导致整个儿童保护体系的缺失和盲点。”
而如果施暴者刻意躲避调查、恶意隐瞒,社工基本上无能为力。
更大的问题在于,一旦受害儿童失联(如梅根退学后),社工想要“上门查看”,但如果对方是住在私人公寓,在没有警方协助的情况下,社工几乎无路可走、无门可入。在现有制度下,社工并没有进入私人住宅的权限,也无法强制要求家属配合。而梅根的虐童案,就是发生在公寓里头。
这不是“社工不尽责”,而是“社工被制度困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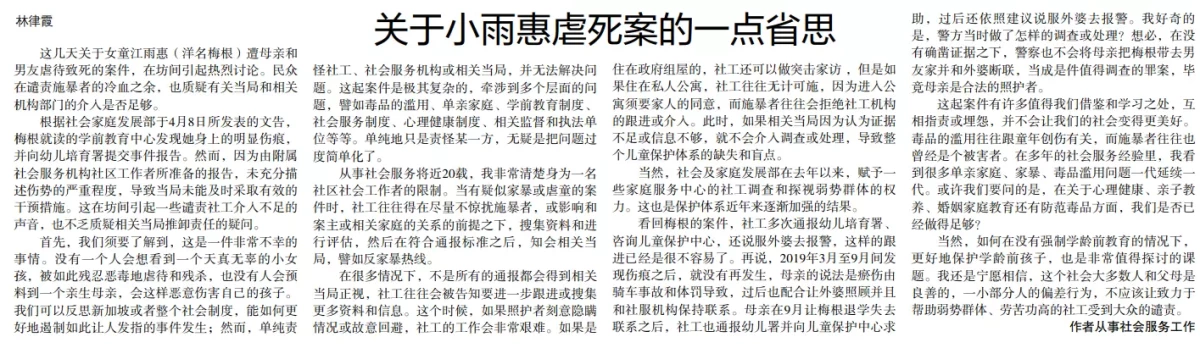
刊登在2025年4月12日《联合早报》言论版。
有公众问:
“如果外婆不愿报警,就无计可施了吗?学前中心、社工、幼培署能不能自行报警?”
《海峡时报》的读者Lim Soo Ping 提出以下建议:
是否可以立法,将“社工在调查虐童案件时,向社工撒谎列为刑事罪行”?
一旦怀疑有儿童受到虐待时,可拨打999请求警方协助,进入住宅搜求受害儿童。另一个替代方案是设立一条专门处理此类案件的警察热线。
这些建议得到了包括国务资政李显龙的夫人何晶在内的公开关注,可见其严肃性。
当然,我们不能忽视,赋权社工更多执法权力,也必须有边界与监督,不能无限上纲。
一味强调执法化,可能引发家庭与社工之间更深的不信任感,也可能造成对弱势群体的不必要干扰。因此,必须谨慎立法。
警方是最后一道防线
直到2020年1月,梅根的外婆在与外孙女彻底失联的情况下,终于同意报警,并由社工陪同前往警局报案。这距离梅根被虐待致死,还剩下约一个月的时间。
目前,警方接报后的具体调查过程与跟进细节尚未对外公布。但公众普遍关注一个令人痛心的问题:既然已经报案,为何仍未能挽救梅根?
这不只是对个案的好奇,更是对整个儿童保护机制最后一道防线的拷问。
报警之后,警方是否有足够信息判断儿童处于危险之中?社工与警方之间的沟通是否顺畅?有没有因为“缺乏即时证据”而延误了干预的时机?这些疑问,亟待官方公开透明地回应。
学前教师
另外,儿童会也提醒,学前教师的主要职责是培养和教育孩子,保护孩子免遭虐待是他们因职业所承担的额外责任。
因此,相关当局必须确保学前教育工作者在履行这项“额外职责”时,具备必要的支持与训练,包括:清晰了解哪些行为构成虐待;掌握识别虐待迹象的能力;在面对疑似虐待案例时,知道可以采取哪些恰当而安全的应对策略;有能力也有信心及时上报相关单位,而不担心遭遇后续阻力或家庭施压;以及在出现犹豫、顾虑或心理压力时,能获得适当的情感支持与制度保障等。
邻居
男被告带着被涂了大花脸的梅根,走到公寓外“示人”,故意羞辱梅根。男被告一边发出笑声,一边催促梅根对路人打招呼。
红蚂蚁不知道从家里走到屋外,他们是否有遇到其他邻居,如果有其他人看到这一幕,他们是否会感到异常?是否会想要出手干预?
梅根在被虐待时,在家里长时间哭喊,被丢在阳台里睡觉、暴晒在阳光下,这样的情况竟然长达一年之久,难道没有邻居注意到这一幕吗?
保护儿童是一项集体责任,除了有关当局,每个人,无论是邻居、家庭成员、朋友,还是公众人士,都应当在发现虐童迹象时,毫不犹豫地采取行动。
举报虐童行为,不是拆散别人家庭的行为,而是拯救生命的举动。
这不是在“多管闲事”,而是义不容辞去保护无辜、挽救生命的责任。每一次沉默,可能都会错过一个生命的最后机会。
我们每个人都应成为儿童保护的第一道防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