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国留学热,使得中国父母对领导力的培养重视了起来。
西方的大学录取学生,不只是看一次统一考试的成绩,而是对申请人的多个方面进行评估。考试成绩当然也是评估的重要一部分,但是标准考试的成绩只占一定的比重,而且标准考试也容许参加不只一次。
除了标准的考试之外,学生平时的考试成绩几乎同等重要。所以,申请西方大学,需要同时提交标准考试和平时考试的成绩单。

在考试成绩之外,另一项重要的评估对象,是申请人的学习动机,即是说,申请人为什么要选择某所大学的某个特定的专业。
在这方面,通常大学会要求申请人提交一份个人陈述(Personal Statement)。在个人陈述中,申请人需要详细地陈述个人背景、择校动机和未来职业规划。
总的来说,申请人不仅要较好地掌握对于大学学习很必要的基础知识,而且必须对自己的学校和专业选择有深入的思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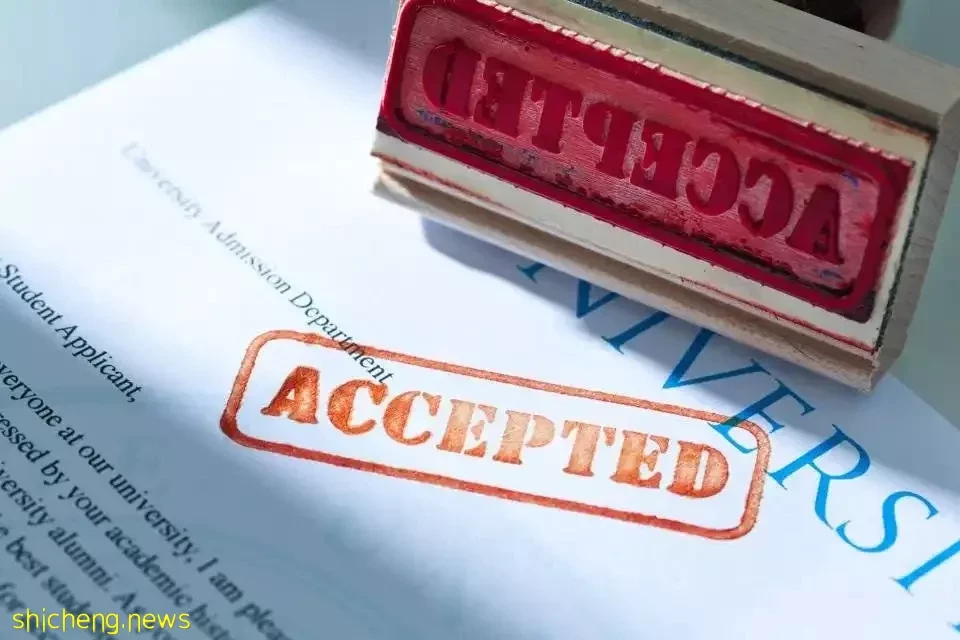
显然,成绩单只能反映学生对知识的掌握情况。人的综合素质不仅包括知识的方面,另一方面能力也非常重要。为了实现某些人生目标,有时能力比知识更加重要。
其实,西方不同的国家对能力的重视程度,也表现出很大的差异。我们可以在英美之间做一个简单的比较。总的来说,英国人更偏重理论,而美国人更偏重实务。有人曾对经济界的精英做过统计,发现美国大学的毕业生与英国相比,所占比重明显偏多。这也很好地体现在英美大学招生的不同标准上。
总的情况是,英国大学更看重考试成绩,而美国大学对课外活动和领导力有更多的重视。

美国人对实务和能力的重视,与其实用主义的思想文化基础有很大关系。特殊的文化历史背景,使得美国人相信实用的东西就是正确的。
在美国文化发展成型之后,实用主义哲学在十九世纪末被体系化。在教育理念方面,杜威提出了“教育即生活”的实用主义教育口号。按照这种教育理念,教育的根本目的是让人们有更强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能够更好地生活。由此便有了教育与社会实务之间的密切联系。
而为了做好社会实务,能力,尤其是领导能力就变得至关重要。

在网上搜索Leadership的图片,发现上图最接近我所理解的领导。一个领导应该站在他人的身边,但又与他人不同。一个伟大的领导,是死后还能站在后人身边的人。
领导力(Leadership)在最宽泛的意义上就是一个人影响他人的能力。显然,这种影响他人的能力就对应于最宽泛意义上的权力(Power)。
一个人影响他人有不同的方式,由此权力被分成三种最基本的类型:强迫性的权力(Power by Coercion)、奖赏性的权力(Power by Reward)和激励性的权力(Power by Inspiration)。
简单说来,强迫性的权力是说,你不按照我说的做,就会有严重后果。奖赏性的权力是说,你按照我说的做,就会得到好处。这两种权力都基于现实利益,只不过基于利益正反两面的结果。
激励性的权力超出现实利益,是更高级别的影响力。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受到影响、采取某种行动,不是出于现实利益的考量。

基于上述三种不同的权力,领导也就呈现出多样的类型。这主要取决于三种权力在其影响力中所占的比重。行使单一权力的领导显然是存在的,但是大多数领导的影响力是不同权力的混合体。
在特殊的社会历史条件中,领导被做非常狭隘的理解。一方面,领导被与某个特定机构中的特定职位等同起来;另一方面,领导被与向别人发号施令联系起来。
但实际上,领导力既不与某个职位有必然的关联,也不意味着要控制别人。最强大的影响力一定会超越某个特定的机构,甚至超越当下的现实利益。只有这样,它才能穿透历史,超越时代。

我们只要略微考察一下目前仍然富有影响力的历史人物,就能很清楚地看到这一点。
我们就以苏轼为例。
在他戏剧性沉浮的人生中,苏轼在朝廷中做过官,也遭受过贬官流放。论政治权力,朝廷中命官的权力很大,但这种权力只能影响同时代的下属。如果只有这些,人们现在会早就把他遗忘在历史中,就像历史上众多大大小小的官吏一样。
苏轼在目前的影响力,主要源自他在人生晦暗时期的作为和作品。他能激励现代人的,是在这些作为和作品中展现出的人格。这后一种影响力是与政治权力不同的文化权力。政权权力总是局限于一定的地域、特定的时代,而文化权力是激励性的权力,能够穿越地域和时代。

这一番关于领导力和权力的讨论,为培养领导力提供了重要的思想基础。如果我们对领导力有偏见,在培养孩子的领导力方面就容易误入歧途。
在讨论安娜【小编注:莱佛士女中学生,作者的女儿。参见:伴女儿一起成长:考入莱佛士女中,跨入人生新阶段】的情况之前,我还是先说说自己的情况。
在我们那个一场考试定终身的时代,学生们都一心学习课本上的知识。大学录取学生看的只是高考成绩,学生别的方面的素质基本上不在考虑的范围之内。
领导力的培养,本来就不是学校教育受到重视的一部分。在中学里,由于学习成绩好,老师给我安排了课代表和学习委员的头衔。这些头衔听起来像是领导的职位,但是其任务就是帮助老师干一些收发作业本的杂事,根本谈不上对他人产生什么影响。

这种如此偏重考试的教育体制,显然是特定历史条件的产物。有人因此就得出,中国的教育体制原本就比西方单调。
我们追溯一下中国教育的历史就会发现,中国传统的教育显然应该不是这样。帝国时期,中国教育的核心任务,是为管理帝国的官僚体系培养人才。官僚本身就是领导,培养领导的教育体制不可能对领导力漠不关心。
其实,帝国的官僚不仅需要有领导才能,而且需要文武全才。即便做一个七品芝麻官,县里从农业生产到公堂断案的所有事务,也都要一人全管。

对考试的偏重和对能力的忽视,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
一方面是中国的科举体制长期实行之后僵化的结果。北宋时期,经过欧阳修的改革,中国的科举体制发展到最完善的境地。当时的考试注重的是实用的治国安邦思想。但到了明末清初时期,在实行了几百年之后,科举考试已陷入内容空洞、只具形式的八股文。由此,出现了考试与实用的脱节。
另一方面,新时代的文理分立现象,进一步带来了学习理科知识与社会能力(包括领导能力)的对立。

由于受到自己时代思维模式的影响,我在很长时期里都是处于“一心只读圣贤书”的状态。即便对当下实事的关注,也是处于独自思考的状态。
只是工作了之后,我才参加一些社团活动。近几年运行微信公众号,把自己的思想分享给他人,算是一个重要的发展。待几年后孩子长大了,我有了更多的时间和精力,还会有更大的动作。
与我相比,安娜成长于一个全新的时代和一个很不同的教育环境中。在领导力的培养方面,她有着与我截然不同的情况。
由于当初我们来到新加坡之后不久,安娜便开始上小学,她在早期需要付出更大的努力适应这里的学习环境。
尽管如此,安娜很早在领导力方面就表现突出。她二年级被选为班长,后来又担任过级长(Prefect)和亲善大使。刚进中学时,由于是来自自己小学的唯一学生,安娜也经历了一段适应时间。但她很快就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

安娜在进入中学的第一学期,就积极参加班级领导的竞选。
在第一学期竞选失败之后,她仍然积极地参加班级的活动,并努力为同学服务。结果,第二学期她被选为副班长。这个职务在第二学年经过新的竞选,一直保持下来。
二年级时,安娜被选为学生代表。
进入第三学年,安娜的领导活动集中到学生代表大会中,这样,她的领导活动从班级扩展到学校。此外,这一学期课外活动的领导进行换届,四年级的学生把领导职务交给三年级的学生。新一届的领导同样由选举产生。结果,安娜被选为莱佛士戏剧课外活动的副主席。
莱佛士女子中学非常重视领导能力的培养。
学校为学生提供了较多的领导职位,但是领导职位仍然需要通过竞选获得。竞选的过程也很规范和公平。候选人先经过老师和学生推选。竞选时每个候选人需要发表一段演讲并回答观众的问题。最后,领导由集体投票产生。

△联合学生通讯员俱乐部招生宣传现场。通讯员可以选择写作、摄影或美术领域。(图片来源:《联合早报》)
安娜参加的领导活动不只局限在学校之内。
第二学年初,安娜被选入《联合早报》的学生通讯员实习生团队。这算是过了第一关。在一年时间内,实习生必须在校园期刊《早报逗号》上发表三篇文章,才能转成正式的联合通讯员。
今年年初,安娜通过第二关,顺利实现转正。刚一转正,她又积极参加通讯员的组织活动。加入活动的组织委员会,需要通过面试。安娜已经加入了两次活动的组委会。一次是今年三月的通讯员迎新活动,另一次是即将举行的通讯员颁奖典礼。
安娜的联合通讯员活动是校内活动的重要补充。
一方面,这种活动的范围更广,因为通讯员选自新加坡全岛的中学。另一方面,《早报逗号》是中文期刊。稿件用中文写,所有活动中也都说中文。这是我们家庭和学校华文课程之外的中文环境,新加坡的孩子在别的场合下惯常用英语。这样,她有了更多使用中文的机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