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份报告预测至2030年,世界单身人口比例的跃升幅度将是惊人的20%。也就是说,10个人中就有2个单身的。

随着社会的发展,世界各地的晚婚、独居越来越成为时代现象,单身生活越来越成为时代潮流。在单身生活越来越被年轻人接受的同时,他们对婚姻也越来越缺乏憧憬。
在单身人口的增长方面,日本大概在世界各国中名列前茅。日本国立社会保障和人口问题研究所最新的一份调查显示,2015年时,30岁以下的日本成人约有三分之一从未约会过,超过40%从未有性经验。此外,在日本18岁至24岁的未婚人口中,将近60%的女性及70%的男性于调查当时并无交往关系,比起2010年的调查提升了10%,而与2005年相比更是跃升了20%。事实上,甚至有30%的男性及26%的女性表示自己无意寻找对象。
几十年前,庆祝单身的节日简直难以想像,今昔的差异令人惊讶。然而,婚姻制度历经深远的改变,在现代社会也连带改头换面。中国的光棍节也不是凭空出现的,中国的家庭平均人口数历经陡降,自1947年每个家庭5.4人降至2005年的3.1人,社会形态也从农业社会转变成现代都市社会。
而新加坡,也是出了名了对单身人士不友好。比如,单身女性申请新加坡签证需要通过层层审核,而新加坡政府对单身人士购房资格也有严格的限制,单身非新加坡公民只能购买价格比HDB贵很多的公寓。
即使是单身新加坡公民想买组屋也需等到35岁以后,若想申购新组屋还会受到月收入的限制。哎,不是我们不想买组屋,而是因为新加坡政府不允许呀 。
单身人士中,很大一部分是女性,且这些女性都有一个共同特征:高学历高收入,基本实现了精神和经济独立。高智商又具备独立生活的能力,自然择偶标准也就拔高了,毕竟不能随便找一个人拉低自己的生活质量不说还影响精神健康。如果1+1得到的结果不是大于2,那还不如继续快乐且高质量的单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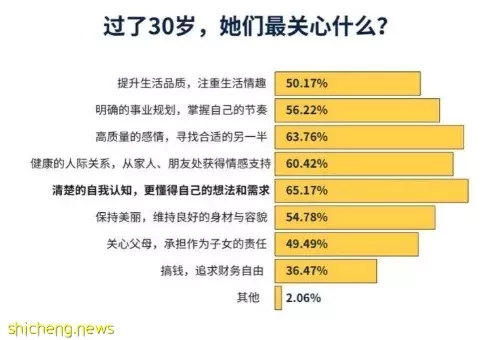
虽然单身人士们自己无所谓,但是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世界范围,尤其是发达国家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凸显以及越来越低的生育率。这就是由大量单身者引发的“蝴蝶效应”。
1980年代起,新加坡的人口老龄化问题开始显现,保持单身的大学生(尤其是接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逐渐增加,生育率逐年下滑。
这种现象不仅引起了父母的恐慌,更受到了政府的关注。
1983年8月14日晚上,时任新加坡总理的李光耀在常年国庆群众大会上发表了出人意料的讲话,指出新加坡的男性大学毕业生若要他们的下一代有所作为,就不应该愚昧地坚持选择教育程度和天资较低的女性为妻。
这次讲话后来被称为“婚嫁大辩论”,引起很大的回响。
尽管这次事件导致人民行动党在次年的选举中得票率下降12%,李光耀仍坚持推行一系列政策,希望改变新加坡大学毕业生的婚恋状况。

在他看来,不论是“棒喝”那些不愿娶高学历女性的精英男士,还是由政府出面当“红娘”,甚至用税务优惠鼓励大学毕业生结婚,都是为了新加坡最宝贵的资源——人才。
为何发动“婚嫁大辩论”?
因为最聪明的女性反而没结婚。
李光耀先生表示:促使我决定发表那次“婚嫁大辩论”演讲的,是我桌上那一份1980年人口普查数据的分析报告。
报告显示,新加坡最聪明的女性没有结婚,下一代缺少她们的传人,这意味着将会产生相当严重的后果。
最优秀的新加坡女性没有传宗接代,因为学历相等的男性不肯娶她们。
新加坡的大学毕业生一半左右是女性,其中将近三分之二小姑独处。
无论是华族、印度族或马来族,亚洲男人都宁可娶个教育程度较低的妻子。
1983年,只有38%的女性大学毕业生嫁给学历相同的男性。
对这种失去平衡的婚姻与生育趋势,我们再也不能不闻不问,不加以干预了。
我决定给新加坡的男性一记当头棒喝,使他们从愚昧、陈腐、具破坏性的偏见中醒悟过来。
我引述了美国明尼苏达州对好多对双胞胎所做的一项研究的结果:
这些孪生兄弟姐妹在许多方面都非常相似,即使分别由不同家庭在不同的国度带大,他们在词汇、智商、习惯、对饮食和朋友的好恶以及性格和个人特征等方面,仍有80%左右完全相似。
换句话说,一个人性格习性的塑造,近80%是先天遗传的,大约20%则取决于后天的栽培。

孩子的能力介于双亲之间,少数会超越或不及他们的父母。
因此,大学毕业的男性娶教育水平较低的女性,等于没有充分制造让孩子能够升上大学的条件。
我呼吁他们娶教育程度相等的女性为妻,也鼓励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生育两个或更多子女。
大学毕业的女性心里不舒服,她们的情况经我一提成了举国注目的焦点。
非大学毕业的女性,还有她们的父母亲,怪我劝阻男性大学毕业生跟她们成婚。
报章舆论排山倒海般向我袭来,抨击我是精英主义者,因为我相信人的资质是遗传的,不受教育、饮食和培训等后天条件的影响。
一对从事专业工作的夫妇对所谓低收入家庭培养出来的孩子不那么聪明的假设(其实我没有做过这种假设)提出挑战。
“就说小提琴家李斌汉吧,他出身牛车水的平民区,当初如果不给他机会,他根本不可能发展本身的才华。”(从小在牛车水长大的李斌汉当年被耶胡迪·梅纽因发现,赴英国进入梅纽因的学校就读,后来成为曼彻斯特管弦乐队的第一小提琴手。)
“整件事情抹上精英主义的色彩。”另一个女读者写道,“我是一个未婚的成功专业女性,现年40岁。我保持单身,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有人竟然认为区区一点钱财奖励就能让我跟第一个吸引我的男人上床,然后为了新加坡的未来生育出一个天才儿童,这实在是莫大的污辱。”
连当时身为人民行动党后座议员的杜进才也对我的想法进行嘲讽。
他说,他的母亲从没上过学,父亲是个书记,只受过中学教育,如果必须依赖双亲的教育背景,他根本没有出人头地的机会。
为了支持我的论点,我把过去几年以12、16和19岁三个年龄层在考试中成绩最好的学生的10%作为调查对象,对学生家长的教育背景进行分析的统计报告公开。
这些数字说服了大部分的人:
父母亲是否受过高等教育是决定学业成绩优越与否的关键。
我也公开了六七十年代的数据分析报告:
大部分获颁奖学金负笈海外的优秀生,家长都没有受过多少教育。
这些家长当中有管仓库的、做小贩的、开的士的,也有当工人的。
我把这些数据和八九十年代的数据对比,后期数据显示,首100名最杰出的奖学金得主当中,超过50%有个从事专业工作或自雇的父亲或母亲。
由此得出明显的结论:
六七十年代那些有本事的奖学金得主的双亲,如果迟一个年代出世,身处教育普及,随时有多种奖助学金和贷学金可供优秀学生申请的时代,他们也一定能考上大学。
西方媒体对这场风波大事报道。自由主义派的西方写作人和评论员借此讽刺我无知,认为我满脑子成见。
但是有一位学者为我辩护——哈佛大学的心理学教授赫恩斯坦。
他在1989年5月份《大西洋月刊》发表的《智商与生育率下降》一文中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新加坡的李光耀总理说过‘智能水平将不断下降,经济将摇摇欲坠,我们的行政管理工作会困难重重,社会将出现滑坡’,原因在于那么多受过高等教育的男性不跟教育水平同等的女性成婚,却娶没受过教育的女性,或者索性不娶。但是,李光耀是个例外,因为敢于公开谈论低生育率在素质方面产生影响的现代政治领袖没几个人。”
数年后,赫恩斯坦与人合撰了《钟形曲线》一书,把资质来自遗传的证据摆在读者面前。
成立社交发展署,政府出面做“红娘”
为了缓和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的问题,我们成立了社交发展署,推动男女大学毕业生之间的社交活动。
我还亲自挑选了新加坡国立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医生范官娇来主持大局。
当时她年近50,丈夫也是一名医生,两个子女在念大学。
她待人处事温文可亲,总有办法叫年轻人放松绷紧的心情,是挑此大梁的最佳人选。
社交发展署成立初期,大学毕业生不论男女,全对它不屑一顾。
国际传媒再一次抓住机会大肆嘲讽我们牵红线的努力和它所组织的有关活动——有专题研讨会、讲座和电脑课程,也有游轮假期和地中海俱乐部的旅行。
实际上,女性大学毕业生未婚人数日益增加的现象已开始引起家长们的恐慌,个个急得四处求助。
1985年的一个夜晚,在总统府出席招待会之后,芝告诉我,跟她同一辈的女士们同病相怜地互相谈论著受过专业训练的女儿未婚的问题。
她们感叹女子奉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成婚的时代已一去不复返了。
在大部分女性没受过正统教育的年代,聪明的和资质较差的女性都有同等机会“出嫁”,因为没有所谓“O”水准或大学毕业的分级。
如今相亲的做法已经无法被受过高等教育的女性所接受。

除了怪罪于男性大学毕业生之外,他们的母亲何尝没有责任。
非大学毕业的母亲希望自己的儿子娶个非大学毕业的媳妇过门,以免媳妇骑到自己头上来。
传统的文化偏见总认为男人维护不了一家之主的形象,是可怜又可笑的事,要改变这样的偏见谈何容易。
华人如此,印度人更是如此,马来人尤其严重。
同样的问题其实在任何教育层次都有。
一大批“A”水准(剑桥普通教育证书高级水准,或者高级中学)毕业的女性,找不到学院或同等水平的男性愿意娶她们为妻。
“O”水准毕业的女性也一样。女性只愿意上嫁,男性只愿意下娶,结果是教育程度最低的一群男士找不到老婆,因为未婚的女性教育水平都比他们高,谁也不愿意嫁给他们。
为了辅助社交发展署的功能,我促请人民协会理事长成立社交促进组,以中学教育程度的男女为服务的对象。
社交促进组的会员人数迅速增加,到1995年时已增加到9.7万人,通过它所组织的活动而互相认识的会员中,有31%结为夫妻。
教育普及化摧毁了旧有的择偶方式,叫政府不得不想方设法取代传统红娘扮演的角色。
1980年人口普查得来的数字也显示,教育程度较高的女性比教育程度低的女性生育少,而且少得多,这使我们的问题雪上加霜。
完成大专教育的妇女平均生育1.6个子女,初中和高中程度1.6,小学程度2.3,没上过学的4.4。
为人父母者要生育2.1个孩子才足以维持人口替代率。
新加坡教育水平较低的人口正在加倍增长,教育水平较高的一群却连替代水平也达不到。
为了扭转这个生育趋势,我和当时担任教育部长的吴庆瑞,在1984年决定让生育第三个孩子的大学毕业的母亲,在为所有的子女选择最好的学校时享有优先权。
这可是每一个家长梦寐以求的一种特权,却也是个敏感而看法不一的课题。
内阁中由拉贾拉南率领的平等主义派勃然大怒,拉贾拉南对“聪明父母必出聪明子女”的说法予以驳斥。
即使确实如此,他辩驳说,也没有必要去伤害人家的自尊。
巴克也表示不满,不因为他同意拉贾拉南的看法,而是因为这种政策将冒犯资质较弱的家长和他们的孩子。
年轻一辈的部长面对资深同僚三种全然不同的见解,也意见不一。
凡事求实的吴庆瑞赞成我的看法,我们两人坚持己见,认为非得把那些男性大学毕业生唤醒不可,以使他们摆脱不合时宜的下娶观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