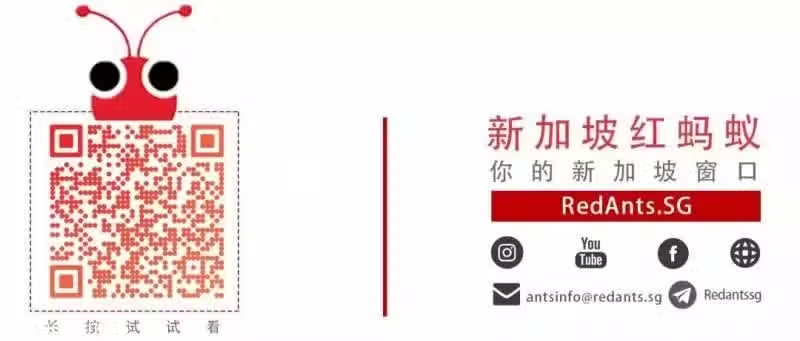新加坡著名諧星葛米星化身為喜劇人物「Phua Chu Kang」用新加坡式英語(Singlish)傳遞防疫信息。(Gov.sg視頻截圖)
作者 程英生
今年年初,本地學者陳美英在《海峽時報》寫了一篇論文,談新加坡語言環境的演變,認定英語已經成了國人名副其實的「新母語」。
陳女士說,國人有了互相認同的語言,有利各族團結與社會和諧。她也覺得建國總理李光耀先生還在世的話,必定深感欣慰,因為他一生的心愿是人人都懂英語,國家活動舉行時用上一種語文便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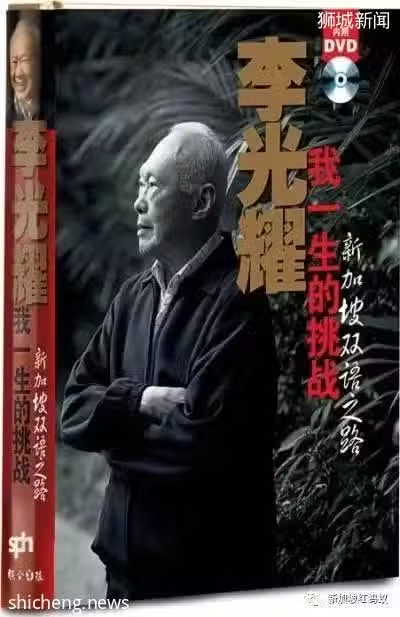
已故建國總理李光耀生前出版的《我一生的挑戰——新加坡雙語之路》。(聯合早報)
陳女士的文章論述精緻,語氣肯定,數據也豐富。她的看法不讓人驚訝,社會裡向來就有尊英語為母語的呼喚,一直伴隨著維護雙語政策的聲音。
原本以為,陳女士的論斷必會引起共鳴,引來一些社群的呼應。
不料,幾個月過去了,輿論場上不見討論;《海峽時報》刊登的幾篇讀者來函里,沒有熱烈的呼應,有的是冷冷的懷疑。讀者說,一般國人的「新母語」,更像是Singlish(混雜式英語),而不是英語。
英語的使用日益顯著,無需數據也能證實。然而,只要走入尋常百姓家,走到人們生活的深處,不難發現市井小民中,始終未改「鄉音」的,來不及擁抱那位新母親的,不在少數。

小市民還是比較習慣用方言來交流。(網際網路)
現實生活里藏著統計數字說不清的複雜。其實,那個人人都說英語的理想世界還沒到來。
最近的一場世紀大疫,就凸顯了這個社會本質。
在尋常日子裡,政府行政,上下溝通,都是英語為主。我們的確穩健地朝著統一用語的時代前進;只是偶有重要訊息,還有其他語文的輔助,而這依賴的多是生硬的翻譯,由人們在譯文中摸索官府的意思和意志。
而今,一場瘟疫來襲,日子變得不尋常,平日的語文策略暴露了局限。
到了這非常時刻,訊息必須直達每家每戶,官方非但要把話說清楚,讓人知道措施的用意;又要把話說得溫馨,讓人感到措施里的情意。
這麼一來,英語就有了局限,翻譯也不易消化,更難牽動人心。唯有多語並用,才能深入民間。
於是,我們目睹了一場民間語言總動員:主流的和非主流的;正規的和非正規的。四種官方語文之外,方言和Singlish也都無妨。此刻需要的是有溫度的、親切的生活語言。
懂得多語的網紅、名流、演員、歌星、部長和議員,都紛紛上場,展現各自的語言天分,發揮各自智商和情商。
動員現代名人還不夠,還把王沙和野峰的遺世之作召喚回來,說要讓年長人士重溫舊夢,給他們一個理由宅家看電視。

被新加坡人公認為最佳拍檔的王沙(右)和野峰。(聯合早報)
語文環境這麼一變,彷佛歷史倒流,一路回到王沙和野峰的時代,那個建國初年的語言原點。
然而,推崇時代進步的人士不必擔心,疫情一過,一切回歸正軌,時間的巨輪會繼續向前奔去。 也許到了下一個非常時期,我們必須全民動員的時候,我們已經成了一個一語通行的社會。
英語成了母語,社會更為團結,這個不難確定。 不易確定的是,在那語言統一的世界裡,在那更有效率的時空中,我們會不會因此流失一些寶貴的東西? 那要留待歷史去解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