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今年的公共獎學金得主Zulhaqem Zulkifli決定到英國牛津大學修讀佛學碩士文憑。(海峽時報)
公共服務委員會今年別開生面,在頒發政府獎學金時有所突破,選材不但跳開傳統的精英初院,把視野擴大到理工學院甚至工藝教育學院,對得主的選修科目也相對開明,讓人印象深刻的是一名在南洋理工大學修讀哲學的馬來學生,獲頒獎學金到英國牛津大學修讀佛學碩士課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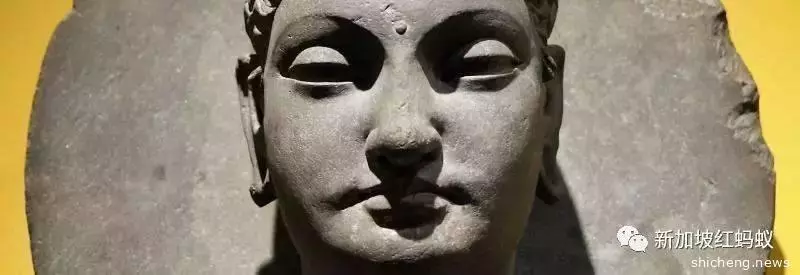
英國牛津大學是全世界少數有提供佛學碩士課程的大學。(牛津大學)
讓人不解的是竟然有公眾投函報端,批評委員會的做法。批評者認為獎學金得主應該修讀「實際」的科目,必須是對新加坡的經濟和發展有關的學問。換言之,這種批評是一種基於實用主義的功利心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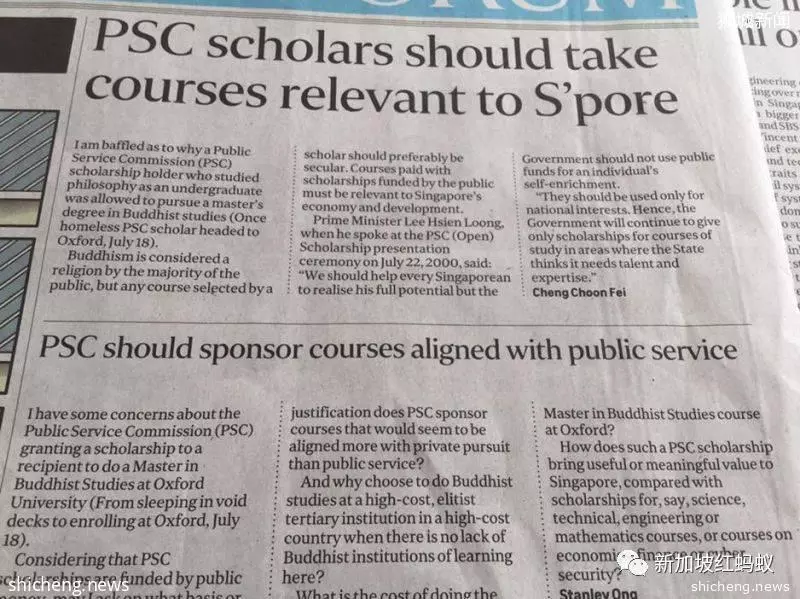
《海峽時報》7月22日讀者來函版有兩篇批評委員會做法的文章。(海峽時報)
本來,政府自建國以來就一直自詡超越左右意識形態,在施政上採取實用主義,凡是適用於新加坡國情的,不管是資本主義、社會主義還是其他什麼主義的點子,統統照用不誤。這種務實的態度,確實讓新加坡的短短的幾十年就擺脫了困境,晉升已開發國家行列。
然而凡事也都有代價,這種實用主義其實本身也是一種意識形態。其特點就在於自以為不是意識形態,這才是最大的盲點。這種意識形態的最大弊端,就在於過度務實而不知務虛,所以不乏一種物質主義的心理。通過這種意識形態看世界,就容易輕視無法立竿見影產生物質效果的事務。

主管公共服務的貿工部長陳振聲是今年公共服務獎學金頒獎典禮的嘉賓。(海峽時報)
表現在政策上,就是對文化事業的蔑視(因為不能當飯吃)。在教育上則表現為重理輕文,只要檢查一下早期內閣部長和高級公務員的履歷,就不難發現他們大部分不是理科就是工科出身,甚少有文科人才。
據說,新加坡大學原本要廢除歷史系,同樣因為「不實用」,後來是因為武裝部隊軍官學院需要培訓軍官軍事歷史,才勉強保留了下來。
當時的很多施政都是以「能不能當飯吃」作為判斷標準,大批戰前有歷史價值的建築被醜陋的大廈取代,地標性的國家圖書館讓位給一條短短的隧道,都是這種心態所導致的粗暴結果。一兩代人被這種政策潛移默化,甚至在學校里被直接灌輸這種價值觀,也難怪有人今天會批評委員會的頒獎標準了。
應當承認,我本人也深受其害,欲罷不能。所以在支持委員會的做法時,用的也是實用主義的邏輯:新加坡是個多元種族和文化的國家,社會和諧是重大的國策目標。要增進種族和宗教間的理解,有什麼比讓馬來回教徒學習佛教學問更實際的呢?這難道不是有利於新加坡的發展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