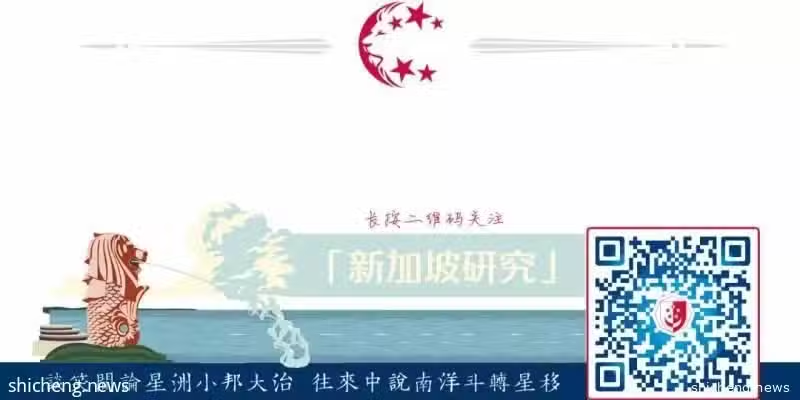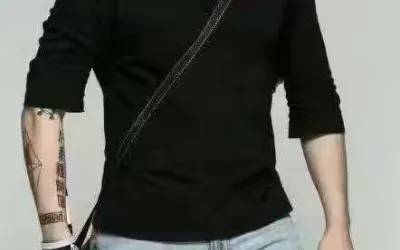儀軌建設只是社會組織發展的一個環節,這些看起來似乎有點「虛」的程序其實一點也不「虛」。多一點道義上的肯定、精神上的約束,多一點莊嚴和神聖,值得借鑑。
前不久,恰逢一支中國青年企業家代表團訪問新加坡,筆者促成了他們到訪南洋理工大學公共管理研究生院,並舉辦了一場中新對話。新加坡前國會議員曾士生先生也到場演講。晚上,筆者與這支代表團一起赴新加坡中華總商會參加新加坡現代企業管理協會第15屆理事會成立典禮,這一場成立典禮的儀式給參加活動的中國商會組織成員及本人帶來較大感悟。
成立典禮由新加坡中華總商會會長蔡其生先生擔任主賓,籌委會主席和現任會長也分别致辭等等,這些與國內社團組織成立並無太多區別,區別是在於有一個莊嚴的就職儀式和宣誓典禮。在宣誓典禮上,新任會長要率領新任理事一起向見證主賓宣誓,一經宣誓,便意味著社團管理層要照此踐諾。同時,新會長還要發表就職演說,提出施政綱領。這一幕,令人想起了我國香港、澳門特首的就職典禮,雖然新加坡此類社會組織的體量有限,但典禮儀式的莊嚴肅穆以及所帶來的神聖感卻頗有相通之處。至於儀軌,簡言之,就是儀式的規範,早期多用於宗教儀式的規範,如今儀軌已不僅僅限定於宗教儀軌。據筆者觀察,新加坡華人社會組織在成立、換屆和重大活動等多個領域已經形成一整套相對完善和制度化的儀軌。
在社會組織建設中,儀軌建設也是重要一環。在19世紀中後期華人「下南洋」移民潮興起後,華人社會組織便開始蓬勃發展,第一間華人宗鄉社團組織是作為萊佛士登陸新加坡先遣隊的木匠曹亞志在1822年創辦的寧陽會館。為什麼華人社會組織會有如此悠久的歷史?這主要是因為當時的新加坡作為英國殖民地,殖民地政權在對華人事務不甚積極,南來的華人大多舉目無親,在生活、就業以及社會福利等方面得不到有效保障,華人不得不抱團求存,一批以地緣、血緣和業緣為基礎的宗鄉會館遂應運而生。當時新加坡華人社會大致有五大方言族群:閩南、潮汕、廣府、客家、海南。以新加坡早期潮汕族群為例,善堂是其社團活動的紐帶,而潮汕善堂的大峰祖師崇拜,則附加了潮汕社團的宗教儀軌,比如「扶乩」儀式。這種宗教儀軌經過與慈善事業、社群認同的「三元互動」,逐漸轉化並強化了人文認同,增強了華人社團的凝聚力。到了現代商業社會,除了傳統宗教儀軌外,一般社團組織的儀軌逐漸規範化為簡易化的宣誓、監誓等通行儀軌。如成立於1929年的新加坡潮州八邑會館,在2011年3月10日舉行的第四十一屆董事典禮上,就是由時任新加坡外交部長的楊榮文先生主持監誓儀式,並有觀禮嘉賓若干。

雖然儀軌變得更簡單、通行,但儀軌所帶來的信仰感卻更加普遍,認同感也得到加強,舉凡新加坡社團舉行換屆儀式,相應的儀軌總是不可或缺,成員都會正裝出席,有的還多番演練,務求莊嚴神聖。之所以如此,以筆者觀之,不僅是要強化公共社團職務的崇高感,也要社團管理者肩負起更多的責任,提升使命感,推動社團發揮更多的作用,使社團領導名副其實,既能推動社團成員的互助、共贏,也有助於政府加強管理,降低社會溝通成本。此外,當代社團對於儀軌儀式的尊重,也反映了新加坡華人社會對於華人傳統文化的傳承和重視。同時,這與當代新加坡政府對社會組織發展的重視也是分不開的。新加坡從總理到各部部長,均經常應邀參加一些社會組織的活動,尤其是成立、換屆典禮。包括一些少數族群社區居民,新加坡政府也會促使他們成立社會組織,以保留少數族群的傳統和文化,並推動他們融入主流社會,增強作為「新加坡人」的認同感。李顯龍總理就曾專門出席了錫克族人所組織的新加坡卡爾薩協會慶祝成立75周年的晚宴。在政府的積極推動和支持下,新加坡社會組織的儀軌已經在一定的地域特色和文化屬性的基礎上,形成了較為完善的帶有制度化色彩的基本規範和價值體系,這對於新加坡社會組織的有序、健康、誠信發展是極具價值的。有一個特別需要注意的現象是,新加坡社會組織基本上兩年一換屆,且一些社會組織已經在實際運作中實現了不連選連任,此舉相對擺脫了社會組織的寡頭治理狀態,提高了組織成員對組織管理的積極性,也使得每一次的換屆儀式顯得更為隆重。就職儀式對於社會組織領導人來說,和歐巴馬擔任美國總統的就職儀式在性質上並無多少差別。
反觀國內部分社會組織建設,由於處在早期發展階段,常常與社會組織開創者的個人魅力掛鉤,一些社會組織嚴重依靠開創者的個人號召力、智慧和才幹,未能形成有效的規範引導和制度建設。鄧飛之於「免費午餐」、坤叔之於「東莞市千分一公益服務中心」,均或多或少與他們的個人精神魅力、社會號召力有很大關係。這也是社會組織或公益事業草創期的一種特色。在這一方面轉型較好的有兩個典型:「阿拉善see生態協會「和」壹基金「。前者從一開始就實現了組織建設的規範化,每一屆的會長、監事長、章程委員會主席都由較為激烈的選舉產生,王石、任志強、馮侖等名人雖發揮了一定的魅力作用,但通過選舉機制和協商機制逐步調和,新的領導者不斷成長;後者則通過組織的發展和規範化逐漸從李連杰的個人精神魅力主導中擺脫出來,公共性、社會性日趨明顯。但是,即便如此,這些國內較為知名的社會組織,在儀軌上多是靠個人之間的口才、知名度、信任度等。對於社會組織的長期發展來說,縱然可以維持,但要進一步發展,一個能夠帶來神聖感、莊嚴感、使命感的儀式規範還是有必要的,這是組織走向良性發展和穩定發展的必然要求。
儀軌建設只是社會組織發展的一個環節,這些看起來似乎有點「虛」的程序其實一點也不「虛」。多一點道義上的肯定、精神上的約束,多一點莊嚴和神聖,值得借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