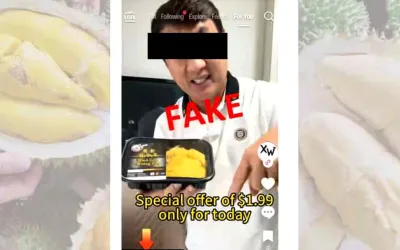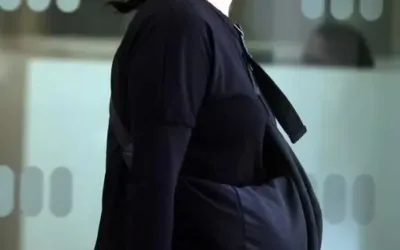產業重生:從 「無人問津」 到 「兵家必爭」
在新加坡國家體育場 Lady Gaga 演唱會的熱潮之外,這個城市國家正以另一種方式吸引全球目光 —— 作為全球半導體供應鏈的關鍵節點,新加坡正經歷著從 「夕陽產業」 到 「戰略要地」 的驚人蛻變。
2018 年以前,新加坡半導體業一度被視為 「明日黃花」。新加坡半導體工業協會(SSIA)執行董事洪瑋盛回憶:「當時去學校演講,一個班級的出席人數不到 10 人。」
然而,中美貿易摩擦與新冠疫情徹底改變了這一局面。美國對中國半導體加征關稅,全球汽車業因晶片短缺在 2021 年損失超 2610 億新元,促使產業鏈加速 「去風險」 布局。
現如今,
全球每 10 片晶片就有 1 片在新加坡生產,
半導體設備產量占全球 1/5,
行業占 GDP 近 6%,
雇用超 3.5 萬人,
成為新加坡經濟的 「隱形支柱」。
六十年積澱
從組裝代工到技術高地的攀升
新加坡半導體的崛起始於 1968 年美國國家半導體的首次設廠,隨後 Fairchild、德州儀器等巨頭陸續落地,奠定了封裝測試的產業基礎。

1980 年代,本土企業特許半導體(Chartered Semiconductor)成立,建成首座晶圓廠,一度躋身全球第三大晶圓製造商。儘管特許半導體 2009 年被格芯收購,但其培養的技術人才與產業生態,為後續發展埋下伏筆。
如今,新加坡以 22 納米製程為主力(聯電 50 億美元新廠今年 4 月啟用),同時聚焦未來技術:
先進封裝技術:美光科技投資 70 億美元建設高頻寬記憶體(HBM)封裝廠,格芯、世創電子等擴產計劃合計超 180 億新元;
矽光子技術:新科研衍生公司先進微晶圓(AMF)專注矽光子晶片,對標英特爾,商業模式類似台積電,瞄準 AI、數據中心與量子計算市場,預計 2029 年相關市場規模將達 8.63 億美元,年增率 45%。
AI 時代的新戰場
新加坡能否孕育 「下一個台積電」?

面對 AI、電動車、5G 等新興需求,新加坡正以 「雙軌策略」 搶占先機:
(一)跨國巨頭錨定未來
恩智浦、世界先進等企業在新建設 12 英寸晶圓廠,聚焦汽車晶片(恩智浦全球市占率 11%);美光的 HBM 封裝廠將滿足 AI 對高帶寬存儲的需求,預計 2027 年量產。這些項目不僅帶來投資,更引入量產經驗與市場洞見。
(二)本土創新瞄準細分賽道
先進微晶圓(AMF):作為新加坡 「矽光子技術先鋒」,AMF 以 「純技術專注」 差異化競爭,客戶涵蓋電信、大語言模型領域,試圖在光子晶片賽道實現 「換道超車」;
恩必創新(MPics):由特許半導體前員工林國強創立,聚焦電動車電源管理晶片,以 「百萬分之三不良率」 的嚴苛標準打入歐美供應鏈,對標博通等巨頭。
(三)政策護航與生態構建
新加坡經濟發展局通過 「製造業 2030」 願景強化產業定位,新科研(A*STAR)則聚焦未來 3-5 年技術,如矽光子與先進封裝。2025 年東南亞國際半導體展(SEMICON)即將開幕,600 余家企業參展,凸顯新加坡作為區域樞紐的吸引力。
挑戰與機遇
在 「友岸外包」 中鞏固地位

儘管新加坡半導體業由跨國企業主導,但地緣政治為其創造獨特機遇。企業從「成本優先」轉向「供應鏈韌性優先」,新加坡穩定的商業環境與技術生態成為『「友岸外包」首選。
數據顯示,新加坡 2023 年對美半導體出口占比 16.6%,雖面臨潛在關稅風險,但 「雙源採購」 趨勢下,其作為 「中立節點」 的價值持續提升。
然而,本土企業仍需突破 「設計 - 製造」 生態短板。洪瑋盛坦言:「新加坡缺乏大量晶片設計公司與下游需求,這是歷史瓶頸。」 但 AI 時代帶來新變量 —— 先進微晶圓的賈格迪什相信:「20 年前難以想像,但今天的新加坡已具備孕育世界級半導體公司的土壤。」
人才回流與產業信心
從 「冷門行業」 到 「朝陽領域」
曾經 「無人問津」 的行業,如今重現吸引力。洪瑋盛現在去學校演講,場場爆滿:「年輕一代看到半導體在 AI、電動車中的核心地位,願意投身其中。」 這種信心源於產業的 「雙重確定性」—— 既有跨國巨頭的穩定需求,又有本土創新的上升空間。
從 1968 年的首家工廠到 2025 年的技術競逐,新加坡半導體業用六十年完成從 「代工基地」 到 「創新樞紐」 的躍遷。
在 AI 重塑全球產業鏈的今天,這個城市國家正以 「矽光子」 與 「先進封裝」 為支點,撬動下一個十年的增長奇蹟。正如林國強所言:「我們只有 3-5 年窗口,但新加坡的技術積累與戰略定位,值得押注未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