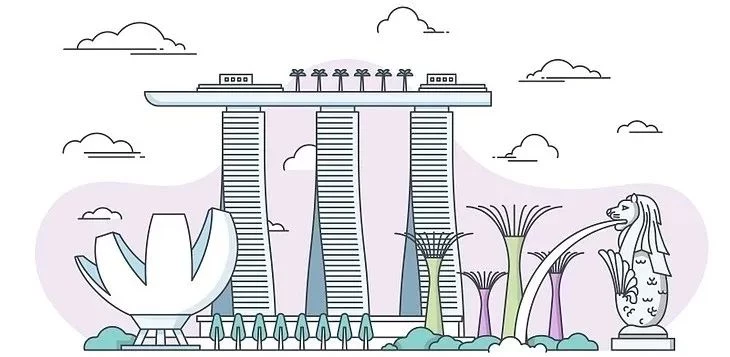2000年,新加坡踏上了成為生物技術中心的征程,當時當地政府在所謂的「國家生物醫學科學戰略」中將生物醫學研究定為該城邦經濟的「第四支柱」。根據該倡議,新加坡於 2003 年建立了 Biopolis,一個定製的生物醫學研發中心。
20年來,數十億美元被投入到生命科學領域,新的研究機構政府機構相繼成立,大大小小的生物製藥公司安家落戶,即使如此,新加坡依舊需要一個轟動生物技術領域的大事件。
生物技術投資者Christopher Tan表示:「投資機構已經進行了長期的投資,投資人們已經看了成功的早期萌芽,這是一個漫長的旅程,我們依舊在等待真正的主角登場。」
資本的試探 01
新加坡連續創業者Guy Heathers表示,雖然政府一直大力宣傳生物藥的開發,但私人投資方依舊在試探的邊緣徘徊。新加坡的生物技術經歷了突破,同時也充斥著失敗。
Tessa Therapeutics一度被認為將成為細胞治療領域的領導者,曾於2017年底和2018年4月完成由淡馬錫領投的總計1.3億美元融資,去年更是獲得1.26億融資,總額超過2.5億美元,卻在一個月前宣布關閉,Tessa 業務開發前任副總裁Heathers表示,這無疑是會給新加坡當地的生物技術生態系統帶來負面情緒。
除此之外,癌症治療的中期公司AUM Biosciences宣布與 Mountain Crest Acquisition Corp 合併上市計劃終止對於新加坡生物技術領域造成的第二次打擊。
Heathers對此表示擔心,通常來講,被製藥公司收購或在納斯達克上市這些真正能為投資者賺錢的例子發生才更真實地吸引到投資者。
若將成功定義為一種藥物在美國獲得批准,那麼新加坡就有一個這樣的案例。去年,CTI生物製藥公司獲得了美國食品藥品監督管理局批准,將JAK抑制劑Vonjo作為骨髓纖維化的治療藥物。該分子最初由新加坡生物技術公司S*BIO開發,該公司早已不復存在。
新加坡科學技術研究局 (A*STAR)執行長Damian O'Connell表示:一次性具有全球影響力的產品獲批是不夠的,新加坡需要成為一個「連續贏家」,擁有大量類似的積極消息,才能讓人們真正認識到它在整個藥品生態系統中的地位,現在只需要取得更多成功的時間。
最有前途的新加坡生物科技公司的接力棒似乎已經交給了 Hummingbird Bioscience,該公司在2021年由Novo Holdings領投的C輪融資中籌集了1.25億美元,引起了轟動。目前,Hummingbird正在開發針對癌症和自身免疫性疾病的抗體藥物,達到了臨床一期。納斯達克上市公司Aslan Pharmaceuticals參與了濕疹候選藥物eblasakimab的競爭,該藥物剛剛發布了2期結果。
不斷發展的生物技術中心 02
Tessa時任執行長Thomas Willemsen在5月份接受Fierce Biotrech採訪時表示,新加坡在早期研究方面積累了豐富的經驗,但要成為一家成熟的生物技術中心仍需要更多的後期商業化經驗。A*STAR 生物醫學研究委員會執行董事 Benjamin Toh 回憶道,許多科學家也只考慮發表論文。
Toh 說,科學家們的心態發生了轉變,開始考慮將科學轉化為產品和生物技術衍生產品。隨著時間的推移,人們開始認識到生物科技公司的價值,隨著經濟的成熟和房地產市場的降溫,投資者也開始尋找替代投資。
根據SGInnovate 和 LEK Consulting最近的一份報告,如果不計算大型製藥公司在當地的辦事處,新加坡生物技術公司的數量已從2012年的7家增加到2022年的52家。但只有三家公司處於商業階段,其中一家專注於生物仿製藥;其中兩個處於臨床3期,其中包括Tessa。其規模與擁有1,000多家生物製藥公司的波士頓地區根本無法相提並論。
也許新加坡不應該與波士頓並列比較。這個島國面積只有約280平方英里,人口不到550萬。大波士頓地區本身居住著約 500 萬人,其面積是新加坡的五倍。
對於Heathers來說,20 家成功的生物技術公司足以算得上這個島嶼的規模能否擁有一個成功的生態系統。但新加坡仍需要在全球生態系統的生物技術中心中確立自己的地位。
A* STAR旗下創新企業集團執行董事Irene Cheong表示,目前,核酸治療、生物加工以及細胞和基因治療是新加坡選擇深入研究的領域之一。

文章參考
https://www.fiercebiotech.com/biotech/vistagens-stock-skyrockets-1272-after-social-anxiety-nasal-spray-hits-phase-3-trial-goal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