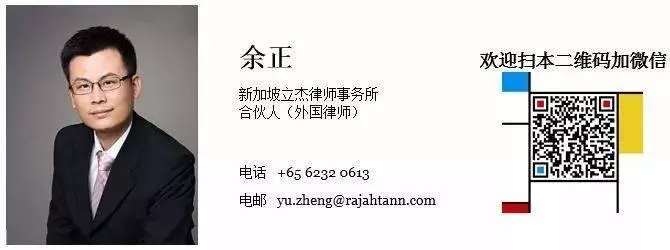2019年9月18日,新加坡高院在Heince Tombak Simanjuntak and others v PaulusTannos and others [2019] SGHC 216 ("Heince")的案子裡承認印度尼西亞雅加達地方法院商業法庭所判的個人破產令。這是新加坡法院第一次探討對於認可外國法庭判下的個人破產令的法律原則。
案情
2017年,印尼法庭宣判被申請人Paulus Tannos等4人的破產令。由於被申請人在新加坡有許多財產,申請人Heince Tombak 等人作為破產接管人和管理人(Receivers and Managers)在2018年向新加坡高院申請認可印尼個人破產令,允許接管人管理、實現和分配被申請人在新加坡的財產。被申請人而向法院請求駁回申請人的申請。
新加坡在2017年採納了《聯合國貿易法委員會跨國界破產示範法》(UNCITRAL Model Law on Cross-Border Insolvency) ("跨國破產示範法")。新加坡高院首先審議了目前的申請是否屬於跨國破產示範法的管轄範圍。新加坡高院解釋跨國破產示範法在新加坡的實施制度下只限於公司破產清盤,而不牽涉到個人破產。所以,對於外國個人破產令,若要在新加坡受法庭的認可,必須以新加坡普通法的法律原則做出申請和後續判決。
新加坡法庭認為,認可外國個人破產令的普通法原則和承認一般外國判決的原則是一樣的。只有在符合下列條件下,新加坡法院才會承認外國個人破產令:
1. 外國破產令必須由具有管轄權的外國法院作出。該外國法院的管轄權必須源於以下理由:
a. 該外國法院位於債務人的住所地;或
b. 債務人已認可或服從該法庭的管轄權,比如:債務人事先簽訂的管轄權協議、債務人參與外國訴訟(提出管轄權異議除外)。
2. 外國破產令必須是最終和決定性的。
3. 對於個人破產令的承認不存在特殊的抗辯理由。這些抗辯理由,主要包括:外國訴訟程序違反自然公正、承認執行外國判決損害新加坡的公共政策。
在Heince案子裡,四名被申請人都是印尼公民,這些人通過他們的印尼律師參與了印尼法院的庭審程序。新加坡法院進一步評述道,即使被申請人都不是印尼公民,他們委託律師參與印尼庭審程序的行為,就等於接受認可了印尼法院的管轄權。因此,印尼法院是有管轄權的法院。
在這案子裡,雙方的爭議在於印尼法院的個人破產令是否是最終的。若一個判令正被上訴到更高的法院,而暫時不能執行這個判令,那這判令不算是最終的。雖然被申請人拿出許多和印尼法院溝通的文件來主張破產令正在上訴,新加坡高院認為這些證據沒有顯示被申請人正式提出了上訴。在這情況下,新加坡法院認為印尼法院的個人破產令是最終和決定性的。
被申請人對於印尼破產令的承認也提出了3個抗辯原因:
1. 獲得個人破產令的庭審程序違反了自然正義;
2. 構成個人破產令的基礎交易文件(個人保函)是以欺詐行為獲得的;和
3. 個人破產令由申請人欺騙性的執行。
新加坡高院審核證據後,認為證據不足,無法證明存在違反自然正義和欺詐的情形,駁回被申請人的抗辯,最終承認了印尼法院的個人破產令。
最後,新加坡高院考慮了國與國之間承認執行司法判決的互惠原則(principle of reciprocity)。新加坡高院認為,雖然有些國家的法院(如印尼)會以互惠原則為主要考量來判斷是否承認外國法院的判令,新加坡一向以來都不是以互惠原則來承認外國判令,而是某種普惠原則。也就是說,不管外國法院是否承認執行新加坡的司法判決,新加坡都會承認執行外國的司法判決。這是一段很有意思的評論。表面上看,新加坡單方面的採用普惠原則,似乎在國際交往中會比較吃虧。但筆者認為,實際上卻並非如此。這是因為,在互惠原則下,總需要有一個國家首先承認外國的司法判決,這才能啟動互惠關係。倘若所有國家都要等其他國家先承認自己的司法判決,這就永遠無法出現互惠關係。可以說,正是因為有了Heince這個案例,這才給印尼法院在未來根據互惠原則承認新加坡的破產令創造了條件。只要存在這樣的條件,就會有商人和律師努力尋求實現它的機會。國際商業活動強烈需要各國之間互相承認執行彼此的商事司法判決。在這種強大力量的推動下,以互惠原則為基礎的大陸法系國家,將越來越多地承認和執行新加坡的司法判決。
總結
Heince案子裡,新加坡高院清楚的解釋了承認外國個人破產令的原則。只要個人破產令出於有管轄權的法院,個人破產令是最終的和決定性的,而對於個人破產令的承認別無抗辯原因,新加坡的法院就會承認外國個人破產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