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紅螞蟻鮮少看新加坡電視劇,第一部是2002年的《小孩不笨》,第二部是2021年由白薇秀主演的英語連續劇《最後的夫人》,第三部則是最近播出的電視劇《小娘惹之翡翠山》(簡稱《翡翠山》)。
少看本地劇的原因,一來是「外來」劇集選擇豐富,二來覺得本地劇往往劇情套路、演技不夠出彩。
這次之所以點開《翡翠山》,除了身邊朋友力薦,也因為它在Netflix本地電視榜高居第一,於是決定跟風一看。
雖然這部劇集的劇情確實有點狗血,但《翡翠山》讓紅螞蟻印象深刻的,是顛覆了對本地演員演技的既定印象,黃暄婷飾演的「張安娜」,演得真是夠毒夠賤。
張安娜自小因八字不合被送到外婆家,十歲才回到翡翠山。小時候外表乖巧,實則心機深重:年紀輕輕就會在樓梯上潑油陷害懷孕的二伯母,之後又把二伯母收養的「心娘」視為眼中釘。
長大後她更是不加掩飾,自稱「災星」,發誓要在張家當個唯恐天下不亂的存在。她慫恿堂妹張安雅(黃晶玲飾)復仇妓院,設計陷害闊少黃祖業,死纏爛打要逼對方娶她。
最後兩集劇情癲狂到底。她開槍射殺解除婚約的「郭志邦」,放火燒死兩個親哥哥,還妄圖讓心娘與祖業陪葬。
紅螞蟻一直以為張安娜這個反派角色的心態扭曲,是成長環境造成的,拜她那歹毒父親與盲寵母親所賜。
然而,《翡翠山》的大結局劇情卻出現大轉彎。
張安娜追殺祖業失敗,企圖跳樓輕生未遂後被救,並被診斷患有精神分裂症,最終被送進精神病院終老一生。
安娜確診精神分裂症劇情缺乏鋪墊,加深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

《聯合早報》舉辦「娛樂投票」,讓讀者投選最討厭的《翡翠山》中的反派角色,由張安娜高票當選。(新傳媒)
劇中從未交代張安娜究竟是在何時患上精神分裂症。她是自小就已出現病徵,還是在接連挫敗後才逐漸發病?
她在無法拆散祖業與心娘的感情後,又被郭志邦悔婚選擇了安雅,這一連串打擊是否觸發她最終的精神崩潰?
劇情的這些轉折缺乏鋪墊,讓人質疑其設定是否合理,甚至可能誤導大眾,把「精神分裂症」等同於「邪惡行為」,無形中加深對精神病患者的污名。
心理衛生學院高級精神科顧問醫生鄧鈺錚認為,《翡翠山》中對角色的處理不當,可能加深公眾對精神分裂症的誤解與污名化。他特此投稿至《聯合早報》和《海峽時報》,藉此向觀眾科普精神分裂症,希望大眾可以正確地看待精神疾病患者。
他說,精神分裂症是一種嚴重的精神障礙,其症狀包括幻覺、妄想、思維混亂、社交退縮和認知困難等表現。
劇中主要反派張安娜雖被診斷精神分裂症,卻缺乏相應症狀的描寫,其行為更偏向心術不正、處心積慮。
鄧醫生提醒,把精神疾病與邪惡行為畫上等號,不僅會誤導公眾,也會加劇人們對患者的偏見,使他們不敢求助、延誤治療,阻礙康復之路。
事實上,許多編劇與演員在詮釋特殊角色時,都會請教專業人士。例如,金馬影帝吳慷仁為了演好《富都青年》中無證移工的角色,曾親自到吉隆坡富都巴剎打工,跟著攤販送貨、殺雞,只為真實還原角色處境。
鄧鈺錚呼籲內容創作者在描繪精神病患時,應主動諮詢心理健康專家,確保劇情真實可信、富有同理心,同時也履行媒體責任,提升公眾對心理疾病的認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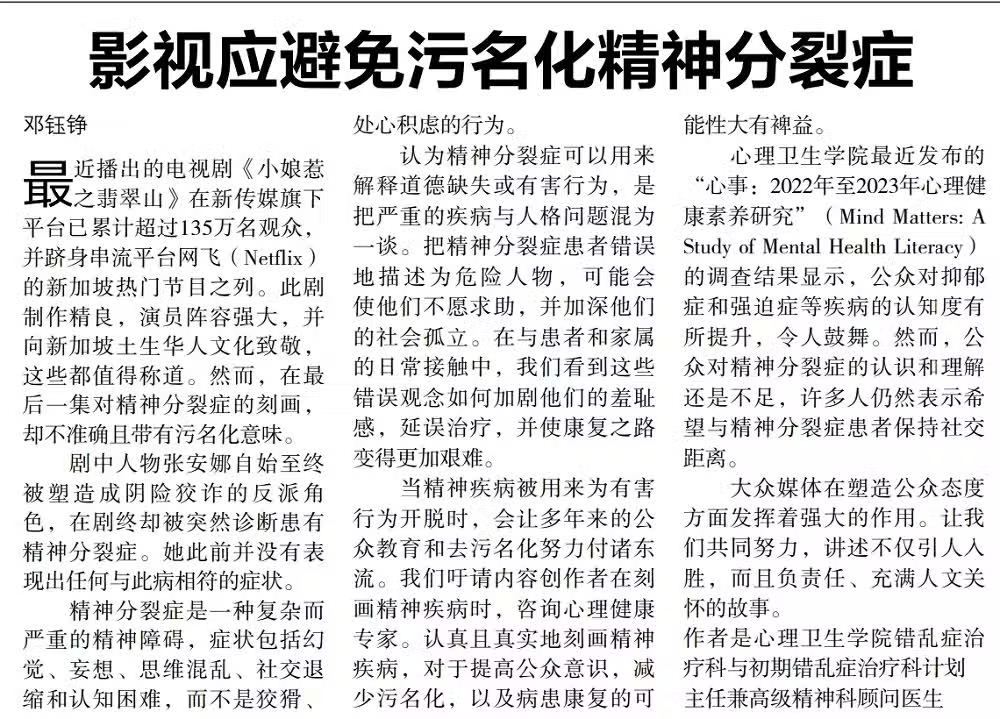
刊登在5月8日《聯合早報》的言論版。
精神分裂症(schizophrenia,又稱思覺失調症)是一種慢性嚴重精神疾病,會影響人們的思維、感覺和行為。
據2016年新加坡心理健康調查,新加坡每116人當中就有一人患精神分裂症。
造成精神分裂的具體原因至今尚不清楚。精神分裂症的發病確切原因也尚不清楚,但可能與遺傳、生理、心理和社會因素等有關,這些因素會增加個人患上精神分裂症的風險。
近年來,免疫系統變化與精神健康問題之間的聯繫,逐漸成為研究熱點。
精神分裂症患者面對的症狀大致可分為陽性症狀和陰性症狀。
心理衛生學院錯亂症精神科部門精神科顧問陳震霆醫生早前接受《聯合早報》採訪時解釋,陽性症狀即出現幻覺,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會聽到或看到別人見不到的東西或開始妄想,他們開始堅定地對某事物偏執固定的信念,而且這種信念是基於一種奇怪或錯誤的觀點。
而陰性症狀,則表現為對生活和活動失去興趣,更多地孤立自己,並與社會隔絕和他人保持距離。
絕大部分精神分裂症患者發病時缺乏病識感,讓病人配合就醫非常困難。這是由於精神分裂症患者並不會認同自己所出現的症狀是不正常的,因此他們可能認為自己並沒有必要看醫生,更不願意接受治療,而導致病情加劇或惡化。
精神分裂症患者須接受長期治療,包括服用抗精神病藥物,許多患者還可從心理學家和職能治療師的幫助與支持中受益。
精神分裂症患者若不接受適當治療,可能嚴重影響病人的情緒、行為,以及日常生活,還可能導致抑鬱症、焦慮症等併發症,引起藥物濫用、輟學、失業、社會孤立等,甚至萌生自殺念頭。
陳震霆醫生說,精神分裂症患者可能感覺抑鬱,甚至對生活失去盼望,這將導致症狀複雜化。
精神疾病並不等同於道德缺陷,更不該成為「反派人設」的懶惰解釋。我們固然希望影視作品的劇情與演技引人入勝,但也期望在人物塑造時,能夠帶有更深的責任感和社會意識。
張安娜的故事或許已經落幕,但精神分裂症患者每天仍在與疾病抗爭。
他們不需要更多誤解,而是更大的理解與支持。更真實、更多元、更有同理心的角色敘事,才能為精神健康議題打開更寬廣的公共空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