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提到新加坡,人們都會認為他是一個奇蹟,不僅經濟繁榮,而且政治穩定,人民生活富裕幸福。根據世界貨幣組織的統計,2022年新加坡人均GDP達82808美元,高居世界第六位,還在美國、英國、德國等老牌資本主義國家之前。而新加坡1965年才獨立成一個國家,更神奇的是,新加坡幾乎完全是被動地獨立的。因為新加坡本來是馬來西亞的一部分,1963年9月,馬來西亞從英國治下獨立時包括新加坡、英屬婆羅洲地區,以及半島上的馬來亞聯合邦。
但是,馬來西亞的領導人對於合併後新加坡華人的數量及潛在勢力深感憂慮。兩年的合併以失敗告終。新加坡的華人人口龐大,具有巨大的潛在力量,這讓馬來西亞的領導人對於新加坡的加入憂心忡忡,馬來人不願意被華人統治。於是,從未向馬來西亞爭取獨立的新加坡被馬來西亞踢了出來,被迫成為一個獨立的國家。
當時,世界上幾乎所有人都不看好新加坡的未來,這個連淡水資源都無法自給的國家看上去搖搖欲墜、危在旦夕。英國著名歷史學家阿諾德-湯因比在1969年寫道,他認為剛獨立的新加坡是不大可能維持下去的,「這個主權獨立的城邦......作為一個政體卻小得不切實際」(新加坡國土面積僅733平方公里,甚至不如中國大多數縣的面積大)。對投資者而言,新加坡這個地方毫無吸引力,很多人把新加坡視為「一個位處日益排外的區域、隨時可能會爆發動亂的外來飛地」。
然而,新加坡不僅頑強的生存了下來,而且創造了舉世矚目的奇蹟,成為全世界讚揚、學習的對象。許多國家欽佩新加坡的成就,有些更試圖效仿,視之為發展典範。杜拜遵從新加坡的商業模式,喬治亞總統米哈伊爾·薩卡什維利(Mikhail Saakashvili)曾標榜本國是「融入新加坡元素的瑞士」",和新加坡一樣是海洋戰略樞紐的巴拿馬盼望在未來成為「中美洲的新加坡」"。中國的某個市長也向新加坡學習,植樹造林、治理污染,並「對投訴計程車司機不文明行為的市民予以獎勵。
那麼,是什麼原因使得新加坡成功?
有人說,是新加坡沿襲了英國人留下的憲政民主制度,新加坡將開闢新加坡殖民地的英國人萊佛士作為重要人物紀念,新加坡許多的建築物、私人機構、街道和百年名校都是以他的名字命名,比如東華大學萊佛士國際設計學院、萊佛士廣場、萊佛士書院、萊佛士醫院、萊佛士酒店和萊佛士網絡超市、史丹福路等等。李光耀不僅沒有批判英國的殖民史,反而引以為豪,讓它成為新加坡故事的積極一面。

所以,如新加坡自己認為的一樣,不能否認英國殖民沿襲英國制度對於新加坡成功的影響,但是這是唯一因素嗎?如果沿襲一個好的制度就可以成功,那為什麼同為馬來半島且也是前英國殖民地的馬來西亞,以及前美國殖民地,幾乎照搬了美國制度的菲律賓沒有成功?2022年馬來西亞人均GDP僅12364美元,僅新加坡的七分之一多一點。而菲律賓更是只有可憐的3623美元,連新加坡的二十分之一都不到。
如果從1965年新加坡獨立的時候算起,當時馬來西亞是1804(國際元),而新加坡是2667( 國際元),菲律賓是1631(國際元),可以說差距並不大,尤其是菲律賓,當時GDP是新加坡的61%,而到了2022年僅有新加坡的4.4%,這個差距可謂天壤之別。
如果不僅是制度因素甚至制度不是決定因素,那麼到底還有其它什麼因素決定了新加坡的崛起?
這裡,就不得不提到一個人:李光耀,以及他身邊的領導團隊。幾乎所有研究新加坡崛起秘訣的人,都不得不承認:如果沒有李光耀,就不會有新加坡的今天。在新加坡獨立後很長一段時間,都是李光耀操控著新加坡這艘巨輪,在風狂雨驟的世界大潮中迎風破浪,披荊斬棘,守正出奇,穩步前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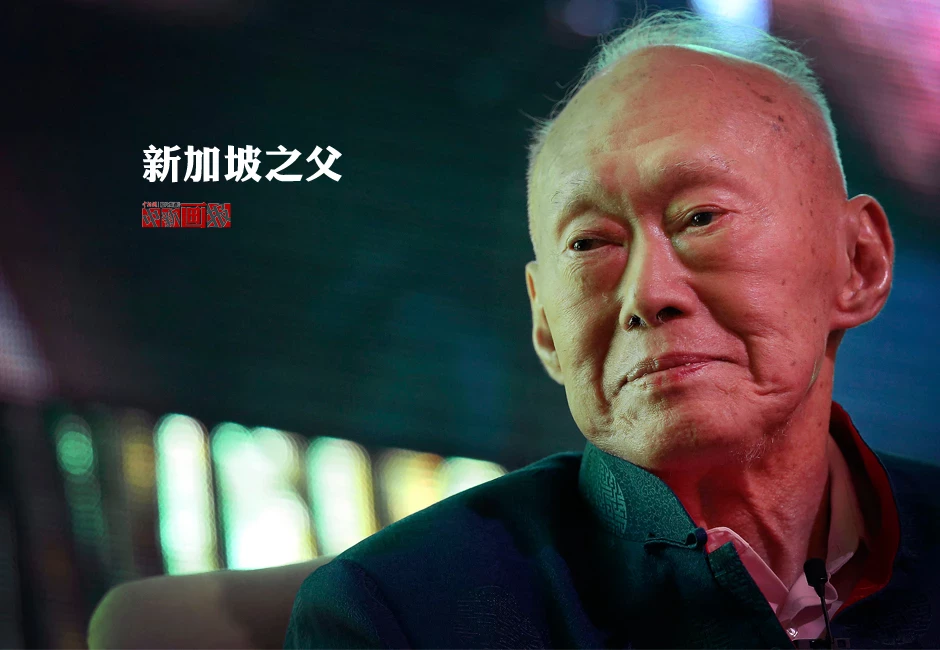
50年代末,新加坡出現了一個極力爭取獨立(是從英國殖民統治下爭取整個馬來半島的獨立)的新政治團體——人民行動黨。兩個政治領袖形成不穩固的同盟:一位是年輕激昂的律師李光耀,及其所領導的講英語的溫和派人士,另一位是英俊有魅力、能言善道的林清祥,及其所帶領的左派人士。李光耀16歲進萊佛士學院,在那裡主修經濟學,後來在英國讀書四年,先在倫敦經濟學院主修經濟學,後來到劍僑大學修讀法律,他在英國能夠理論與實踐並重,他鑽研英國政治傳統的經典作品,同時學習辯論的藝術。後來回到新加坡,他先是以律師,後以政治家的身份,將他全部所學付諸實踐。
與李光耀共事的另一名新加坡領袖是信那談比-拉惹諾南。他是一名出生於斯里蘭卡的泰米爾人,早年曾在馬來亞生活。他深諳這種文化,他是人民行動黨領導層這個精英圈子中唯一的非華人。拉惹諾南對一黨專政的好處深信不疑,認為這樣「要比被反對黨騷擾,做起事來能更加獨立(且更有效率)。
拉惹諾南雖然不是華人,但他恪守儒家「反對等於犯上」的信條,認為政府站在絕對的道德高地上,政府的合法性來源於其道德的優越性。他主張所有經歷現代化的社會都必須做出犧牲,而國會和工會對新加坡來說是一種負擔不起的奢侈品。政治權力與經濟特權必須讓步給專制統治者設計推行的理性且高效的政策,而政治精英也無需向公眾輿論負責。
李光耀和他的人民行動黨背離了社會公義、民主制度和社會主義,反而走向了威權主義,他們更加認定這一戰略最有利於經濟發展,而這是新加坡賴以生存的根本。
李光耀和他的團隊宣稱,他們追求的不只是工人的福利,而是整個國家的福利。他成功地建立一個受到嚴密監管的一黨制威權國家,而他一人手握大權。他的能力勝過了魅力,政治環境也因而相對穩定。新加坡沒能出現一個能夠與之抗衡的反對黨,新加坡的重心從政治轉向了經濟。
在李光耀的堅定領導下,所有精心設計的政策都被有效地執行,一個重視經濟發展的高度集權的官僚體制開始成型,政府成為改革的先鋒,代表人民行動,認為人民的願望即是擁有舒適的生活,以及由理性務實的治理所帶來的政治穩定,新加坡人民最喜歡追求的是美食和購物,所以他們與政府站在同一戰線,讓李光耀的人民行動黨在每屆大選中一直取得壓倒性勝利。
毫無疑問,新加坡決心把英語定為第一語言的做法,緩和了其與世界先進國家的關係。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中,新加坡得益於它作為一個國際性多語社會的身份。當地華人可以帶頭招募來香港和台灣的資本。馬來人可以連接伊斯蘭社群。事實證明,強調國際化的海事傳統(包括海港生活及與其相關的一切),對向成為一個全球化都市的新加坡而言,是一個巨大的潛在資產。
李光耀及其他領導人所說的價值觀有一部分源自儒家傳統,但是他們是有選擇地看待儒家這一高度複雜的中國古老社會哲學。與中國的儒家社會一樣,新加坡特別重視等級制度和人倫關,但是不同之處在於新加坡熱衷於管理,執著於持續不斷的測量、分類和量化(這是西方管理方法)。在新加坡的儒家世界裡,精英階層是選自最聰明、最有活力、受過高等教育的人,並且經過一層層的篩選和淘汰。這和中國古代的科舉考試有非常相似的地方,只不過新中坡的官員篩選不注重詩文能力,而是政治與經濟的管理能力。在新加坡看來,執政黨的合法性在於其所取得的經濟成功,而非藝術成就。
李光耀和他的團隊認為,帝制中國的傳統中蘊含了亞洲「文化穩定因素」的基礎,那是可從自身文化汲取的核心理念,新加坡政府發起了一場「亞洲價值觀」的運動,試圖闡明新加坡成功的原因,並為有時不得不採取的高壓手段辯護。事實上,新加坡政府所採取的社會契約與帝制中國並無二致,政府通過優越的執政表現來證明其統治的合法性,只要人民的生活過得好,他們便會接受這種合法性的假設。
新加坡對中國的「亞洲」認同無疑植根於中國近年來在國際上的崛起,以及新加坡占主導地位的華人人口。因此,新加坡很重視華人文化氛圍的歷史古蹟,諸如虎豹別墅、孫中山南海紀念館,以及華裔館等,都得到了建造或者修繕。

由於政治原因,普通話(官話)在19世紀末傳入新加坡,反映了中國人團結一致、聯合支持中國國內的革命事業的願望。一個世紀後,普通話變得更有吸引力,因為它能開啟中華人民共和國所提供的商業與文化機會。新加坡呼籲全體華人把普通話作為第一語言或第二語言來學習。在政府眼中,亞洲語言,尤其是普通話,具有另一個優勢,即作為「文化壓艙石」,用以抵抗過度「西化」浪潮的文化價值觀。這建立在語言形成價值觀的假設之上。」當政府對「西方」文化的批評愈加嚴厲,這一想法便得到更多的重視。
很多人對於新加坡是否是一個民主國家持有爭議。在獨立後最初的幾十年,新加坡政府在結構上類似民主制度,但它的操作模式並不民主。對李光耀及其領導班子而言,好政府要比民主更重要。誠然,新加坡定期舉行選舉,但大多數新加坡人忠實地投給了人民行動黨。參選人都是經過精挑細選,擁有豐富的學術履歷。新加坡政府不受利益團體的制約,因而能夠提出穩定且前後一致的政策。新加坡政府的效率和廉潔度幾乎無可指摘。
為了追求現代性,新加坡將紀律和禮議放在藝術和民主之上。藝術被視為凌亂、張揚且離經判道,而民主則被視為混亂不堪。馬凱碩是亞洲價值的重要支持者,他的論證思路可以如是概括:一個發展中社會必須先成功取得經濟發展,然後才能實現已開發國家所享有的社會與政治自由。不過問題在於,這個關鍵點到什麼時候才能發生?

總結起來,新加坡能成功取決於以下這些要素:不斷進步的海事技術、地理位置、馬來文化遺產、英國法律與幹勁十足的華人企業家的成功結合、有才華的領導班子,以及好運氣。新加坡已經在當代世界脫穎而出,成為物質成功和秩序的隱喻,但是它還沒有建立一套有利於創造性破壞和生成新想法的制度,這是新加坡的最大挑戰。新加坡顯然在高峰期抓住了時機,天時、地利、人和成就了今日的新加坡。但新加坡不會完工,如美國科學家和實業家埃德溫-蘭德所言「天堂才是底線」,然而天國顯然永遠不會到來。
但至少,現在新加坡已經定義了成功,而我們每一個國家,每一個人,也在努力定義自己的成功。那我們的成功之路又如何走?至少,新加坡給我們提供了一面很好的鏡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