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亚洲思想家系列(Asia Thinker Series)的特别活动在2022年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2022年思想之节庆(Festival of Ideas)举办,活动生动探讨了在这个深度科技化的时代,公共政策制定如何以全新、独特且深刻的方式影响人们的生活方式和质量。
参与讨论和分析这一问题的嘉宾大多来自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LKYSPP),其中包括李嘉诚公共管理学教授兼环境与可持续发展研究所(Initiative on Environment and Sustainability,IES)所长Benjamin Cashore、高级研究员黄国和博士(Ng Kok Hoe)、助理教授Sreeja Nair博士以及副教授吴木銮博士(Alfred Wu)。而来自韩国开发研究院国际政策大学院(KDI School of Public Policy and Management)的王顺教授(Shun Wang)也参与了讨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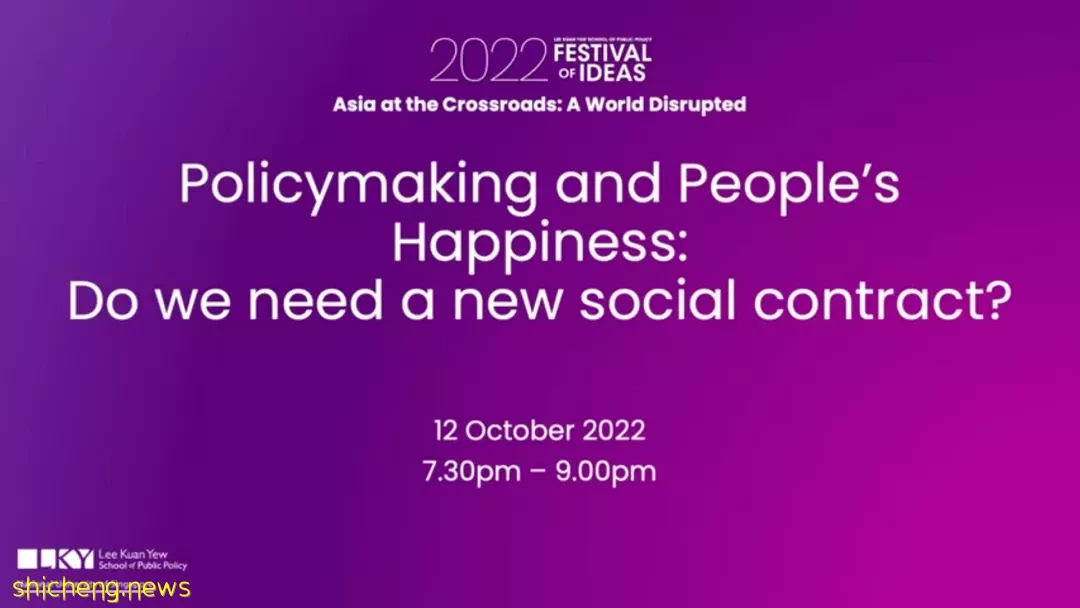
近几年在全球肆虐的新冠疫情、快速的数字化转型以及民众态度和意识方面的变化都影响了政府和政策制定者开展公共政策工作。为了满足选民与时俱进的对政治、气候、经济和社会的期望,政府需要更加全面地考量以制定出更具包容性的政策。但这样的社会契约能让民众感到幸福吗?

担任本次讨论会主持人的Cashore教授指出:“在过去两年中,新冠疫情扰乱了世界秩序,如今的世界秩序有些混乱,亟待更多的社会关注。从这个角度看来,幸福不仅意味着一个朦胧的概念,也同时是一项衡量经济发展的重要指标。
1 收入与幸福
《世界幸福报告》(World Happiness Report)副主编王顺教授研究幸福经济学已有十多年,他表示:“幸福对人类来说并不是一个新词,但直到最近几十年对这一话题的研究数量才迅速增长。”
从Google Ngram Viewer这一搜索引擎捕捉的搜索频率就可以看出人们对幸福的研究兴趣日益增长:自1990年代中期以来,“收入”的在线搜索量明显下降,而“幸福”的在线搜索量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在学术文献领域同样有所体现。王教授补充道:“早期的经济学过分关注收入,因为收入决定了民众所享受的福利,然而计算国民生产总值(GDP)时不会扣除用于整体福利的各类支出,其中的一些支出,如用于治理空气污染和控制犯罪的支出,则让民众产生了消极情绪。”

王教授指出,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创立的能力方法(Capability Approach)作为评判经济发展的标准早期限制颇多,后来该方法被改进为人类发展指数(Human Development Index,HDI),将人均国民收入、教育和健康三项指标纳入其中,以便更全面地衡量人们的福祉。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研究发现,收入和幸福之间的相关性随着经济的长期增长而下降。王教授表示:“通过吸取过去的研究经验,我们发现除了收入,还有许多其他与民众幸福感相关的决定因素,如经济、政治、社会和物理环境,以及家庭和个人特征。”
“增强国民幸福感是一项重要的公共政策目标。”他强调说,“这对经济分析及提高政府和企业的效率都大有裨益。幸福是一个非常全面的衡量标准,可以提供一个通用的指标,用于比较各个领域的不同结果。”因此,越来越多的人呼吁政策制定者认真严肃地将幸福作为衡量经济发展的标准,并以此制定政策和指导行动。
2 社会包容与社会契约
黄国和博士(Ng Kok Hoe)在社会包容及社会包容如何为公共政策提供机会方面具有丰富的专业知识和大量的研究经验,他解释道:“社会契约有许多定义,但最贴切的定义来自于《我们欠彼此什么》(What We Owe Each Other)这本书,书中提及了管理我们个人和集体生活的规范与规则。我们也可以把社会契约视为国家、市场和家庭之间三方的风险与责任分配。”

黄博士解释说任何社会契约都面临既定的挑战,如人口老龄化、科技进步带来的失业威胁、工作灵活性和临时工的增加。但在新加坡,政府还需要应对新加坡独有的风险问题。这些问题包括:中度到高度的社会不平等、社会流动缓慢、底层人群收入停滞不前、严重依赖在恶劣条件下工作的流动劳动力以及让新加坡养老金制度承受巨大压力的快速老龄化。
黄博士建议从三个方面重新考虑新加坡的社会契约:设定最低收入标准以满足民众基本需求,提高民众工资并扩大社会保障范围来确保其优质的工作氛围,为民众提供足够的培训和经济资助来支持他们实现职业过渡和转型。
3 重建社会契约
Sreeja Nair博士把关于科学、气候和政策制定研究之间的相互作用纳入了讨论范围,也为讨论带来了新的视角。Nair博士概述了善良、同情、感恩和敬畏这四种美德,在她看来,当我们面临战争和民众流离失所、气候变化、心理健康问题、经济不确定性和技术变革所带来的负面影响时,这些美德对个人而言显得尤为重要。
Nair博士表示:“做好充分准备迎接与当前截然不同的未来是一项巨大的挑战,实施新想法还会提高公共管理的难度(就学习成本而言)。因此,政府可以小规模推行新措施,通过试点方案来实施新想法。所以在政府间鼓励政策实验和创新是必不可少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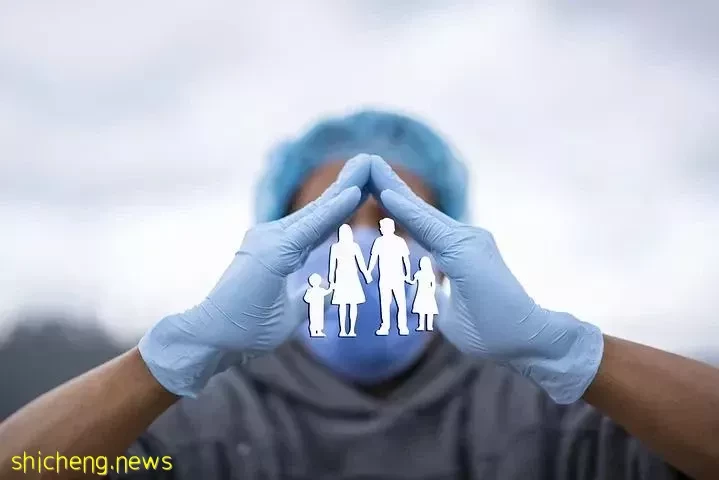
她提出,重新构建社会契约的另一种方法是从代际视角考虑多样性、公平、包容和正义的理念。她呼吁,政府制定的政策不仅应当为社会的大多数人服务,也要关注那些处在社会边缘的群体。
她还提出,人们对自然、环境和自然资源的态度也应纳入考虑范围。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社会不仅需要增加传统的技艺,还需要着重考虑与大自然的关系,这样整个社会都会在重新思考和想像中改善我们与自然的长远关系。
4 社会信任
吴木銮副教授(Alfred Wu)认为,幸福不仅仅关乎生活满意度。吴教授以新冠疫情期间民众和政府的互动为例进行了说明。他指出,在民众和政府之间互动中, 社会信任的重要性在新冠期间更加突出。吴教授在最近进行的研究中得出结论并指出:政府信任与民众心理压力呈负相关,这一现象在老年人群中尤其普遍。“至于未来公共管理领域关于幸福的研究方向,如果未来我们还会抗击此类大流行,那么首先需要研究的就是社会信任。”
5 幸福:概念和说明
鉴于社会契约之间的显著差异,Cashore教授认为,我们需要重新思考 :幸福能否成为衡量社会契约关键概念。也许我们应该考虑使用更精确的概念。
对于王教授而言,幸福的概念已足够宽泛,因为他将幸福描述为一个多维的概念。人们是否幸福取决于自己目前的情绪是积极或消极,而这两种情绪在日常生活中经常互相转换。生活评价和认知方面的幸福则会稳定许多,且与社会、经济、政治和生活环境息息相关。

基于他对贫困和社会包容的研究,黄博士发现,受访者想要达到基本生活水平必须具备以下无形资产:归属感、他人的尊重和自我尊重、安全感、独立、自由和机会,这样才能构建出衡量幸福的全面标准。他指出,安全感、人们的乐观程度以及他们对未来的看法是理解幸福的切入点。
对于这种观点,Cashore教授提出疑问:安全真的与幸福相关吗,又或者安全只是幸福的来源之一。Cashore教授认为,有目标想要改造或改变世界的人生来就很快乐,因为实现更远大的目标会远比实现个人目标更快乐。

Nair博士建议把幸福划分为静态和动态的。她指出:“如今许多幸福的讨论都只关注当下;但在制定政策时,如果你不能做到高瞻远瞩,没有从过去和遗留问题中吸取教训,而是以静止不变的方式看待问题就可能会产生不利影响。”然而,这并非说明幸福作为一个概念是无法实现的。Nair博士解释说,这可能是一把双刃剑,人们也许会对政策制定的某些问题感到沮丧,但也会产生一种使命感,这种使命感可以推动很多行动。
吴副教授最后总结说:“无论是在和平时期还是其他时候,政府都必须积极努力建立社会信任,否则,所有的硬件基础设施和良好的政策都无法转化为更好的战略和方向。”

扫描上方二维码观看本次活动完整讨论
文章来源:Global-Is-Asian,2023年1月16日,星期一
作者:Global-Is-Asian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
本文内容来自于作者,不代表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官方机构观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