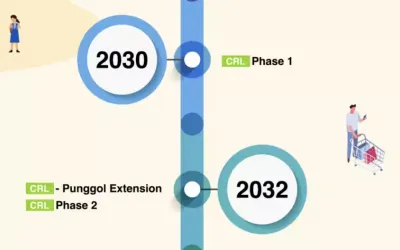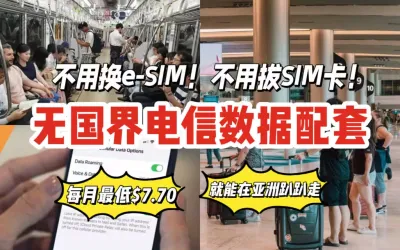刚刚过去的九月里,狮城发生了一件大事:女佣巴蒂案的原审判结果被推翻了。
大多数人可能都会这桩案件有所耳闻,简单概括一下,就是:
廖文良和廖启龙父子于2016年10月30日举报自家印尼女佣巴蒂被辞退时,偷窃价值3万4600新币的DVD播放机、床单、被单、百多件衣物、厨房器皿、名牌包、手表及太阳眼镜等物品;
国家法院法官于2019年3月判巴蒂罪成,坐牢26个月;
巴蒂不服判决,通过律师上诉至高庭;
2020年9月4日,高庭法官陈成安推翻国家法院判决,巴蒂成功洗脱四项偷窃罪名;

整个事件中,女佣巴蒂被起诉—被判坐牢—不服上诉,再到推翻原判,历时接近四年。
小女佣正面迎战大富豪,最终取得“胜利”的故事,是谁都没有想到的反转。
如果说女佣巴蒂的最终“胜利”是此案震惊全岛的因素之一,另一引起关注的点,则是涉案雇主廖文良的樟宜机场集团总裁身份了。

这一事件中,最值得引起深思的不是剧情的反转,而是:巴蒂为何蒙受四年的不白之冤?与廖文良的身份是否有关?
这一切,难道只是一场“权力的游戏”?
01. 被无限压榨的"巴蒂们"
2006年,新加坡樟宜机场集团主席廖文良招聘了一位住家女佣,也就是这起案件的被告人——来自印尼西亚的女佣巴蒂。
廖家还有另外四名成员,即廖文良妻子Ng Lai Peng,女儿Liew Cheng May,儿子 Karl Liew廖启龙,以及儿媳Heather Lim。

根据庭审记录,2007年,时年33岁的巴蒂来到廖文良家当女佣。像其他女佣一样,她辛苦劳动,只为在新加坡换取生活之需。
她兢兢业业,工作时间从周一到周六,每日早上5点开始工作,直到晚上11点,超负荷的工作,换来的却是极低的薪水。
巴蒂刚开始在廖家工作时,月薪为300新币,每两年续约一次。到了2016年,月薪才勉强涨到了600新币。
而她的雇主,廖文良,在2013年就被新加坡媒体评为“十大打工皇帝”之一,年薪在当时就达到516万新币。
算个最简单的除法:5160000÷12÷600=716.7。也没有很夸张,雇主的月薪不过也就是女佣的区区716倍罢了。
当然,这么算或许有些不公平,毕竟两个人的能力和专业都有差别。但是对普通人来说依然很难想像,照顾富豪雇主之家的女佣,竟拿着如此微薄的薪水。

更让人跌破眼镜的是,廖家对巴蒂的压榨还不止于此。
根据巴蒂在法庭上的陈述,廖家曾多次迫使她到廖启龙(廖文良之子)的住处和公司非法工作。
早在2012年和2013年,巴蒂就被派往廖启龙的办公室打扫。2016年3月,在廖启龙携妻儿在搬到离廖家不远的另一处公寓后,廖家更加频繁地要求巴蒂前往打扫。
在新加坡雇佣女佣,必须注明工作地址。一旦出了这个地址,那就得申请准证。廖家的这种行为,已经触碰了法律。
在新加坡,女佣被雇主压榨的情况并不罕见。巴蒂身后,还有无数被无限压榨的“巴蒂们”。
新加坡客工组织情义之家(HOME)与香港反人口走私组织Liberty Shared合作,于2019年1月15日发布了一份报告,揭露在新加坡的女佣面对三大问题:过度劳动、言语羞辱和薪资纠纷。

根据国际劳工组织定义,若以任何惩罚相威胁,强迫任何人从事违反其意愿的一切劳动或服务且不能随意离职,即是强迫劳动,其中包括限制劳工行动‘克扣工资、恐吓和心理压迫等等。
雇主为女佣申请工作准证,有责任确保女佣遵守准证条例,包括婚姻限制、强制医疗检查并确保女佣不涉及任何非法活动,雇主还得缴交五千元的保证金。
报告指出,正因为这些条例,反而鼓励雇主严厉地监控女佣的生活起居,有者甚至面对暴力、禁食、被辱骂和过度劳动的威胁。

仅2018年一年时间里,HOME就接到900起来自外籍女佣的申诉,其中处理最多的投诉是雇主扣留工资和工时过长。
在本地工作十年的Indah,被雇主克扣超过四万元工资,也不被允许使用手机,几乎七年没和家人联系。
另一女佣Ella每日工作17小时,每月只有一日休假,即使向雇主申诉手痛,仍被迫每日用手清洗雇主一家的衣物,还遭受言语霸凌。
Rosa则每日工作19小时无休,她不满工作环境要求转换,却被雇主威胁甚至禁止他离开家门。Rosa试图爬窗户逃走结果摔断腿。但是住院期间还要上手铐。警员甚至没告知他雇主是否又被调查,还对她企图自杀的行为发出严厉警告。
……
新加坡法律规定,女佣必须住在雇主家里,这也使得女佣的实际工作时间等难以计量,被压榨也就成了常态。
有的女佣,认为自己被当做“现代奴隶”一般对待:
“我们的生活如同现代奴隶,因为我们的法律权益不被认可,待遇差过其他劳工。”
02. 雇主与女佣的爱恨情仇
在新加坡,女佣群体在官方人口数据统计中一般被称为FDW(Foreign domestic worker)。
根据2019年9月新加坡《2019年人口简报》数据,截至2019年6月,新加坡总人口570万,其中168万都是非居民人口,也即外来人口。在这之中,FDW占据新加坡外来人口15%的比例,总数达到25万2000人。
在新加坡,几乎每5户家庭中就有1户雇佣女佣。
Experian发布的数据显示:2018年,女佣的存在为新加坡做出了近9亿美元的经济贡献,约占新加坡全年GDP的2.5%。
不可否认,大多数女佣兢兢业业、任劳任怨地做好自己的本职工作,对新加坡家庭做出了很大的贡献。许多新加坡家庭依赖女佣照顾病患者、年长者、孩童、宠物以及处理繁琐家务等。
这个隐藏在无数个家庭背后的默默无闻的群体,也是新加坡发展的重要力量。

人与人之间的相处是一门高深的学问,雇主与女佣之间的相处也是。
新加坡外来女佣的历史最早可以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这么多年以来,新加坡的雇主和外来女佣之间,上演了许多的“爱恨情仇”。
对很多女佣而言,尽管住在雇主家里,但很少有雇主会把她们当作自己家庭的一员。很多雇主会在家里安装摄像头,监控女佣的一举一动;有些雇主对待女佣非常严厉,说话也很刻薄,还限制女佣的自由,包括没收手机、不让外出等等;更有甚者,甚至虐待女佣……
新加坡《联合早报》向国家法院取得的数据显示,2011年有14起伤害女佣的案件被提控;2012年18起;2013年和2014年各23起;2015年增至26起。
虐佣案件包括蓄意伤害、持武器伤害和严重伤害三类,当中蓄意伤害最为普遍。

雇主与女佣关系紧张的原因,有的是因为雇主不仁,也有的是因为女佣不义。
一名30岁印度尼西亚女佣,自2017年就在受害雇主家工作,照料雇主一家六口的日常起居和饮食。2018年8月,她不知从哪里听来的偏方,相信只要雇主吃下掺入自己经血、口水、尿液的食物和水,雇主就不会因为她工作做不好而责骂她。
于是,雇主一家就浑然不知地多次食用这些加了“料”的食物...... 不仅如此,这名女佣还利用雇主对自己的信任,多次偷窃雇主的钱财,总数1万7千多新币。

很多新加坡雇主都会感叹:在新加坡想找一个女佣很简单,想找一个“好”女佣却是难上加难。
与此同时,相信很多女佣也会感叹:在新加坡想找一个雇主已经够难的了,想找一个好雇主却更难。
双方都难,抱怨连连之下,雇主和女佣之间的各种纠纷,在新加坡的媒体报道中就屡见不鲜,新加坡民众对此也就见怪不怪了。
03. "权力的游戏"
将视线转回巴蒂的案件上,巴蒂曾在廖家服务九年。九年的朝夕相处,摩擦在所难免,难道两方的纠葛也是来源于此?
这就是这起案件的特别之处,巴蒂的事件,不是简单的雇主和女佣之间的矛盾可以概括的。
这其中,或许还涉及到“权力的游戏”。
我们再来从头梳理一下整个案件。先从双方的身份说起:
雇主廖文良自2009年起担任樟宜机场集团主席,也是盛裕集团(Surbana Jurong)主席、新加坡交易所董事、华社自助理事会理事及亚洲房地产巨头凯德集团(Capitaland)的创始总裁,兼任多职,位高权重。
商场叱咤风云,廖文良在学术上也是盛名满载。
他身兼新加坡国立大学商学院、工程学院、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教务长讲席教授。显赫的地位和功勋,曾让他荣获了新加坡总统颁发功绩奖章。
而女佣巴蒂,印度尼西亚籍,无钱无势,背井离乡来到新加坡打工只为赚取微薄薪水贴补家用。

论社会地位,一个是新加坡响当当的商业巨擘,一个是藉藉无名的印尼女佣,任谁看来都是云泥之别。
再来梳理一下时间线:
2007年3月至2016年10月,巴蒂在廖家工作九年;在2012和2013年,巴蒂曾被廖家派到廖文龙的办公室非法劳动;
2016年3月,廖文龙搬到新家,巴蒂再被多次派到廖文龙新住处和办公室非法劳动;在此之后,巴蒂曾多次表达对此的不满;
2016年10月,廖文良发现一个充电宝不见了。价格虽不高昂,但他格外珍视。多次怀疑巴蒂手脚不干净的他决定开除巴蒂;
2016年10月28日,廖文良不在新加坡,示意儿子廖启龙代为开除巴蒂。当天早上,廖启龙安排雇佣代理公司代表到场,告知巴蒂她被开除了。事情突发不说,还只给了巴蒂两三个小时的时间收拾行李。在把自己三大箱的行李嘱咐给廖启龙,让他帮忙运回印尼后,意难平的巴蒂威胁到她会向人力部举报廖家迫使她到廖启龙的住处和公司非法工作的事。
当时的巴蒂没有想到,或许正是这份威胁,让廖家动了“先发制人”的心,狠狠地告了她一状。
2016年10月29日,廖文良和家人花了两个小时检查两个箱子,发现许多属于他们的物品,并拍摄约21秒视频。
随后,廖家以怀疑巴蒂偷其家中贵重物品将其告上法庭,称巴蒂偷走了他们家价值3.4万新币(约17万人民币)的物品,包括115件衣服、多个奢侈手袋、一部DVD播放机和一块尊达手表;而警方的取证工作是在2018年4月18日才完成的,在此之前,那些所谓的“赃物”还可以被廖家人自由使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