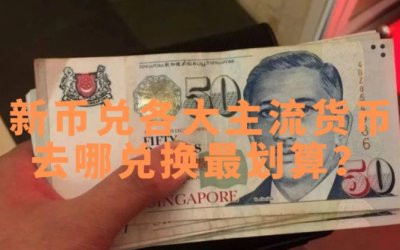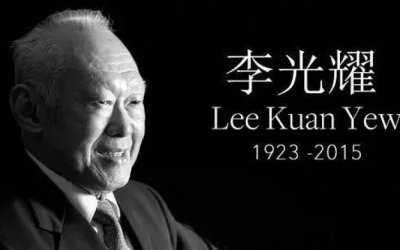人为糅在一起
“限制居住比例将防止种族‘重组’。”

新加坡牛车水地区一直是新加坡华人聚居区,如今成为了特色景点和购物中心,吸引了各国游客。图/毛淑杰
新加坡是一个移民国家。华人占比约七成,马来人、印度人次之。
据新加坡国家博物馆资料,英属殖民地时期的新加坡,政府采取“分而治之”的政策,不同族群集中在不同地区。比如市中心为华人区,甘榜格南和芽笼士乃为马来人区,实龙岗和三巴旺为印度人区等。
这样种族隔离政策,固然方便了殖民者的管理,却埋下了种族隔阂的隐患。
1964年7月-9月,新加坡连续发生了两起大规模种族骚乱。其中,发生在1964年7月21日的宗教游行冲突事件,马来人和华人群体在全岛范围内发生械斗,造成23人死亡,454人受伤。
上世纪90年代,新加坡建屋局推出种族融合政策(Ethnic Integration Policy ),规定不同种族群体在组屋中的占比,比如同一社区中,马来人约两成、华人约七成、印度人和其他少数民族约一成。后来,这个比例也随着社会人口结构改变而做出响应调整。
“从长远来看,限制居住地的种族比例将防止种族‘重组’。”时任新加坡国家发展部部长S.丹那巴南在介绍这一政策时警告称,无法想象新加坡退回到独立前那个时代。
新加坡组屋大都设置了公共空间,比如咖啡店、健身角和社区中心。在这里,常见到不同种族居民交流、玩耍。
赵秀玲观察,大部分新加坡组屋的一层都是架空的,这会带来诸多便利。一个是避免带来空间分割,方便人员便捷穿行,减少城市拥挤。另一方面,这也创造了社区的公共空间。“我们常常在组屋中看到,马来人会在架空层申请办婚礼,而华人会在这里办葬礼等。这是带有新加坡特色的空间利用方式。”她说。
新加坡南洋学会会长许振义是新加坡第三代华人移民。他的祖父最早从中国福建来到新加坡,随后开枝散叶。
“对我来说,组屋已经贯穿了我们家族至少三代人的记忆,是一段很有公共性的家族体验。”许振义的父母经历过新加坡独立之初的艰难时刻,是早期新加坡组屋的见证者。而他本人也在组屋出生,并在其中生活了三十余年。
在许振义看来,组屋在多个方面促进了新加坡社会的融合。
英国殖民统治时期,不仅华人、印度人、马来人等族群聚居区明确区分,甚至在华人聚居区内部也有细致划分,比如海南村、潮州村、南安村、晋江村等。人们主要在本身社群内生活、娱乐、工作,包括婚娶。而入住组屋后,相当于把不同族群“人为地揉在一起”,强行打破了原有的聚居区,促进了不同族群的融合。
随着时代发展,组屋建设从市中心扩展到了郊区。许振义观察发现,新加坡政府重视不同类型组屋的布局和搭配,比如在新区组屋建设中保留小户型,在老市区拆掉旧屋、增加大户型等,从而符合不断变化的住房需求。
组屋虽定位是公共房屋,但其地段并不偏僻,周边也常常出现私人洋房、别墅、公寓等。再加上,新加坡市政建设是去中心化的,组屋周边也有较为完善的商业、学校、医院等配套设施,利于居民生活。
“新加坡组屋和其他建筑是融在一起的,一方面很少有专门的富人区或者贫民区,另一方面也没有明显的老城区和新城区。新与旧、贫与富都是融合在一起的。可以说,组屋某种程度上促进了种族、阶层、贫富的融合。”许振义说。
“新加坡规划之父”刘太格曾担任新加坡建屋发展局局长、市区重建局局长。他重视整体规划,希望每个区域都能发挥综合性效能。
他在多个场合说过,“西餐式”规划提倡功能分区,一堆马铃薯、一堆菜,一堆肉。而“我的做法是炒饭,马铃薯、菜和肉都切小,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饭”。这样的融合式规划理念在组屋中也有体现。
2018年9月4日,新加坡时任国家发展部长黄循财在建屋发展局高峰论坛上表示,新加坡人在组屋附近的小贩中心吃饭,购物中心购物,孩子们一起玩耍和成长,由此培养了一种社区感和归属感。
“组屋生活是新加坡民族认同和生活方式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他说。
组屋制度运转六十余年
“关键在于政策设计的严密性和灵活性。”
除中国外,新加坡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以华人为主体的国家。建国之初,新加坡政府倡导“东西结合”,既要学习西方先进技术与文化,也要保持东方传统文化的精华。
1985年,新加坡中学推行的道德教育课中,也包括忠勇、孝友等中国传统儒家思想。李光耀本人也在公开场合倡导儒家理念,比如强调“家庭是社会的基本结构”“孝道不被重视,生存体系会变得薄弱,文明的生活方式也会变得粗野”。
组屋制度施行之初,新加坡政府要求组屋申请以家庭为单位,未婚男女青年不能购买住房。而且,已婚子女如果与父母、祖父母住在一起的,成为多代同堂的家庭,或在邻近地段购买住房,他们的申请有优先选择权,房价也给予折扣。
76岁的李祖民经历过那个年代。1971年,23岁的李祖民大学毕业。身边不少同学为了能尽快拥有房屋,情侣们争相提前登记结婚。
彼时组屋定价较低,李祖民申请到的第一套组屋约100平方米,全款大约4万元新币。李祖民说,当时大学毕业的年轻人,只要毕业后能找到工作,几乎都能买得起组屋,“普通的组屋一间大约几千块新币”。
在新加坡建屋局官网,可以查阅到组屋购买者的详细条件,除了国籍外,还包括年龄、家庭状况、收入上限、既有房产等。时过境迁,组屋制度也随之改变。
如今,新加坡组屋价格也随着地产热潮攀升,在二手组屋市场上,多次出现百万新币的“天价”组屋。而借助建屋局于2024年推出了新政策,单身公民也可以享受公共住房福利,“家庭”不再是必选项。
许麟济认为,新加坡组屋制度能够顺利运转六十余年,其关键就在于政策设计的严密性和灵活性。
首先,公共住房政策最初是为了解决中低收入家庭的住房问题,因此设有严格的收入限制。早期规定,只有家庭月收入不超过2000新币的居民才有资格购买政府组屋,超过这一标准一般能够自行解决住房需求。随着新加坡经济发展和工资水平的提高,目前申请组屋的家庭月收入上限已提高至约1万新币。
此外,新加坡还规定,每个公民一生中最多只能购买两套新的组屋。且一个人不能同时拥有两套组屋。此外,如果申请人已经拥有私人住宅,则不允许购买政府组屋等。
“通过这些限制措施,新加坡政府能够有效管理公共住房资源,确保组屋能够真正服务于有需要的家庭,避免资源被不必要占用。”许麟济说。
十多年后,新一代的新加坡人已有了更好的住房选择。
如今,李祖民已从组屋中搬出多年,而他的孩子一代属于中高收入阶层,并不符合组屋申请标准,转而选择生活在安保性更好的私营住宅、别墅等。
据新加坡统计局2024年7月数据,2023年新加坡77%的常住人口居住在建屋发展局 (HDB) 下属的公共住房中。相较于十年前的82%,这一比例在不断下降。
(李祖民为化名)
南方周末记者 毛淑杰
责编 姚忆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