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60多歲的長者拖著腳走進醫療社工林雅彥的辦公室,身上穿著單薄的半透明白色上衣、粗製的卡其色百慕達短褲,神色有點不自在。新加坡中央醫院無菌空調下的舒適氛圍並不是這位失業的長者所習慣的環境。他並不是自己預約來找社工的,而是醫生指示他到這裡來求助;原因是他患上了慢性疾病,卻不肯接受檢測。「我沒錢做檢查。」他用福建話說出了非常直白真實的理由。那是1993年4月,才剛從初級學院畢業沒幾個月的林雅彥詳細詢問了他的狀況,馬上就得出一個結論:這位年長者符合條件,可在政府推出的一項新措施下申請全額資助。她告訴眼前這位長者,放心去接受檢查吧。
可是他依然焦慮,問道:「所以我得要出多少錢?」
林雅彥說:「一分錢也不必出。不用擔心,政府會幫助你的。這是新政策,會幫助負擔不起的人支付醫療護理費用。」
「真是?這是真的嗎?政府哪有那麼好?」
林雅彥回想起來,對方的反應是「鬆了一口氣,卻又不敢相信」。她直率地說:「好到令人難以置信吧。對許多病人來說,一般總是認為一有什麼新政策出台,那八成是政府又往人民身上摳錢來了。」可是事實是,如今就是有了這麼一個「保健基金」(MediFund),為那些在政府提供的種種現有津貼後仍然付不起醫藥費的貧困人士,鋪設了一張全新的安全網。這是一項劃時代的新政策。
在這之前,醫院只能依賴非常有限的基金來源,以抵消貧困病患負擔不起的醫療費用,而醫療社工總是得四處奔走,向私人基金會募款。整個程序冗長緩慢,也不見得有收穫。打個比方說,如果病患需要接受核磁共振成像掃描,等到籌款有著落,卻早已延誤了診斷,也錯失了治療的黃金期。「而且,那個年代還沒有電郵。」林雅彥補充道。「貧困病人需要拖上好長一段時間才等得到回覆說能否繼續接受治療。整個程序非常繁瑣拖沓,重點是,基金非常有限。」
保健基金,終止了這些機制化的「乞討」方式。最大關鍵在於,設立保健基金,意味著新加坡的醫療體系不會再有人因為經濟問題而得不到應有的治療與護理。「這不只是願景,不只是溫情。這是個道德行為。」林雅彥如此總結。「而這一切,得感激吳作棟。」
1993年4月,馬林百列集選區補選結束四個月後,保健基金正式成立。這項新計劃連同「教育儲蓄」(Edusave)基金,在吳作棟一心想要建立的更寬容、更溫和的新社會裡,是他最早也最直觀的兩大倡議。這樣的一個新加坡,會對處境較不幸的國民幫扶更多,讓這些弱勢群體不至於掉隊。他後來稱之為「溫情的唯才是用制度」,雖然這個時髦的詞彙是在好多年後才出現。其實最先讓他得到啟發進而反向思考的,是早在他還未成為總理之前聽過美國前總統甘迺迪說過的 一句名言:「潮漲眾船高」。這句話與中文成語「水漲船高」不謀而合,意指強勁增長的經濟讓所有人受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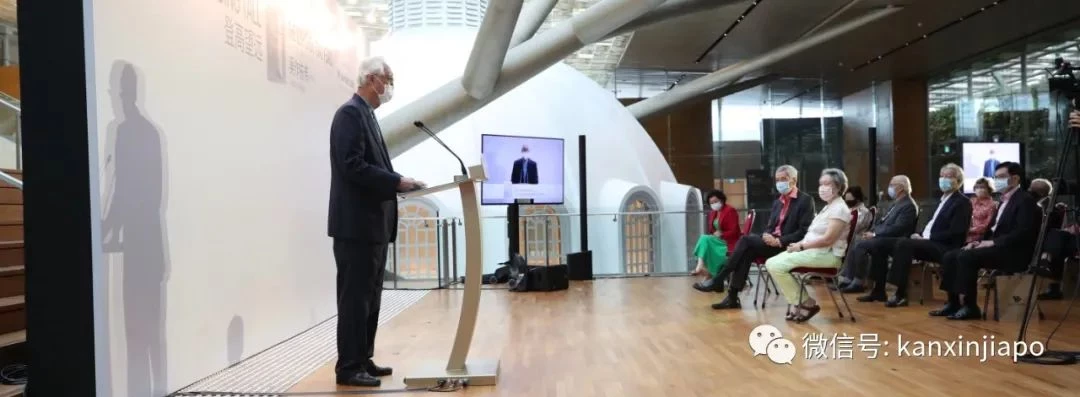
吳作棟並不認同這個說法。他說:「我很早以前就意識到漲潮時不一定每一艘船都會隨潮而升。我在巴西班讓長大,以前就見過小船一隻只地系在樁柱上,避免它們隨浪漂走。這些主要是舢板和小舟。船主會確保纜繩夠長,潮漲時海水才不會漫進小舟舢板或將之完全淹沒。偶爾我也會見到一兩隻舢板半淹在海里。所以參照這個比喻,小舟能否隨潮而升,就得取決於繫著樁柱的纜繩有多長。這個樁柱就是國家。纜繩是你的家人,是你所處的經濟環境。纜繩太短的話,潮漲得再高也沒法把小舟推高,反而還會把它捲入海中。你得給我一條長點兒的繩子。可是長繩怎麼來?我們就把重點放在這裡 —— 怎麼確保在潮漲時能給人民長點兒的繩子。」他把這番解說稱作自己的「小哲理」。
要給人民拋出長繩,他必須有資金來源。吳作棟並不想動用儲備金,也無意創建一個福利國家。但他決意不像李光耀政府這般極盡節儉。「我接任總理後,如果一味只懂得積累儲備金而不分享國家財富,肯定會讓政府在政治上遭到抨擊。」他說道。「記得劉程強在1991年全國大選是怎麼嘲諷嗎 ——『政府有錢人民無!』」劉程強是在野陣營工人黨所派出的候選人,1991年大選時用潮州話將這句口號發揮得淋漓盡致,在東北區後港力挫行動黨原任議員陳原生,爆冷勝出。
吳作棟決定改變李光耀長久以來在每屆政府任期結束時將所有財政盈餘撥入國家儲備的做法。他撥出部分常年財政預算,成立了兩項獨立的捐贈基金,分別是保健基金和教育儲蓄基金。吳作棟說,這個改變並未在內閣引起任何反彈,連李光耀也未提出反對。他說明: 「捐贈基金的性質就同國家儲備金類似,本金是不能動用的,可動用的只有盈收。這麼一來,也就不違背不動用儲備金的原則。」
前公務員首長林祥源說,當時正是探討這個問題的絕佳時機: 「總會來到一個階段,你會這麼問:積累了如此豐厚的儲備金意義何 在?這是因為到頭來,這筆儲備金是當今的這一代人協助積累下來的。就新加坡的情況來說,我們沒有黃金白銀或者其他天然資源,我 們擁有的就只有儲備金。儲備金對於新加坡來說,就好像是其他國家 的油田和礦產一樣。但是,有了儲備金,你是不是該把它用在辛辛苦苦積攢儲備金的這一代人身上?這是個再自然不過的問題,卻也同時 是個看似毫無關聯的問題,除非你覺得國家已經存夠了尚未有指定用 途的儲備金。我認為吳作棟先生能看到這一點是好的,他說該去想想這個問題。」
吳作棟運用財政盈餘的手法充分反映了他的品質:謹慎、投入、溫情。保健基金和教育儲蓄基金都屬於捐贈基金,政府最初分別投入2億 新 元 和 1 0 億 新 元 ,在 國 家 財 政 有 盈 余 時 適 當 撥 款 給 這 兩 項 基 金 。到了2020年3月31日,在兩項基金成立逾四分之一世紀之後,保健基金已有46億新元,教育儲蓄基金則達到67億新元。再以本金總額進行投資以賺取收入利息,而每年的津貼撥款就是來自於這些投資所得和利息。
「本金總額全放入一個玻璃容器里,閥門牢牢鎖上。」吳作棟如 此形容。「只有負責看管的人握有鑰匙。所以每一年,你會打開水龍 頭,流出一些股息。而我可以告訴人們不必再為醫療費用而操心,因為在衛生部的預算之外,我還有這筆經常性收入可以注入,幫助那些 實在負擔不起的人支付住院費和門診護理費用。要是我把所有的錢都鎖在儲備金里,一旦有需要幫助這些人,我就還得再提高衛生部預 算,甚至調高稅率。」保健基金與教育儲蓄基金就好比國家開設的定期存款戶頭,可利用本金投資所得收入來扶持那些需要幫助的人。只要新加坡的經濟持續增長,吳作棟的計劃就能確保長繩一直都在,幫助小舟在潮漲時也隨之升高。
而醫療與教育,是他心目中的兩大最佳平衡槓桿:這兩方面最 需要長長的纜繩。保健基金的扶助對象是最貧困的一群人,而教育儲蓄基金的宗旨就更為宏大了,要激勵學生,幫助弱勢家庭子女迎頭趕上。基金初期只是純粹為學校里開辦的各種增益課程如舞蹈課、體操課、美術課等提供資助,家長也可動用教育儲蓄基金支付學校雜費或增益課程學費。漸漸地,教育儲蓄基金的用途從原來設立的獎助學金,擴展到領導能力與品德模範等各類獎項。在今天,每年通過保健 基金和教育儲蓄髮放的金額分別達1.5億新元和 2 億新元。吳作棟說 明:「你永遠也不可能消除有錢人所能享有的優勢。但你可以確保那些處在最底層的人,不會只因為缺乏資源而被剝奪機會。我們的說法是,讓人人都能在人生的馬拉松長跑中站上同一條起跑線。」
就保健基金而言,他在設計這項計劃時已經把執行時的靈活性納入制度中。他很清楚經濟援助很少是直截了當,單憑收入水平就能決定的。所以,與其讓一群照章行事的公務員來決定誰才符合條件申請保健基金,他把這個決定權交託給醫療社工,由社工評估個案來酌情處理。吳作棟相信醫療社工的關注點不會只限於收入水平,而是更願意考量其他因素。關鍵在於,他明確指示保健基金應當以更寬鬆的方式來管理。換句話說,只要申請者能顯示自己確實無法負擔住院費,就可獲得批准。他說:「醫院應該把重點放在治療,而不是還得為壞帳操心。」林雅彥說,這個做法其實也讓醫療社工這一行獲得了必要的授權和認可。「保健基金的評估標準其實兼顧了感知度與敏感性,深化了這項計劃的價值。」她進而補充說:「他是我們這一行的『意外守護者』。」

無論是保健基金或是教育儲蓄基金,都折射出吳作棟早年的生活經歷在他身上留下的深刻印記,特別是年幼喪父之痛。他憶述:「如果當時的社會也有這麼一重安全網,父親可能就不會死於肺癆病。我從來沒問過家中長輩為什麼父親當年沒去看醫生接受治療。可能發現得太晚,也可能就是因為沒錢。保健基金對他來說就會很重要了。那個時候只要撥給他幾百塊錢,他也許就得救了。」正如林雅彥口中所說的,吳作棟「是一個生活經歷過磨難的人,一個曾經失去至親的人。」
父親臨終前留下了遺言要他努力讀書,他從此恪守一生。當他考取了優異成績,家裡卻經濟拮据,政府頒給了他助學金,扶持他從中學一路到考取大學學位。1990年12月,在出任總理後不過數周的一場演說中,他說:「我對國家心存感恩。國家給了我機會,可以跟其他富家子弟競爭。我投入了競爭。我成功了。」
問:有些人說政府在分享財富方面做得不夠 —— 窮人還是很窮。不過卻也有另一些人擔心政府做得太過,會傾向福利國家制度。像這樣的關注點,當年在您制定這些措施時是不是也曾提出來討論?
答:那個年代我們還不談論「收入不均」這個詞。我們的想法 是,應該怎麼為國家創造財富,把財富適度地再分配給較貧困國人。首先,切勿向富人徵稅過重,免得反倒遏阻他們去辛勤工作,轉而想方設法通過成立信託甚至移民他處來避 稅。稅率應該維持在一個人人都「樂得」繳稅的水平。而我 說的不只是公民而已。我們需要吸引跨國企業到新加坡投資。如果企業稅率過高,他們就不會來了。你得與其他地方競爭,比如香港。所以,這是第一項原則:使稅率維持在國人都樂得繳稅的水平,外國人也會因為稅率較低而到我們這 里來設廠經商。
問:我還是第一次聽到這樣的說法:樂得繳稅。如今個人所得稅 率已經下調到20%上下?
答:我們的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一度降到20%。
問:降至20,大家會很樂意嗎?
答:你用了「很」,我可沒有。(大笑)我們真正考慮的是最高邊際個人所得稅率和公司或信託稅率這兩者之間的差距。
問:目前的個人所得稅率最高可達22?
答:22%是超過32萬元以上收入的稅率。我認為這是合理的。32萬元以上的收入,你每賺一元,付稅22分給政府,這是可以接受的。有些國家的稅率還要高得多,就反而會遏阻勞作。所以許多高收入人士都會選擇在其他國家註冊為稅務居民,例如巴哈馬、百慕達、英屬維京群島、摩納哥等等。我們富有的生意人、企業家理應推動經濟發展,也為財富再分配作出貢獻。
問:那要如何落實財富再分配?
答:我們會儘可能把財富再分配與勞動力掛鉤。確保人們得有付出才能享受福利,例如教育儲蓄獎學金、優異助學金、學業進步獎等等。其次,得有針對性,就如保健基金。放到今天的情境來說,這些惠民措施計劃就好比水電費回扣、消費稅補助券、就業補助計劃、社保援助計劃、樂齡補貼計劃等等。
問:如果您今天還主政,您會不會推出「建國一代」配套和「立 國一代」配套?2
答:建國一代,會的。至於立國一代嘛,我很可能需要三思。
問:為什麼?您不認為立國一代也值得享有這些福利嗎?
答:這當然是他們應得的。當今的年長者賺的是舊時代的薪資, 卻得活在這個時代的環境中,負擔這個時代的生活費——舊工資,新生活成本。我們的國家儲備都是建國一代和立國一代這些前輩們辛勤耕耘所換來的。在能力許可時與這些年長一代人分享儲備結出的果實,絕對是應當的。
問:但那是否意味著政府就得持續這麼做?
答:這也就是為什麼我會說,對於推出立國一代配套,我會三思而後行。如果你覺得這是你必須做的,那你就得確保自己有 能力創造更多財政盈餘來支撐。財政盈餘多半仰仗於儲備金 投資所得的回報。如果你有能力持續創造豐厚的財政盈餘, 那就太好了。但這是否為恆久之策?這是關鍵所在。如果能 做到,那就沒問題,你就能夠每隔十年左右,為後續的每一 代人推出一個特別配套。
問:您好像對這種預想不太有信心?
答:綜上所述,有了建國一代配套,又有了立國一代配套,人民就會期望再有個「Majulah Generation(興國一代)」配套。行! 如果經濟持續增長,財政有盈餘可以分享,沒問題。要不然, 興國一代之後,就是「Mati-lah Generation(亡國一代)」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