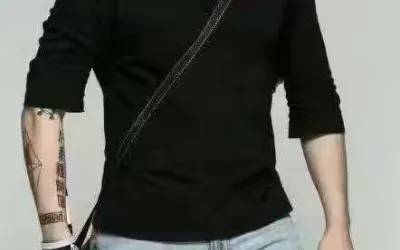繼紅螞蟻在1月20日完成了《「孤獨死」每天都在新加坡上演,見報的只是冰山一角》一文後,陸續又出現了更多關於獨居老人死於家中、屍體腐爛後才被發現的新聞。
1月26日:74歲獨居德士司機被發現倒臥在勿洛北4道第102座組屋9樓的家中。
1月31日,大年初三:西海岸通道一名女鄰居聞到刺鼻的異味報警,53歲男子被發現死於家中。
2月1日:71歲男子被發現暴斃在惹蘭紅山第141座組屋的單位內。樓上鄰居聞到異味後整夜未能安眠,第二天一早去敲門才發現屋內有腐屍。
2月2日:71歲男子被發現暴斃在勿洛南2道第12座組屋二樓的家中。
2月10日:57歲獨居男子在兀里連路第208A座組屋的家中去世,屍體發臭引起鄰居關注報警。
3月2日:朋友連續五天未能聯繫上82歲的獨居老婦,最終在武吉巴督西8道第171座組屋22樓的家中發現她已倒斃。
對於獨居老人來說,如果行動不便且沒有家人可依靠,想要有尊嚴地度過晚年,療養院或許不是一個糟糕的選擇。
個案一:和親人疏離了
83歲的李阿明(音譯)因行動不便且沒家人可依靠而住進療養院。
他年輕時經歷了離婚以及和兄弟姐妹失聯後,就和朋友一起住進芽籠峇魯的一房式租賃組屋。
2022年,李阿明的健康惡化而入院,出院後他被轉介入住瑞那拉耶拿教會(Sree Narayana Mission)屬下位於義順的療養院。
已有超過30年沒和兄弟姐妹聯繫的他告訴《亞洲新聞台》:
「我現在已經超過80歲了,已經好多年沒有人來看我了。我的家人沒有人來看我,他們不知道我住進了療養院,而我也不知道我兄弟姐妹的住家地址。」
新加坡有一群像李阿明一樣的老年人,他們入住療養院或福利院並非出於選擇,而是迫不得已。
他們大多數因為無法自理,且與家人和朋友疏遠多年。還有一些人沒有子女,或者家人已經先離開了這個世界。
李阿明說:
「但是我來到了療養院後,感覺很好,有人照顧我,還結交了朋友,又可以打麻將,出去玩。」

樂齡SG計劃由國家領導讓年長者的住家更親樂齡、打造更安全且容易通行的社區,以及建造更多融合住房、護理和社區服務的輔助生活設施,只在協助年長者原地養老,實現健康、充實和有尊嚴的晚年生活。(聯合早報)
個案二:膝下無子女,親人都比自己「早走」
83歲的陳秀玲(音譯)膝下無子女,而丈夫已經先一步離開了這個世界。丈夫過世後,她幾十年來頭一次感到寂寞。
那時,她每天到日間護理中心報到打發時間,工作人員注意到她變得越來越健忘,並且得依賴他人的照料。日間護理中心擔心她回家後的安全和健康狀況,將她轉介至療養院接受全日制照料。
2024年,陳秀玲住進了瑞那拉耶拿教會的療養院。她受訪時坦言,從未想過自己有一天會住進這樣的地方。
陳秀玲女士在療養院的個案經理兼社工瑪麗(Mary Joseph Lourdes)說,像陳女士這樣的長者,剛開始往往很難適應療養院的生活。
「多數人一開始都會處於『拒絕相信』的狀態,總想著『為什麼我會住進療養院呢?』」
這種情況在沒直系親屬的長者身上,尤為明顯。因為他們當中許多人早已習慣了獨居,直到年老和疾病的到來,才迫使他們尋求他人的幫助。
個案三:露宿者
70歲的Zack(假名)因多次吸毒和盜竊罪而坐牢,出獄後他不想給家人帶來負擔,選擇當露宿者。
這些年來,他與親人失去聯繫,並依靠有限的積蓄維持生活,直到2020年入住衛理福利服務基督之光衛理關懷院。
Zack說:
「以前每一餐都得四處翻找食物,在這裡,他們給我準備好了食物和必需品。」
也曾是露宿者的Ah Tan(77歲)住在基督之光衛理關懷院已經17年了,和他同住的兄弟過世後,他便在小印度的竹腳一帶露宿街頭。
雙腿截肢的Ah Tan哽咽地說:
「我的兄弟姐妹和母親都走了,只剩下我一個人。」
基督之光衛理關懷是新加坡11個福利院中的其中一家,這些福利院由社會服務機構運營,專門為貧困人士提供照護。
衛理福利服務表示,這些長者住進福利院的常見原因:財務困難、長期監禁或住進心理衛生學院入院治療精神健康問題,這些因素最終導致他們失去住所。
他們在福利院接受直接的輔導並參加社交活動,以應對自己「複雜的心理情感挑戰」。
衛理福利服務指出,這群人很少在公眾場合露面,可能很多新加坡人都不知道他們的存在,或者對他們有誤解。
目前,在新加坡的貧困人士法令下,貧困人士若沒有能力照顧自己並缺乏家庭支持,可入住福利院。當局會進行社會調查,確保個人符合該法令的貧困者定義,即沒有明顯的生計來源或住所、沒有心智能力。
由於這些標準,這些福利院中的許多長者居民都是沒有照顧者或近親支持的人,因此長期住宿護理是他們最好或唯一的選擇。
養老院是孤獨老人的避風港

養老院的院友參加活動。(聯合早報)
據新加坡社會及家庭發展部的數據,截至今年2月,大約有1500人住在療養院、福利院、安老院、養老院等,其中60%的年齡在60歲及以上。
2023年,衛生部指出,2030年,每四名公民中就有一人年滿65歲或以上,當中有大約8萬3000人是獨居老人,這一數字可能還會繼續增長。
聖約翰養老院執行長Richard Quah表示,約有8%至10%的居民與家人沒有任何聯繫。
「可能源於各種原因,包括家庭爭執、溝通中斷、生活轉變或出現了照顧責任相關的分歧。」
療養院和福利院也表示,許多缺乏家庭支持的老年人也來自低收入家庭,他們以前住在一房或兩房的租賃組屋,並且有較嚴重的健康問題。
職總保健合作社高級醫療社工Tho Pei Leng透露,其中一些人過去曾經歷過家庭衝突,包括被虐待、父母缺席或與賭博和借貸有關的問題。
養老院的一天生活
在基督之光衛理關懷院,居民們的一天從早上6點開始,首先是洗澡和吃早餐,隨後他們接受醫療治療並參加晨間運動。
其他活動包括各種旨在維持居民整體健康的項目,例如:適應性鍛鍊、認知遊戲、娛樂遊戲以及物理或職業治療課程。
關懷院也為所有居民提供三頓正餐和兩次茶點,還舉辦娛樂活動,如每月一次的電影之夜。
除了照顧居民的基本生活,養老院也必須顧慮他們的心理感受,特別是孤獨感。
社工瑪麗表示,許多沒有親人的居民最常談論的就是失去親人的悲傷。在他們進入養老院之前,或許和親人還有些聯繫,但如今再也沒有人來看望他們,這種落差對他們來說是巨大的。
尤其在同一個養老院內,有些居民仍有家人來看望,節日期間也能回家與家人團聚。這種強烈對比就會讓那些沒有親人的居民孤獨感愈發加劇。
為了減輕孤獨感,養老院一般會定期安排義工探訪這些居民,並在節日期間組織各類活動,讓他們參與其中,儘量讓他們不感到被遺棄。
基督之光衛理關懷院也有讓居民使用他們的技能創前程培訓補助,參與園藝課程。
住在養老院似乎會讓人與社會產生隔離感,但養老院和福利院都強調,他們提供豐富的活動讓居民參與,並努力幫助居民重新連接過去的日常生活、人際關係以及曾經的社區。
回教傳教協會療養院也會帶院友去附近的食閣和超市外出活動。
德教萬緣福利院指他們也曾嘗試帶院友回到他們登記得住址所在的鄰里,作為例行的外出活動之一,希望他們能夠碰到一些舊鄰居或朋友。
回教傳教協會療養院院長兼護理主任Abdul Hadi Kamarolzama說:
「說到底,我們每個人都渴望與家人更親近。衰老的過程本來就充滿孤獨,這也是為什麼在我們的療養院,我們希望創造一個溫暖的環境,讓居民感到受歡迎,把我們當成他們的家人。」
在條件允許的情況下,以及院友的意願下,這些養老院會盡力幫助他們與失去聯繫的家人重新建立聯繫,或至少在他們臨終前安排一次見面。
如果成功取得聯繫,養老院會邀請直系親屬參加院內的家庭聯誼活動,如帶居民回訪他們曾經一起生活的地方進行懷舊之旅。此外,義工和工作人員還會協助居民打扮,並與家人一起拍攝家庭合照等。
療養院曾經被貼上「被遺棄」 「老人等死的地方」 等負面標籤,但回教傳教協會療養院表示,越來越多人開始認識到,入住療養院並非因為家人「不想要他們」,而是因為他們可以在一個有專業培訓人員提供更高標準護理的環境中得到照顧。
「療養院只是換了一個屋頂,但他們的生活依然繼續,友誼和家庭的感覺依舊存在。」

聖安德烈活躍樂齡護理中心(勿洛北)為年長者提供護理服務,也準備多項康樂活動讓他們參與,包括卡拉OK、保健運動、打桌球、手工、縫紉等。(聯合早報)
在沒有近親的情況下,療養院也需要處理院友的後事,但尊重和滿足他們的意願可能面臨一定的挑戰。
仁慈醫院社會心理服務主任碧奇(Bridget Monica Das)說:
「有時,由於心智能力下降,院友在入院時已經無法表達自己的意願,所以我們必須代表他們做出決定。」
南洋理工大學心理學和醫學教授Andy Ho指出,目前公眾對於孤獨死的看法以及我們與生俱來的觀念,都普遍認為這是一個可怕的現象。
「它確實可能是可怕的事情,但人們也可以選擇並享受這種自主權。即使我沒有很多家庭成員,也不意味著我沒有強大的支持系統。」
這就是為什麼,作為老年護理核心支柱的養老院,致力於為老年人提供一個有尊嚴的「家外之家」,而不僅僅只是提供足夠的床位。
關鍵在於,即使院友沒有任何親友,他們在這些場所內所建立的聯繫,至少能夠彌補這一空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