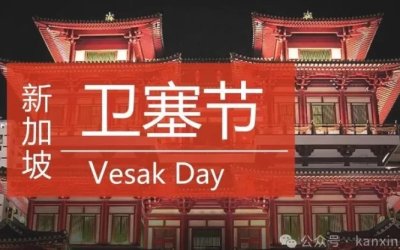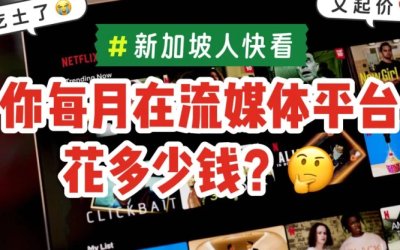步入後疫情時代,儘管病例數近日有增加的跡象,人們卻早已把冠病拋諸腦後。
不少僱主在疫後都採取折中方案、要求員工一周內有幾天回到辦公室、另外幾天居家辦公,但也有一些允許員工遠程上班,不必回公司。
這無形中造就了一個問題——辦公室里的桌椅,誰在使用?
澳大利亞辦公器材供應商XY Sensor發表的最新報告揭露:
多達36%的辦公室小隔間(cubicles)和辦公桌已經很久沒被使用,供過於求。
該報告調查了美國、英國、香港、新加坡等九個城市共2萬4855個獨立工作場所,整理出上述結果。
報告還發現,那些沒有在「積灰塵」的辦公桌中,29%每天被使用的時間不到三小時,另外14%則有五小時或更長的時間沒被使用。
辦公室整體使用率只達到疫前水平的約50%。
美國房地產服務公司世邦魏理仕(CBRE)的另一組數據也反映相同趨勢:
受訪的10個大機構中,有九個都反饋說辦公室利用率較低。
辦公樓空空如也帶來諸多挑戰

新加坡辦公樓。(海峽時報)
辦公桌長時間空置,意味著辦公空間沒被充分利用。
CBRE的同一份報告透露,過半受訪企業預計,他們下來三年會縮小商業資產足跡(footprints)。
其實早在疫情暴發前,不少企業已為辦公空間另作安排,比如向其他公司出租多餘空間,共享工作空間的概念也在那個時期廣受歡迎。
即便如此,全球辦公樓市場前景仍相當不明朗,可能引發更嚴重的問題。
《南華早報》在一篇專題報道中說,像辦公樓這類主要資產市場一旦崩潰,就會跟房屋市場一樣預示著銀行業危機,有可能進一步打擊投資者的信心,加劇全球經濟低迷的境況。
投資者之所以會投資商業資產,尤其是辦公樓,主要是為了賺取比銀行利息更高的利潤。
但如今投資者在需求和租金下滑的雙重衝擊下,還必須面對利率上升的不利因素。
辦公樓擺空城所帶來的挑戰,在一些西方經濟體中尤為嚴重。
世邦魏理仕指出,在美國舊金山,科技公司大規模裁員,加上當地經濟衰退,造成這些企業的公司空置率在上一季創下31.6%的新高。舊金山疫前的辦公室空置率只有大約4%,現在卻有三分之一的辦公桌沒人使用。
也有數據顯示,紐約辦公室的空置率,今年預計會達到22.7%的新高。
另一邊廂,一些英國大企業則果斷選擇縮小辦公空間的規模。

滙豐銀行位於倫敦的總部大廈有45層樓高,一度有8000名員工在樓內工作。(路透社)
滙豐銀行(HSBC)今年6月宣布,準備在接下來幾年撤離倫敦金絲雀碼頭(Canary Wharf)的總部,搬遷至面積更小的辦公室。據悉,新的總部空間只有原來的一半大。
據報道,滙豐這個45層樓高的總部大廈,鼎盛時期曾容納8000名員工,但居家辦公安排加上節約開支的壓力,讓滙豐決定在現有租約於2027年初到期前搬走。
滙豐曾在2021年宣布,將在疫後把全球辦公空間減少近四成。
縱觀亞洲城市,香港辦公樓的空置率也日趨顯著。
國際房地產服務公司仲量聯行(JLL)發表的數據顯示,截至今年6月底,香港辦公樓的空置率達12.6%,比起2019年底的5.9%高出一倍。

截至今年4月,香港共有1300萬平方英尺的空置辦公空間。(彭博社)
也有報道指出,截至今年4月,香港共有1300萬平方英尺的空置辦公空間,其中15%是高價值空間(valuable space)。
CBRE則指出,許多香港公司面臨的困境,不是居家辦公所引起的,而是中國企業租用辦公樓的需求比預期來得低。
新加坡辦公樓空置率不增反減
在這樣令人堪憂的大環境下,新加坡辦公樓市場反而上演逆襲。
本地辦公空間空置率偏低有兩大主因:
居家辦公風氣在新加坡不如其他國家盛行;
本地與外國企業對辦公空間的需求偏高。
一名業主接受《南華早報》訪問時說,「我的辦公室里,所有人都回來辦公了」,並補充說員工都是心甘情願回到公司上班的。

居家辦公模式讓不少企業面臨辦公空間空置率上升的問題,但新加坡市場似乎不太受影響。圖為本地上班族。(聯合早報)
根據房地產諮詢公司萊坊的研究報告,今年第二季,新加坡中央商業區辦公樓的整體占有率達到94.4%,同比上一季稍有增加。
此外,新加坡優質辦公樓的租金,今年上半年也增加了2.5%。
萊坊研究引述會計與企業管制局的數據指出,今年首五個月,新加坡有超過8000個新登記的企業和機構。即使在疫情期間的2021年,也有203家外國企業在新加坡註冊。
雖說辦公桌沒人用以及辦公室沒「人氣」,很大程度上是拜疫情所賜,但從長遠來看,其實也迫使許多僱主重新思考如何為公司節約更多預算,對企業而言不全然是件壞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