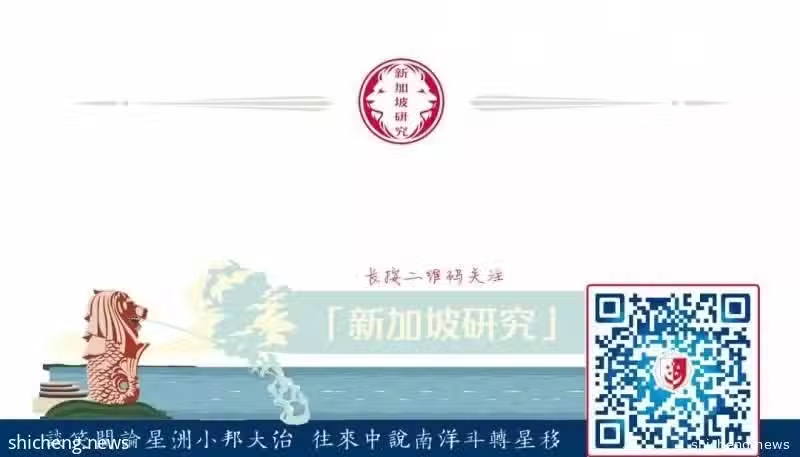無論政府也好,社會也罷,最終要實現的目標都是「有序」。假如罰款成了公務人員創收的手段,而不是實現公共秩序的途徑,這些禁令也勢必早已被顛覆。所以,無論政府是大是小,最終決定公眾態度的始終是政府的好壞。倘若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成了保護某些利益集團的堡壘,而不是為擴大公共利益而服務,這種干預一定是最壞的干預。
作者:查雯
很多遊客將新加坡戲稱為罰款之都,這裡罰金之高令人咋舌。但正得益於種種禁令,新加坡的清潔也讓人驚嘆。對於一個政府來說,頒布禁令並不難,但如何持之以恆地執行這些禁令,並將禁令的效力最大程度地發揮出來,卻是一個難題。增加執法者的人數,這顯然不是一個好做法。原因有二:其一,會增加監督成本。其二,執法者多了,那麼又由誰來約束執法者?
新加坡採取的顯然不是「人盯人」的做法,這裡並沒有很多執法者當街對亂扔垃圾的行人罰款,或者制止乘客在地鐵里吃東西。可以說,在很大程度上,新加坡公共秩序的維護,仰仗於民眾的自我控制。那麼這種自我控制又是如何產生的?
要回答這個問題,不得不提一下法國哲學家福柯,他從「全景敞式監獄」的建築設計得到啟示,對社會控制有過一番深入的探討。簡單來說,「全景敞式監獄」是一種圓形結構的監獄,囚室分布於圓周上,看守則在位於圓心位置的高聳的監視塔中。看守可以輕鬆地監視所有囚犯的活動,而囚犯卻無法看到看守。這種設計的獨到之處就在於,它大大降低了監督成本。監督可能是斷斷續續的,但囚犯們卻始終以為自己正在被監視。於是,他們便會注意自己的行為。「全景敞式」設計的力量就表現在它從不干預,卻可以促成自我監控。
在課堂上,我經常會問學生,為什麼新加坡人不隨地吐痰?不亂扔垃圾?為什麼新加坡司機看到人行橫道會主動停車?學生會坦率承認,自己真的害怕攝像頭,害怕身著便服的執法人員,害怕被罰款,害怕上報紙。
當然,有些人可能將類似的監控看作是國家權力的過度擴張。而諸如「實名購買口香糖」之類的規定,很有可能被視為對個人自由的侵犯。實際上,將國家對社會的控制比作看守對囚犯的看管,這個比喻本身就是對國家權力的挖苦。
那麼另一個問題出來了,「更乾淨的街道和更多的個人自由,你會選擇哪一個?」其實這並不是一個二選一的問題,遵守這些規定本就是公民精神的一部分,只有在你履行了這些義務之後,才能享有一個公民應該擁有的自由。
可以說,新加坡是一個「大政府而有序」的社會。這不符合一些人的審美,在他們看來,國家對社會如此細緻入微的干預和控制是不應該的,更值得推崇的是「小政府而有序」的社會。但新加坡人卻顯得十分樂於接受這個大政府。為什麼?問題的關鍵在於,無論政府也好,社會也罷,最終要實現的目標都是「有序」。假如罰款成了公務人員創收的手段,而不是實現公共秩序的途徑,這些禁令也勢必早已被顛覆。所以,無論政府是大是小,最終決定公眾態度的始終是政府的好壞。倘若國家對社會的干預成了保護某些利益集團的堡壘,而不是為擴大公共利益而服務,這種干預一定是最壞的干預。
(作者時為新加坡國立大學政治學系學者,現任職於外交學院國際關係研究所)來源:環球時報-環球網,請點擊「閱讀原文」查看源網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