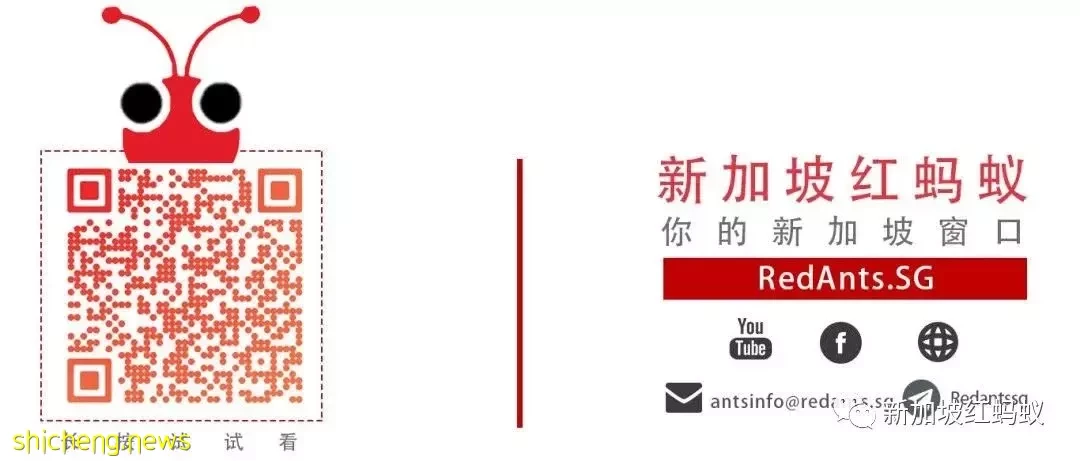鴿子群聚組屋窗外,留下糞便污跡斑斑。(聯合早報)
作者 盧麗珊
住在宏茂橋組屋區,每天打開大門可聽到清脆鳥鳴,因為七層樓高樹木的堅實枝椏是鳥兒築巢安家的地方。陽光下樹葉熠熠泛光,迎風飄動時的沙沙聲響和鳥鳴總是奏出不經意的歡歌。
一年幾個月從廚房窗口還可以聞到不知名大樹開著一簇簇的白花,濃烈花香在夜間慷慨放送給身居高樓的敏銳鼻子。
然而,城市生活中的大自然景象的平衡與和諧並不是理所當然,它取決於有效的協調和管理。
想像一下,當大樹枝椏上鳥群成患時,耳朵聽到的不是歡歌而是惱人噪音。這在很多組屋區很常見,尤其是傍晚時分,鳥屎遍地也就只能默默接受。

組屋底層成了鴿子聚集地。(新明日報)
話說宏茂橋同一個組屋的房子有時還會有蝙蝠飛進來叼走水果,不然就是留下咬了幾口帶不走的香蕉,讓人不勝其煩。
在鄰近的碧山公園的天橋和排水溝一帶,常會看到一群公雞或母雞,拖家帶口帶上一隊的小雞群,它們儼然是理直氣壯的「永久居民」。開車經過時,家人偶然看到它們還是莫名地開心起來。
就像中央醫院令人啼笑皆非的情況。有一陣家人住院,每天經過看見它們還是覺得蠻開心,周圍總有公眾停下來熱心喂食。事實上這已然對醫院造成極大困擾,即使貼上公告請公眾別喂食,野雞還是迅速繁殖,去年不得不見諸報章呼籲公眾不要喂食,「中央醫院花園已變成養雞場」。

中央醫院成了「養雞場」,百年紀念花園有至少20多隻野雞。(紅螞蟻攝)
說到底,還是一個度的問題。 情理上或情感上,大多數新加坡人傾向認為動物在生活中共存是可以接受的,只要它們不要入侵人們的生活空間並造成滋擾。只有當它們的數量增加或產生攻擊性時,它們存在的合理性才會受到質疑。
這將考驗和彰顯執政者處理問題的能力,以及與民協商溝通的品質。動物性或獸性在我們城市生活的蔓延和張狂只能凸顯某方面的辦事不力,或者公平一點來說是溝通上的不良和欠缺。
最終人搞不定的事,反而讓動物有空間無限制發力,導致有人無辜被傷害、被威脅、被無名的恐懼感占據,事件發生後又進而導致多方紛爭不斷。其實動物就是動物,難道錯在它們?
野豬和水獺繁殖都是多年未妥善解決的問題,報章寫了又寫,血流了還是再流,類似事件還是一再發生。
小販中心鴿子為患就是近年,尤其是疫情鬆綁後常在主流媒體被討論的課題。
它們成群出現在骯髒和凌亂的碗碟回收區,有時多到某塊區域都成為鴿子的「殖民地「,我根本無法靠近,也不敢靠近。望著受影響攤販無奈的眼神,也只能與愛吃的美食擦身而過。

新加坡小販中心內人在桌上用餐,鴿子在食客腳邊也吃得歡。(新民日報)
報章上也時有聽聞鴿子在小販中心食客頭上拉屎,導致大家四處竄逃的景象。當吃碗面的時間都變得奢侈,人的空間被侵占到只能逃逸和讓步的時候,我們該意識到某些方面失衡了、失控了。
日前一位義順組屋區店主為驅趕鴿子,以免影響麵包店生意,疑似用藤條驅趕導致鴿子暈厥,旋即將之裝袋拋棄。公眾見狀不滿使事件曝光,防止虐待動物協會義憤填膺,警方介入調查。我傾向同情店主的無計可施的下下策:運用『』私刑「。

麵包店老闆被指用藤條打暈鴿子(左下角),還將奄奄一息的鴿子裝袋丟掉。(新明日報)
鳥不知道自己只是一隻鳥,可是人卻知道鳥逾越了人的界限,危害了生計與和諧,因此發生這樣的事是多麼的遺憾。人最終被鳥搞出一堆麻煩事。
如果俄羅斯十九世紀寫實主義大作家契訶夫還在世,他可能馬上躲進房間創作一篇新的小說:
店主因打暈鴿子被判入獄,鴿子獲得經營麵包店的權利,終生享用它之前冒險被打死去偷取的麵包屑。
從寫實到荒誕,事件確實乖離了常態,失了控,求助無門被迫打鴿子難道就不足夠荒誕?
可憐的是鴿子,可悲但無奈的是店主。
最近水獺闖入武吉寶美組屋區吃掉居民魚缸的七條鯉魚,視頻看到「慣犯」水獺兇狠很的模樣,真是觸目心驚。難以想像,水獺在未來膽子越來越壯大的結果會是什麼?

闖入武吉寶美組屋區吃掉居民魚缸的七條鯉魚的水獺。(新明日報)
訪問每周末一定全家大小到公園跑步的匿名朋友,他對於人獸在城市空間共存的課題傾向保守,也可能代表一部分人的想法。
他認為,水獺這些小動物難道不是應該被關在動物園裡?他說,很多人並不知道只要保持距離,不去惹它們,水獺還算是安全的。只是並非每位公眾都具備這樣的意識,風險還是一直存在,只是在「等事情發生」。
放眼未來,城市生活的多樣性和豐富程度取決於我們如何平衡各方面的需要。有關當局做了很多的努力,然而這些年來不殺(動物)會被罵。好吧,去撲殺了,還是會被罵。
畢竟問題總是比辦法多:在殺與留之間還在輪番上演的,是人類最原始、最哲學性的一場與大自然的博弈和對話。挑戰之大,比想像中大得多。
我們既要感性地尊重動物存在的權利、讓我們有機會感受動物世界帶來的生機勃勃及其樂趣,也同時要客觀和理性地評估,並達至全民的共識:
如何才能在城市空間的局限性當中找到人獸和諧共存,減輕風險的可持續共同生活的理想方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