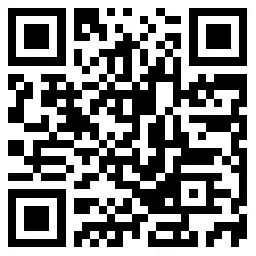成為同傳口譯員,需具備什麼條件?
首先,至少要精深掌握兩種語言。
第二,反應要快。因為口譯與筆譯畢竟有分別,我們在現場不能翻查字典,必須隨機應變,臨陣不慌,快速找到對應語言的最佳闡釋。
第三,具備終身學習的能力,因為我們工作的領域沒有界限。我們必須在短時間內掌握別人研究了好幾十年的東西,再加上工作的範圍非常廣泛,今天是法律,明天是醫學,後天是IT,需要快速抓住全新的專業知識和用語,以專業權威的口吻來傳達給聽眾。
口譯員需要「廣而泛」還是「專而精」呢?
應該介於兩者之間。口譯員需要有一定的視野與背景,才能跟其他人建立共鳴,特別是翻譯對象往往是各領域的專家,例如一個學者在同一個領域深耕了幾十年,講的內容極為精髓化,口譯員必須快速消化、理解,並用觀眾能理解的語言翻譯過來。
他們好比是「行走的智庫」,每一行都要懂一點,還要有進一步的理解,不能流於表面,所以必須又廣又精。我們除了做好會議準備外,還要有相關的日常累積,如閱讀專業書籍,甚至上課。亞太區的口譯市場很多元化,海事、諮詢科技、區塊鏈等,如果我們只專注一個領域,可能沒法養活自己。
口譯員無法挑工作,但客戶是可以挑我們。例如銀行業的峰會,與會者都是業界精英,他們的「黑話」(指專業術語)非常多,客戶會找具備精專背景的口譯員。一般高階的口譯員,必須在幾個領域有深專的知識和口碑。
口譯其實已遠遠超越了語言的轉換,更深層的是文化的傳遞,例如英語就有很多種,不同地區的語言習慣、風俗等也要分清楚,否則講者冒出一些俏皮話、雙關語甚至涉及地域特色的話來,你就不知如何應對。
口譯也是一種再創作。當看到台上的演說者充滿能量的演說時,口譯員也要將這種活力通過語言語調給表現出來,而不是純粹文字上的照本宣科。也許你以為翻譯只需要懂得雙語就可以做,其實不然。
口譯可分哪幾類?
如果按口譯形式來分,除了同聲傳譯與交替傳譯外,還有大眾比較熟悉的陪同傳譯(Accompanying Interpretation),顧名思義就是陪同國家領袖或企業總裁出席會議的隨身翻譯,這也屬於交替傳譯的範疇之內。
有時領導人私下會散步、聊天,他們可能會採用耳語傳譯(Whispering Interpretation),這是接近同步傳譯的方式,當對方領導講話時,口譯員就會給領導人「耳語「(耳邊輕聲翻譯),翻譯是同傳進行的,不需要等對方停下再翻譯。
上述提到的都是單向翻譯,雙向翻譯是由一名口譯員為交談的雙方,完成兩種語言的互譯。
口譯員多是新移民嗎?
要看語種,因為新加坡百分七十是華人,中英口譯相對來說新移民比較少,因為群體少,能夠做口譯的就更少。至於其他語系如日語、韓語等,本地人沒有優勢,自然清一色是新移民,所謂的新移民在本地也是積累了一些生活經驗,不是剛來的一兩年的新移民就能勝任的。
口譯員面對的最大挑戰是什麼?
從口譯員的曝光率、從業人數和公眾對其了解來說,它的確是屬於小眾行業,其重要程度往往被忽視。一直以來,口譯員就是隱形人,主角永遠是演講者、領導人,即便口譯員就站在他們身旁,也沒有多少人去注意。在國際會議場上的同傳箱,很多人都不知道那是什麼,曾有會議嘉賓在手機響起時,跑進來接電話,以為是個休息間。
如果公眾不了解,對行業是很不利的,因為他們不理解我們的工作需求和重要性。最大的困難是,跟會展公司、政府機構、大型公司一起工作時,很少主動積極地配合我們的工作,很少提供充足的準備材料和會議細節,大家覺得你是翻譯,到時出現就行了,這對我們的工作造成極大的不便,最終受影響的其實是聽眾。
在會議前,我們需要做幾方面的準備,例如了解這個會議的內容、日程安排、與會嘉賓的個人背景、身份等。另外,還會到網上找演講者的視頻來看,了解和提前適應他的講話習慣、節奏、口音等。當然最理想的狀態是可以收到演講嘉賓的講稿、演講內容等原材料。
上述說的是一種理想狀態,事實上資料總是不足,並且一般是會議馬上開始了才到我們手裡,還不一定是最終版本,所以我們這行很需要公眾的認識、諒解,以及社會的支持。
疫情對口譯造成什麼影響?
對口譯行業來說,即便疫情過去,或許也回不到疫情前的模式。基本上,以後的會議都會轉型為混合(Hybrid)模式,例如現場1000人,另外的2000人可能在線上聆聽,演講嘉賓或譯員也未必需要在現場。
觀眾甚至可能不必到現場,靈活安排,只是選擇參與自己感興趣的一個小分會,而不是舟車勞頓大老遠飛來參加幾天的全會。以前要在現場設置很多機器設備,但往後可能只要一台電腦連結上網,就可以進行口譯與聆聽,也大大減少了工作人手和流程。
對口譯業來說,因為觀眾群的擴大,對翻譯語言的需求會相應增加,對會展行業來說,成本會減少,但效率卻大大改善。口譯行業正處在一個轉型期,無論是供應者如主辦單位與口譯員,還是最終使用者都在適應和過渡,變挑戰為迎戰,化危機為機遇。
作者
宋鵬博士,口譯顧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