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以來,由於開放的自由貿易政策和寬鬆的移民准入條款,加上其不斷完善的基礎設施和司法制度,新加坡憑藉其獨有的地理優勢,在19世紀30年代一躍成為亞洲最大的貿易港口。
新加坡的這一發展勢頭,在1840年前,隨著中英關係的緊張而關閉的廣州港貿易,而達到了頂峰。
在19世紀40年代時,新加坡的人口總數已經由之前的1000餘人擴展到2萬餘人,而華人群體也在近30年的發展中,一躍成為當地最大的社會群體。

根據官方統計資料顯示,當時的新加坡有各種商社43座,其中英國人占20座,猶太人占6座,華人占5座,其他主要由阿拉伯人、歐洲大陸人、美國人所有,他們利用新加坡便利的貿易設施和寬鬆的自由貿易政策,幾乎壟斷了對暹羅和中國的貿易,然而新加坡的這一發展勢頭卻在1840年後逐漸消沉,並陷入了衰落的20年,這又是為何,和中國有著什麼樣的關聯呢?
襲擾不斷的海盜
應該說新加坡自1819年開埠之初,就一直面臨著海盜的襲擊風險,這一方面是由於新加坡本身的地理位置極易作為海盜襲擊的目標,另一方面是由於新加坡薄弱的防守力量,新加坡在開埠之初僅有30餘名士兵駐守,後來隨著城鎮的發展駐軍人數上升到了500名左右,但用於海上防禦的力量卻只有一艘小型炮艇,這些武裝力量足以防衛新加坡自身,卻不足以清理新加坡周邊的海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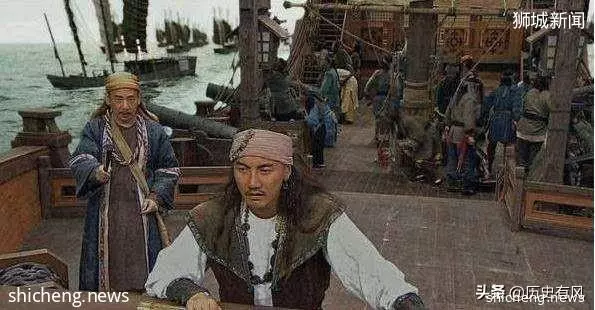
最初的海盜行為主要來自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受限他們的小團隊特點和落後的航海技術,他們在新加坡土著酋長天猛公的暗中支持下,主要以小型的亞洲商船為襲擊目標,一旦得手便迅速撤離到島上的密林中銷贓。
這種肆無憚忌的海盜行為嚴重影響了新加坡的自由貿易,然而隨著華人商會自發組織的警備船隊的投入巡邏,當地的貿易逐漸恢復秩序。
但這種情況卻在1840年以後,隨著中英戰爭,清朝的慘敗而捲土重來,並且有了更大規模的席捲。
從1850年開始,隨著中國國內經濟的不斷崩潰,加上戰爭的肆虐,越來越多的掙扎在生死線的沿海貧民開始通過清朝被迫開放的那些通商口岸向海外求生存。

他們中有很大一部分人組成了團體性的海盜船隊,這些船隊區別於20多年前來自馬來半島和印度尼西亞群島的小型船隊,這些華人海盜團體不僅船體噸位重,且規模大,其襲擊目標不再局限於小型商船,即使是大型的歐洲商船也被肆意襲擊。
而此時,英國為了維護海峽地區的貿易線路,已經在新加坡加派了三艘蒸汽船,真極大的提高了當地防務的效率,然而要應對規模龐大,數量繁多的華人海盜,他們依然捉襟見肘。
在最高峰時,這些華人海盜船隊曾公開駛入新加坡港口,帶著武器對搶劫的商品進行銷贓,英國殖民當局稱強烈要求清政府清理這些來自中國沿海的海盜,然而一方面清政府在當時明顯沒有能力控制這些具備遠航能力的海盜,另一方面某種程度上這也是他們喜聞樂見的,畢竟這些海盜實現了清政府一直想做卻沒有做到的事。

猖獗的華人海盜船隊一度讓新加坡的貿易陷入低落,大量的商人由於懼怕在新加坡海域被劫掠,而不得不繞道其他航線,甚至停止了貿易,根據統計在1854年時,途徑馬六甲海峽的商船僅有不到三分之一能夠順利到達目的地。
一名英國商人甚至語言,新加坡的自由貿易港地位即將衰落,這種情況一直持續到1860年初,英國海軍大舉在南中國海的活動而改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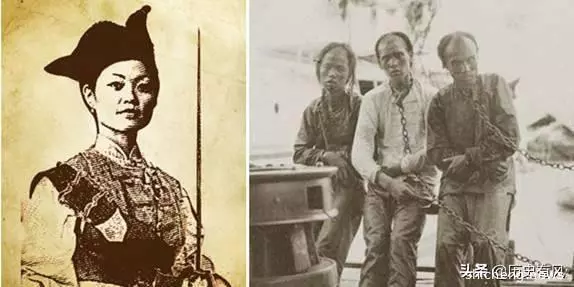
中國口岸的競爭
新加坡殖民當局和當地的商人,曾經在1840年前中英關係緊張時,希望能夠承接已經關閉的來自廣州港的貿易,然而英國的勝利卻讓這種希望化為泡影,並且還威脅了新加坡自身的貿易地位。
英國在取得對華戰爭的勝利後,不僅將香港島開闢為新的殖民貿易港口,同時也開放了更多的中國其他沿海港口,這些港口的開放,對來自印度和歐洲的貿易商船具有極大的吸引力,從1842年五口通商和香港開埠開始,有至少一半的商船選擇直接前往香港卸貨,而不是在新加坡,這對於極度依靠轉口貿易的新加坡而言,完全就是一記沉重的打擊。

混亂的貨幣制度
新加坡作為英國的海外殖民地,與其他殖民地不同的地方在於,其位於荷蘭和西班牙的殖民包圍中,因此在開埠之初,新加坡當地使用的貨幣就包括荷蘭銅板和西班牙銀元,而沒有英國的法定貨幣,這對於殖民當局而言是無法接受的,這將影響殖民地當局的財政收入。
1885年時,為了禁止非英國法定貨幣在新加坡的流通,印度殖民當局通過了一項法案,希望在新加坡發行一種直接與英國法定貨幣直接掛鉤的新貨幣,這一行為讓當地商人誤認為是要取消銀元而採取的第一步驟,而遭到了抵制。

英國殖民當局被迫在1857年撤銷了該法案,這導致當地的貨幣制度依舊處於混亂之中,其幣值漲跌也完全超出英國控制之外,進而影響了新加坡的自由貿易港的地位。
這三種因素的疊加,讓新加坡在19世紀40至60年代的20年時間裡陷入了衰落,而這一期間也正是歐洲殖民東擴的高峰期和清朝自強意識覺醒的萌芽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