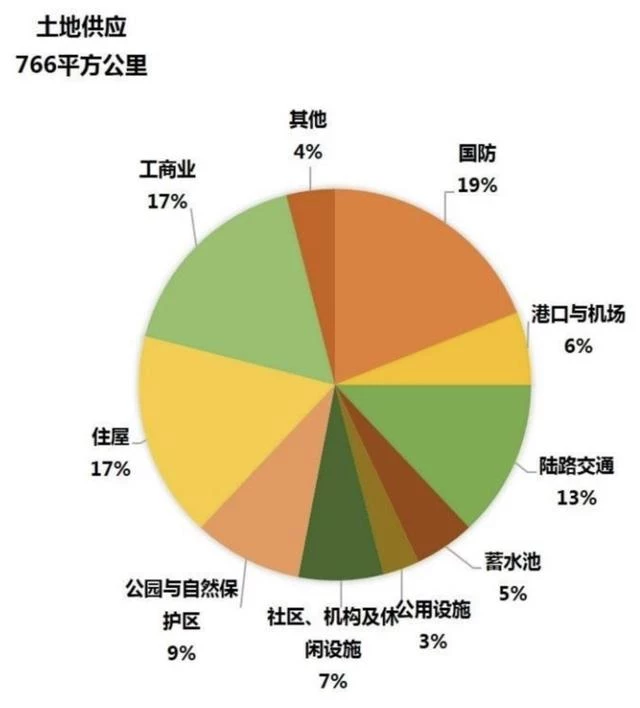
即使可用土地增加了,也依然滿足不了新加坡人日益上漲的土地需求。事實上,新加坡的鄰國馬來西亞和印度尼西亞一直以來都對其填海造陸行動保持謹慎立場,而出於領土糾紛,兩個鄰國相繼拒絕向新加坡繼續提供沙土資源,而印度和越南等遠方的朋友,也因新加坡對沙子如此龐大的胃口而決定不再向其供應沙子,以致沙子的價格暴漲到了誇張的地步。為了應對新的資源掣肘,新加坡人則不得不開始囤起沙子,政府甚至還嚴格地跟蹤各種等級建築材料的儲備情況。另外,新加坡人也有意通過新的方式,包括回收利用挖掘或鐵軌建設產生的物料、圍墾等方式,以減少對沙土資源的依賴。
同時,缺乏水資源也是新加坡人頭疼的問題之一。因為這個彈丸之地的小島已經超城市化了,有無數的工業設施,民生工程,以及數百萬的人口,都嚴重依賴於清潔淡水。雖然夏季風暴總會帶給當地人十分可觀的降水量,但這終究不會是長久之計。國內的清潔用水主要來自於馬來西亞的柔佛海峽上游的林桂水壩,但建立在水資源上的兩國供水協議遠非一勞永逸地可靠,地緣政治以其最全面的方式限制著這個國家的命脈。所以,新加坡人會盡其所能地像儲備沙子那樣地認真儲備水資源,節約用水是這個國家反覆提倡的美德,而水資源循環利用則滲透在這個國家的方方面面。
新加坡就像一個民族的大雜燴,各色人等共同居住在這片土地上,其主要人口是華人,剩餘的則是馬來人、印度人以及世界各國的移民。在現實世界中,不同民族之間始終沒有很好地融合到一起。事實證明,與華人社區相比,馬來人擁有更低的社會地位和受教育程度,馬來人在學校的表現較差,接受高等教育及社會培訓的人數則是少之又少,或許這其中也隱約摻雜了部分歷史成因。早在馬來世界被西方殖民統治以來,新加坡社會與馬來社會之間的這種差距就已經體現出來了,後者更傾向於從事農牧、狩獵等體力勞動,而不像前者那樣孜孜不倦地追求科學與文化的進步,以至還有一種頗為流行的說法聲稱,新加坡之所以與馬來世界截然不同,就是因為彼此的民族分布不同,因為在新加坡,華人占主導地位,而在馬來亞,華人卻是少數族裔。
新加坡政府對待民族間的差異,就像對待一顆定時炸彈,如果不小心處理好國內族群間的關係,國家就可能出現分裂的危險。新加坡對待國內少數民族問題一直採用的是懷柔政策,而在鄰國馬來西亞,馬來人則長期奉行歧視異族政策。在一馬發展有限公司醜聞被揭發以來,馬來西亞國內的經濟發展長期陷入停滯,上任的馬來總統納吉布是個穆斯林,他固執地將國內民族問題與宗教問題結合在一起。2017年《海峽時報》曾報道,馬來西亞對所有伊斯蘭國(ISIS)戰鬥人員實行免簽政策,同年就有30多名伊斯蘭國戰鬥成員在伊斯坦堡被拘捕後,通過巧妙的外交角力得以被送往馬來西亞。即便新加坡在面對鄰國因貪腐現象和經濟衰退時一籌莫展而幸災樂禍,但它也不得不憂慮自身的安全和安保問題,畢竟彼此之間僅僅相隔的是一道淺淺的海峽。
從地理上看,新加坡是馬來世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只是它被人為地抹上了華人的顏色,但在面臨自身地緣條件限制時,新加坡又不得不撇開彼此間巨大的文化差異,與後者尋求認同與協作。當一位新加坡居民在採訪被問到如果新加坡的奇蹟要終結了,國家該怎麼辦,他面色凝重,深吸了一口氣,似乎並不想聽到這個問題;最終在記者的反覆催促下,他才緩緩回答道,「重新加入馬來西亞」。他無可奈何的語氣說明了一切,對新加坡而言,重回馬來西亞並不是統一,而是承認自己失敗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