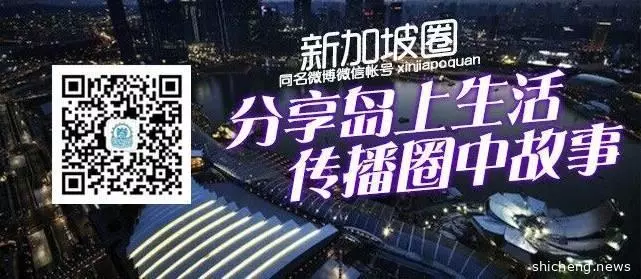於是,本著科學的精神,Fallon又給自己做了詳細的基因檢測。從基因檢測的結果中,Fallon發現自己擁有所謂的「戰士基因」:這是一個位於X染色體上的基因,代號MAOA,與人的多巴胺、去甲腎上腺素、血液復合胺的分解有關。如果它沒有正常工作,這些神經傳遞素的堆積將會造成人的反常情緒,導致人的暴力行為。
所以,這也是第一個被確定的與人類攻擊性行為有關的基因。自從這個基因的功效發現問世以來,有越來越多的科學研究證明,MAOA和暴力傾向之間的確存在聯繫,如果擁有這種戰士基因的人在兒童時期受到了虐待,將更容易做出反社會的暴力行為。

(圖:來源自網絡)
這個發現,讓Fallon教授將對自己的研究重點放到了自己童年的回憶中。曾經被他忽視的很多童年細節,成長經歷,開始慢慢浮現在他眼前。漸漸地他發現,原來自己並非完全沒有心理變態的前兆,只是被掩蓋和遺忘了...
這其中的答案就是——父母養的好
因為童年有足夠愛,所以沒有長成變態
回憶童年,Fallon最大的感受是快樂。
他出生在一個和睦健全的家庭中。在他出生前,母親經過了多次流產,乃至於終於得到了Fallon這樣一個健康的寶寶後,一家人都格外珍惜。父母從小對他也是用心呵護,並沒有給他帶來什麼難以忘懷的傷害,更不用說是虐待了。
但越是這樣平靜快樂的童年環境,就越能凸顯出Fallon身上一些「莫名其妙」的不尋常特點。
首先,他是一個非常爭強好勝的人,但凡是比賽、競爭,都喜歡爭個輸贏,就算是玩遊戲打紙牌都非常認真投入,想盡辦法就是要贏,常常會惹怒和自己一起玩的人。這個習慣一直延續到了現在,就像妻子說的,自己好勝心強到連自己的孫子孫女都不放水,的確有點奇怪;
其次,細細想起來,小時候他還是有一些暗戳戳的叛逆行徑。比如他曾經自製了管狀炸藥來玩,偷了別人的車子來玩,青春期時候還悄悄地闖進店裡去偷酒喝。每一次遇到警察被攔住的時候,他都是小夥伴中最淡定的那個人,完全不會表現出焦慮、緊張、愧疚等常見的犯錯後的狀態,乃至於每次被警察問話後他都是最快被放走的那個人。
他並不是能裝,而是真的很淡定,感受不到那種緊張。而且,他做這些事情的動機好像純粹是為了開心,比如偷了東西後總是會原封不動地還回去,仿佛享受的是過程而不是結果。
最重要的是,在他長大後,這種不尋常的行為還是時有發生。

(圖:來源自網絡)
比如,1990年代Fallon曾有一段時間住在非洲。當時他的一位好兄弟從紐約過來探望他,Fallon帶著這個朋友去了烏干達和肯亞邊境的埃爾貢山基塔洞穴,遊玩了兩天後便送朋友回美國。
大概兩年後,這個朋友憤怒地找到Fallon,說再也不相信他了,因為朋友後來才知道,Fallon帶他去的那個洞穴是致命的馬爾堡病毒的起源地,但Fallon當時對此隻字未提。如果早知道那個地方這麼危險,他說什麼也不會和Fallon一起去的。更不用說當年Fallon還帶著自己16歲的兒子,在那附近篝火、釣魚、露營的時候,真的遇到了獅子豹子之類的野獸,其他家人們都害怕得躲在車裡,Fallon卻不以為意繼續帶著兒子在外面玩....
這樣想想,Fallon覺得自己有時候是真的挺混蛋的。
如果不是確認自己的功成名就是真的、家庭美滿也是真的,這些行為放別人身上,不就是自己研究的潛在反社會人格嗎?

(圖:來源自網絡)
但是,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自己沒有真的發展成一個反社會變態,把變態心理付諸行動呢?
經過深刻的反省、回憶後,Fallon認為是自己快樂的童年讓自己免於變態。
簡單說,他在成長過程中由於家人給予了足夠的愛和關懷,儲存了足夠多的「善良和快樂」,使得他即便長大後偶爾發神經做一些奇怪的事情,也能懸崖勒馬;由於足夠好的引導,他把爭強好勝的力氣用在了正途上。
「我回憶起母親,想起她在院子裡,坐在三角凳上修剪杜鵑花。當時我心裡就想,她就是我凳子的第三條腿。我有精神疾病患者的基因和大腦,但母親是那條防止我傾覆的第三條腿。
她總是堅定地認為我是一個好孩子,是她幫助我茁壯成長,成為了一個善良聰明的人。我被愛了,是這種愛保護了我。」
也是這個回想,讓Fallon提出了一個「三角凳」理論:決定一個人變態心理的主要有三個方面:基因,大腦損傷,以及環境因素。
他擁有戰士基因和心理變態者的大腦結構,但卻由於成長的環境充滿了善意和愛,避免了他心理最終的垮塌和變態...
如何預防自己犯罪?
反覆問自己:善良的人會怎麼做!
對自己的成長經歷有了從外到內深刻的研究之後,Fallon意識到自己這一路走來是多麼兇險。除了感謝自己的家人、父母還有妻子總是在對的時間引導他做對的事情外,Fallon也渴望能夠靠自己建立起一種能約束自我變態心理的機制。
因為在Fallon原有的研究中,自己這樣的人是非常危險的,大腦的構造決定了自己就是衝動易怒情緒化的人,缺乏自發的同理心,在理智上能夠理解道德原則但是在情感上缺乏適當的同理心。
所以為了彌補這一缺憾,Fallon開始培養自己一個心理習慣:當他遇到一些糾結的問題時,他會反問自己,「一個善良正常的人,在這樣的情況下會怎麼做?」
通過這個習慣,他漸漸改正了許多生活上原有的毛病。
比如,當他妻子的家人過世的時候,Fallon原本想隨便找個藉口推脫掉葬禮。但在反問自己過後,他意識到一個善良的人應該懂得,自己的陪伴對妻子來說很重要,於是放棄了去海邊喝酒的計劃,陪妻子回去參加了葬禮。
類似的事情還很多,妻子也表示在Fallon對自己深刻反省研究過後,他變得更加體貼,懂得尊重別人的感受了。
如今,Fallon教授關於「天生變態狂」的研究,在經過對自己的懷疑和反省後得到了深化。他開始面對公眾講述自己的故事,並帶領大家一起探討在變態心理方面,「天生的生理特徵」和「後天的成長環境」之間的關係。
Fallon的理論吸引了很多人,2009年時,他還受邀客串了著名美劇《犯罪心理》中的一個心理變態的心理學教授:在劇中介紹自己的理論,簡直是在本色出演...
經過這些年的研究,Fallon的理論仿佛又回到了一個「模擬兩可」的階段:既不是完全的基因決定論,但也並不認為足夠完美的成長環境就一定能避免心理變態的養成。
在如今年近70的Fallon眼裡,多年的科學研究能夠告訴他的最重要最明確的道理就是:人性是複雜的,人的善惡行為的產生過程也是難以捉摸的。關於善惡形成的原因,像Fallon這樣的科學家們還會繼續研究下去。
不過,公眾從Fallon的故事中可以得到肯定的是:有愛的環境更有可能避免個人走上歪門邪道,而童年的創傷和虐待,不管是否會改變大腦的結構,都更有可能催生出心理變態者...
對於有理性的成年人來說,就算在情感共鳴方面有欠缺和遲鈍之處,但如果能夠同Fallon一樣自省,刻意學習去做一個善良的、富有同情心的人,那最終也能過出平靜正常的人生,給自己也給自己周圍的人帶來快樂和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