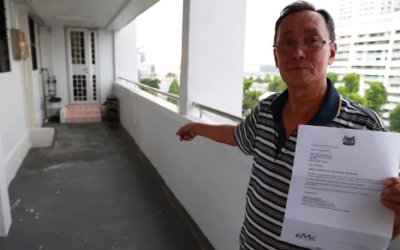新加坡總理李顯龍3月30日出席華盛頓智庫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對話會,活動由協會會長哈斯(Richard Haass)主持。兩人就烏克蘭危機、國際安全架構和氣候危機等多個議題進行討論。以下是對話全文。
00:00 -【烏克蘭局勢的後續影響】
理察·哈斯:首先,我想談談本周早些時候您與拜登總統會晤時發表的聯合聲明。我想特別引述聲明的一句話:「烏克蘭戰爭對印太地區產生了負面影響。」首先 我想請您說明一下,為什麼這麼說 又會如何影響?您能否具體地說明?
李顯龍:烏克蘭戰爭在多個層面都對亞太地區造成影響。首先,它破壞了國際關係框架中的法律和秩序以及國家之間的和平。它違反了《聯合國憲章》也威脅到所有國家的政治獨立,主權和領土完整,尤其是小國。如果大家接受瘋狂決定和歷史錯誤為入侵他國的理由,我想在亞太地區乃至世界其他地區的許多人都會感到很不安。
第二,事態的發展以及歐洲已開發國家和俄羅斯之間關係的損壞,已讓全球多邊合作體系,無論是在貿易、氣候變化、預防大流行病還是防核擴散等方面,難以運行。我們之前能讓敵對國家和競爭對手即便有分歧,也還是能以雙贏的方式進行合作的框架 已不復存在。
當今格局是一個非贏即輸的局面。你希望對方倒台,要修理它,並搞垮它的經濟。在這樣的情況下,絕大多數國家要如何儘可能地團結起來,相互合作,而不是陷入混亂、經濟封閉或無政府狀態?這對新加坡來說是一大隱憂,因為我們依賴全球化生活。
第三,烏克蘭當前的危機必將對美中關係產生重大影響。這場危機必定會,也已經使關係緊張。我們希望拜登總統與習近平主席在最高層級的聯繫能促成理性決策,而雙方的關係也能保持下去。換句話說,我們希望美中關係不會變得比現在更糟,但這是無法預知的。儘管雙方都盡了最大的努力,如果美中關係惡化,這將對整個亞太地區乃至全世界帶來更深遠的影響。
個別國家也對烏克蘭即將發生的事情作出具體反應。每個國家現在都會問,我們能從烏克蘭危機中吸取什麼教訓?就國防而言,當我們需要幫助時,我們可以相信誰會向我們伸出援手,這樣的意識在東北亞尤為明顯。
日本前首相安倍晉三已提出應該考慮在日本部署美國核武器。我相信一些參與戰略課題的日本人此前已有這樣的想法,但現在安倍先生已將此課題擺到台面了。(日本)政府當然已拒絕這樣的提議,並說他們永遠不會這麼做,但這個念頭已經種下,而且不會消失,因為烏克蘭局勢顯示了核威懾可以非常有用。
我想韓國也有同感。如果你看民調,大多數韓國人認為,韓國應該發展核能力,不僅僅是像以前一樣部署美國的武器,而是發展它本身的核武能力。如果局勢真的朝那方向發展,如果你是個樂觀主義,你會說:現在朝鮮、韓國、日本、中國都擁有核武器,那我們已取得穩定的核平衡;如果伊朗、土耳其、沙烏地阿拉伯和其他中東國家也擁有核武器,那將會帶來更大的核平衡。你希望這仍是個穩定的平衡,但我認為我們正朝著非常危險的方向前進。
至於誰會向你伸出援手,我想各國會做出一些考量。亞太區域的框架與歐洲的框架不同。歐洲有北約、有第五條款、有前華沙條約國家、有前蘇聯的共和國等。所以哪裡是界限,哪裡是不可觸及的紅線,情況都有所不同。在亞洲,我們並沒有這些框架,但我們有台灣問題,有「一個中國」政策。而美國這一邊有《台灣關係法》,但美中之間又有《三個聯合公報》。我們應該如何詮釋這些體系?局勢又將如何發展?
以台灣目前的防務情況來看,他們希望能將兵役制度的服役期,從現行的四個月延長至12個月,我覺得這不太可能。因為要讓大家接受更長的服役期並不是件容易的事,至少現在的民意是如此。還有另一項台灣民意調查顯示,如果台灣出事他們認為誰會派兵幫忙,有40%的受訪者相信日本會協防颱灣,而30%的受訪者則認為美國會派兵介入。在去年10月進行的類似民調中,三分之二的受訪者認為美軍會出兵助台。
因此,我認為各政府會做出考量,他們不會一夜之間做出大轉變,但這都是重要的戰略性重估。我覺得除了要對烏克蘭當前局勢做出回應之外,我們也需要思考在亞太地區導向衝突的路徑會是什麼,以及如何避免衝突發生。(一個國家)必須考慮應該建立什麼樣的制度 程序和聯繫,以及做出什麼樣的戰略安排,以避免無法防止衝突而被迫進入防禦狀態。
在歐洲,學術界一直在針對烏克蘭危機進行爭辯。現實主義者如政治學家約翰·米爾斯海默(John Mearsheimer)認為,如果北約沒有東擴就不會發生今天的局面。另一些人則認為 ,烏克蘭危機是無法避免的,波蘭和波羅的海國家都已是北約成員。那在亞洲,我們沒有北約,不過我們也有需要關注的熱點,有棘手的問題需要處理。我們需要機制讓處於對立的國家、對手與美國互動、中國互動、關係已密切的國家互動,讓我們能夠做出非常艱難的調整,那就是如何適應中國,一個更發達、體量更大、科技更先進,但同時不會對世界盛氣凌人,並能被當今全球主要軍事強國美國所接受的中國。
我們必須往這方面前進。我們有亞太經合組織(APEC),這對我們很有幫助,因為它側重討論經濟課題。我們也有東亞峰會,能讓各成員國就戰略性課題展開討論,但在落實有關措施方面,該峰會並沒有發揮很大的作用。目前,美國有意建立印度—太平洋經濟框架來聯繫本區域,不只以戰略或安全和潛在敵意為基礎,而是以取得雙贏為基礎。
我認為你需要考慮到這一點,讓事情能朝向一個不會導致激烈衝突的方向發展。

(海峽時報檔案照)
09:58 -【本區域對美國的看法】
哈斯:謝謝您和我們分享這麼多意見和看法。在這個會議室里,我看到許多我的前同事。我們都曾參與聯合聲明的書寫和簽署工作。這份新加坡和美國簽署的聯合聲明值得一讀。它的實質內容比我所參與的許多聯合聲明都更充實。我不會代表你們當中的幾位發表意見,但我確實推薦它,政府偶爾會信守承諾,而這是其中的一次。
您說了一些我想提出的問題,但我想跟進一下,那就是本區域對美國的看法。所以我的問題是,美國在這次危機中為烏克蘭提供了在我看來是「間接的支持」,包括在軍事、外交和情報方面的顯著支援。最明顯的是經濟制裁和其他措施,卻並未提供直接軍事支持。它拒絕了在烏克蘭設立禁飛區,也拒絕派兵參與地面作戰,這是一個值得參考的一點。這屆美國政府在重要方面的做法和前任政府非常不同。
所以,當人們現在觀察美國,美國在台灣和烏克蘭做什麼、不在做什麼,這是否增強了人們對美國的信心?顯然的,您不認為情況是如此。
李顯龍:我想各個情況都不同。正如我所說的,歐洲有北約,知道在北約課題上的邊界在哪裡。在亞洲 我們沒有北約,我們有三個聯合公報,在台灣問題上也採取了戰略性模糊的政策。
我想大家都希望看到台灣能維持現狀,即使有任何改變,也絕不能以武力或非和平方式發生。這是很難處理的問題,因為它不只是經濟或戰略問題,而是關乎政治和民眾情緒的問題。所以,這是一個需要很長時間才能解決的問題。
哈斯:但您是否擔心,由於俄羅斯可能會再次對歐洲秩序構成重大威脅,所以美國轉向亞洲的戰略不會實現?相反,美國在轉向亞洲時,又幾乎得繞道回去歐洲?
李顯龍:美國向來關注全球課題。我的意思是,如果不是烏克蘭,就會是伊朗,或者是發生在世界上其他地方的其他事情。你們不時也會關注拉丁美洲。所以我認為,我們接受美國在全球擁有廣泛的利益,但亞太地區不僅有中國,與中國的關係是美國必須處理的。
但另外,亞太地區也有許多美國的其他夥伴,當中一些是美國的盟友,其他則是你們的朋友。他們多數與美國有著非常密切的經濟聯繫。二戰後近80年來,美國拓展了這些關係和利益,促進了這個全球相對穩定與和平的區域。因此,無論你有什麼其他廣泛的利益,這都是你無法捨棄的。
我認為歷任美國總統都明白這一點,並都親自關注這個問題。但我無法想像他們因為只關注這個問題,而把其他的事情都排除在外。我也不認為他們會因為忙於其他事務而忽略與中國的關係。我們所擔心的是,在與中國打交道時,美國是否有時間和興趣?是否還可能與東南亞和本區域其他國家展開聯繫?
14:16 -【中國就烏克蘭局勢的反應】
哈斯:讓我們談一下中國的情況吧。有些人,我得承認包括我在內,提出了這樣的觀點。俄烏之戰讓中國有所省思,美國和它的夥伴們,包括新加坡在內,對俄羅斯的制裁既廣且深,也確實是前所未見的。而中國要比俄羅斯更像是一家投資和貿易公司,因此可能更加脆弱。此外,各國所做的其實是在間接保護烏克蘭。而正如您所說的,我們所持的戰略模糊立場,並不排除直接保衛台灣。
從北京的視角來看,您是否察覺到,中國已有所反思,認清自己在本區域甚至以外,需要付出一定的政治代價,因為他們和一場戰爭有密切的聯繫?而這是一場被視為是因個人私利而發動的異常殘酷的戰爭。
李顯龍:我想這讓他們面對尷尬,因為烏克蘭戰爭,違背了中國非常重視的原則:領土完整、國家主權、互不干涉內政。如果你能這樣對待烏克蘭,將頓巴斯視為獨立個體或可能是共和國……
哈斯:那台灣呢?
李顯龍:或中國其他非漢族地區?所以說,這是非常棘手的問題。從制裁行動也可看出,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是密不可分的。因為大家有生意往來,在彼此國家互設帳戶,而任何國家,尤其大國 ,都有可能拆毀他人的房子。我可能擁有很多美國國債,但如果美國決定凍結這些帳戶,那就會帶來實際的經濟損失。所以,我們都是相互依賴的。反過來說,如果你切斷與中國的聯繫,認為沒中國也無所謂 反正你沒在中國的銀行擁有同等規模的帳戶,可是你們的經濟是相互依賴的,中國是你最大的貿易夥伴之一,是許多美國公司的製造基地,這些環節一旦斷裂,勢必也會傷害到你。這並不是說你會陷入很糟糕的情況,但我想雙方都會意識到 這麼做的代價是非常高的。
還有一點:我不認為在本區域內,中國會因為拒絕與俄羅斯保持距離,而承擔什麼代價。處在這個區域的所有國家,都在乎國家主權和《聯合國憲章》。但同時也希望與中國維持關係,而其中也有不少國家與俄羅斯也關係密切,如印度。所以,中國如今採取了自己的立場,並認為你現在反倒來要求他們協助解決俄羅斯問題,而中國的回應是:解鈴還須繫鈴人。換句話說,你自己的問題請自行解決。

(海峽時報檔案照)
17:52 -【印太經濟框架】
哈斯:我們有注意到這一點。您剛才也提到了印太經濟框架。我有兩個相關問題:您認為這個框架應該扮演怎麼樣的角色?當局已闡明該框架的概念,但還未具體說明其細節。印太經濟框架能在多大程度上,作為美國參與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CPTPP)的替代方案?這框架是否會被視為替代品,或充其量只是個不很理想的次佳選擇?印太經濟框架能或將發揮什麼作用?
李顯龍:印太經濟框架應該為美國同亞太地區國家的經濟合作定下正面的議程,一個包容和具前瞻性,並能給雙方帶來好處的議程。最理想的情況是,我們同時也擁有跨太平洋夥伴關係協定(TPP),但那已是付諸東流。
哈斯:(美國政府前貿易代表卡拉·希爾斯正在搖頭。)
李顯龍:付諸東流。TPP已變成CPTPP(《跨太平洋夥伴全面進展協定》),意味著美國沒有參與其中。如今,中國已申請加入,美國打算怎麼做?身為CPTPP成員國的我們又應該怎麼做?我們必須就如何處理這項申請達成一些共識。順道一提,台灣也提出了申請。美國如果要表明它們參與本區域的事務,又會如何回應呢?
在理想的情況下,美國可以採取貿易自由化的市場准入方式,與一個無法重新加入的地區建立聯繫,也可以採取其他方式。但我認為,在目前的政治氣氛下,即使要採取其他方式也太難了,所以美國提出了印太經濟框架。
印太經濟框架並不涵蓋所有美國需要做的事項,但如果能完成這些事項,會帶來積極成果。我想說的是,美國可以儘量將印太經濟框架變得更具實質性,因此在缺乏自由貿易協定的元素和市場准入的情況下,至少可以考慮納入一些數碼經濟合作或綠色可持續經濟合作的元素。
我們可以朝市場准入和貿易自由化小步前進。除了需要國會通過的貿易促進授權(TPA),或需要批准一些法案之外,美國可以開始行動,也許在美國未來的幾次選舉中,整體情緒改變會使之變得更可行,那就會有一條前進的道路。在這期間,政治是一種化不可能為可能的藝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