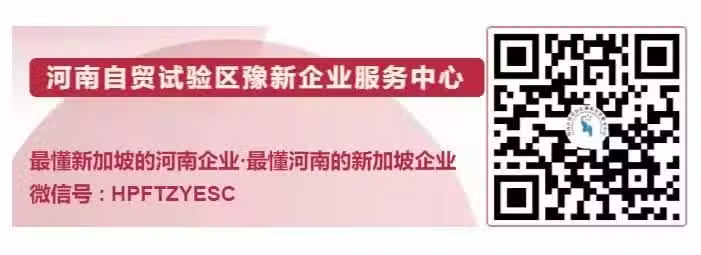新加坡,馬來半島最南端的彈丸之地,卻是世界上絕無僅有的「花園城市」。作為全球人口密度排名第二高的國家,新加坡人口密度高達7796人/平方公里,是北京的6倍,與「宇宙中心五道口」所在的海淀區基本持平。
北京「首堵」的故事想必國人都耳熟能詳,而只有北京市總面積4.4%的新加坡卻沒有這種大城市的通病。它是如何做到的?這一切都要從一位叫做劉太格的城市規劃師講起……

出身書香門第,從小書畫兼修。在澳大利亞新南威爾斯大學建築專業完成本科階段學習後,立即前往美國耶魯大學攻讀城市規劃碩士。畢業後順利進入紐約的貝聿銘事務所,正式開啟規劃師之路。1969年,劉太格學成歸來返回新加坡。他受建屋發展局(HDB)局長的邀請協助建國,在建屋局成立研究小組,負責政府組屋的整體規劃。
劉太格第一個影響新加坡的重要決策,就是將西方「衛星鎮」的設計理念引入組屋,為其規劃完整的社區場景。他設定了一套新加坡標準,將總人口拆分成100萬-150萬的中等團體。每個百萬人口的片區,都由若干個25-30萬人規模的衛星鎮組成。

獅城DNA | 新加坡如何做到「居者有其屋」一文中我們曾介紹過,在新加坡,社區商業中心、電影院、圖書館、養老院、醫療診所、體育場館、食閣、辦公樓、學校、交通樞紐等公共設施與組屋比鄰而建。居民無需走遠,5-10分鐘的步行範圍內可解決各種生活需求。
這樣功能高度齊全的組屋「衛星鎮」,使居民生活最大程度的實現了本地化。在自成一體、合理分布的同時,避免不必要的遠程移動,大大降低了中心地帶和特定區域的壓力。

隨著衛星鎮生態的建立,劉太格將開發思路逐步提升到整體規劃的高度,藉此重構城市。1979年,劉太格上任新加坡建屋發展局局長。10年後,新加坡規劃部與國家發展部的研究數據中心合併,組成新加坡城市重建局,劉太格被任命為局長兼總規劃師。
劉太格倡導每個城市都應做一個長期的、整體性的規劃。他常用火雞和大鵬鳥做比喻:「如果一個城市,50年後會長成一隻大鵬鳥,應該提早把整個大鵬鳥畫出來,讓它慢慢長大。如果只做短期規劃,相當於畫了50隻火雞,綜合起來像,卻並不是真的大鵬鳥。」
因此,1991年劉太格就為新加坡制定了100年的城市發展規劃。這樣一來,整體規劃不需要大幅度更改,只需配合短期動態調整。大方向敲定後,基礎設施隨之配套建設,在參考過分級的規劃後可避免亂投資現象發生。

人口、密度和規模,是城市規劃前期的三件要事。首先預測人口,再根據城市定位選擇適宜的人口密度,二者相除得出大致城市規模。扣除生態紅線後,就是城市開發的邊界。
劉太格多次公開強調要重視人口預測。他用「碗與飯」來形容城市和人的關係:飯少了就多添菜,好比實際人口低於預測值,可以利用多出的空間安排設施;若是飯多了滿出碗來(人口過多),就會引發擁堵、環境污染等「城市病」,社會問題也會隨之而來。

新加坡土地資源十分有限,劉太格在規劃高密度建築時,以西洋棋棋盤的設計作為參考。黑色格子代表高密度的住宅或寫字樓,白色格子代表公園、廣場及商業中心。以棋盤黑白相間為原則,這樣規劃的城市景觀不會顯得壓抑和密集。鋼筋水泥的建築錯落有致,公園廣場成為點綴。人們穿行其中,綠地與天空交相呼應。
對於人們把他稱作「規劃之父」,劉太格覺得有些言之過甚。他謙虛地表示,新加坡在城市建設方面之所以取得成功,最重要的是因為有領導人的遠見及注重遠期規劃。的確,李光耀在其中功不可沒。城市規劃需要合理化的領導決策,講究大系統引導小系統,做到多規合一,這幾點缺一不可。

現任新加坡宜居城市中心諮詢委員會主席的劉太格,近些年也將他的城市規劃理念帶到中國。他先後受聘成為山東省、北京市、天津市、雲南省等多個省市的規劃顧問,參與了我國40多個城市的規劃和設計,並在福州、廣州、重慶、珠海、桂林等地留有得意之作。2008年,他還應邀擔任北京奧林匹克公園規劃設計方案評審委員會主席。
在往返於中國和新加坡的十餘年間,劉太格已然了解中國在城建方面的弱點和痛點。值得欣慰的是,中國政府在過去幾十年的發展中也意識到了問題,且有意願改善,劉太格表示這「原則上是好事」。但他也指出,在中國城市化進程越來越快的背景下,規劃一定要防止「千城一面」的情況出現。

「要尊重軟環境,即自然山水;要保護古蹟;要尊重各地居民以及地貌特點」,是劉太格提出的保留城市特色的建議。他認為在規劃前要處理好人與環境的關係,不要為了所謂的城市改造去犧牲居民的幸福感。正如他在規劃新加坡的過程中對文物和老房子的保護,這些具有歷史沉澱的建築展示了新加坡的歷史和進步,為城市增添了鮮明的特色。
當談到新加坡和中國城市規劃的不同,劉太格用做飯來形容:「中國城市規劃像是西餐式做法,一堆馬鈴薯、一堆菜、一堆肉,提倡的是功能分區。我的做法是炒飯,馬鈴薯、菜和肉都切小,我把新加坡炒成一碟飯,一個綜合性功能的環境。」孰高孰下,不做過多評判,人在城市中的生活質量能真正說明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