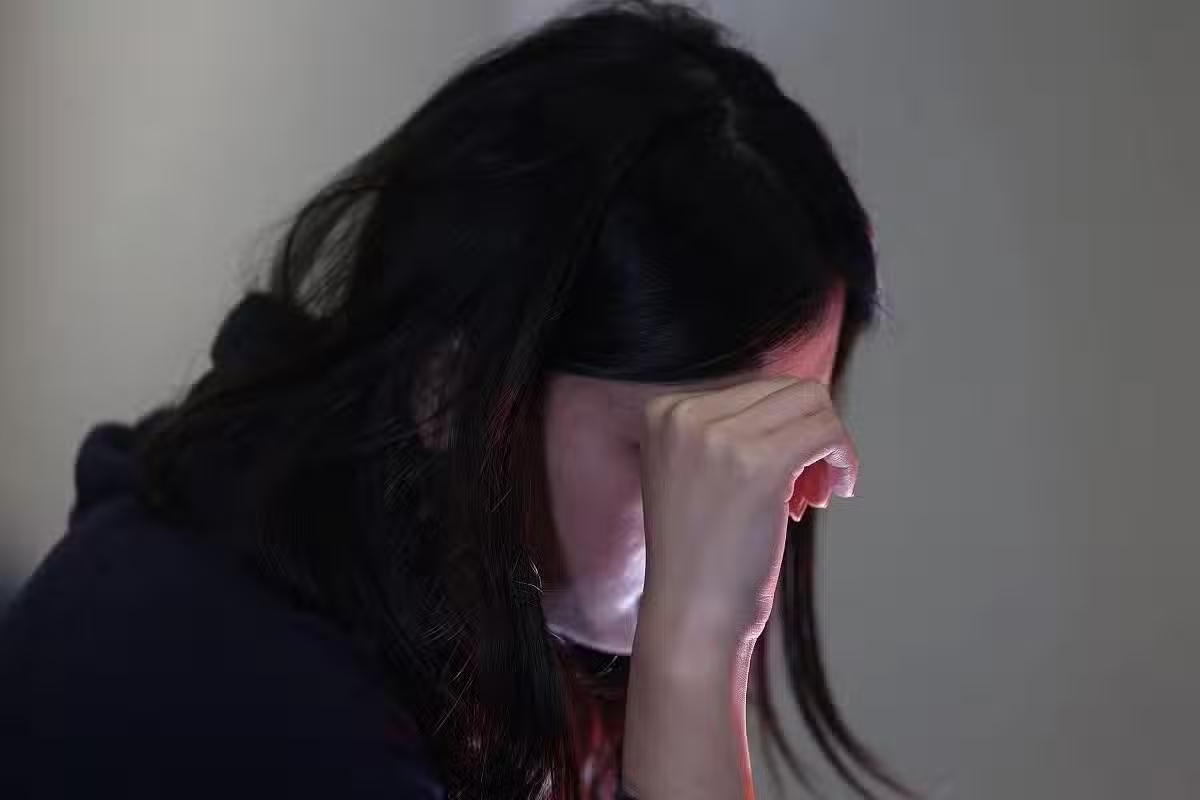
自殺一向是禁忌議題,甚至被視為羞恥的事。
由於不常被討論,缺乏公眾教育,不少人對自殺預防存有誤解,害怕和有輕生傾向者談自殺。
新加坡管理大學的一項最新調查顯示:
每10人中就有8人錯誤認為,當和有輕生傾向者談論自殺時,這個人可能就會輕生;
56%受訪者錯誤地認為,大多數自殺是突然發生的,沒有任何預警(相較於2022年只有53%這麼認為);
31%的人錯誤以為,自殺的人不願意尋求幫助(相較於2022年只有27%這麼認為)。
新大經濟學院統計學首席講師鄭如美今年1月至3月,帶領140名新大學生與新加坡援人機構(Samaritans of Singapore,簡稱SOS)合作,通過面對面、電話和視訊訪談,對5274名本地民眾進行調查。其中,3237名受訪者身邊有直系親屬、朋友、親戚或同事等,曾試圖自殺或因自殺身亡。
這項名為「Save.Me.Too」(意為「也救救我」)的調查首次於2022年進行,今年是第二次。
令紅螞蟻吃驚的是,社會各界花了不少人力物力去教育公眾關於自殺的課題,對輕生存有誤解的公眾卻不但沒有減少,反而略增。
這項調查是在新加坡援人機構2023年報道自殺人數創歷史新高之後進行的。2022年,本地共有476人自殺身亡,較2021年的378人增加超過兩成半。這也是自2000年開始記錄以來,自殺死亡人數最高的一年。
這個數據有點震撼,普羅大眾對自殺話題有如此多誤解,有輕生傾向的人若向我們求救時,我們又如何給予正確的幫助呢?
鄭如美轉述新加坡援人機構接聽有自殺傾向者求助熱線時,問對方是否想輕生。
她說,
「他們不會拐彎抹角。當他們有機會談論這個話題時,他們會感到放鬆和解脫,而不是迴避這個話題。」
多數人不願與他人談論自殺課題,以免讓他們感覺更糟

(ALAMY)
每10個受訪者中,就有8個認為新加坡存在自殺污名化的問題。鄭如美說,被邀請參與調查的人,如家長和年長者都比較排斥參加。
「有些人可能家裡發生過自殺的經歷,這個話題對他們來說太痛苦了。」
鄭如美說,對自殺話題的討論很少,是因為大家都害怕因討論這個課題而使情況惡化。鄭如美自己就因為同樣的原因,一度害怕進行這項研究。
但研究最終還是進行了,相信是因為研究員認為這種「少做少錯,不做不錯」的心態無濟於事。
這點和媒體工作者處理自殺相關新聞的態度不謀而合。
紅螞蟻剛加入媒體行業時,在晚間報紙當意外記者,當時前輩都告訴我們行內的這條不明文規定:
不要連續幾天報道關於自殺的新聞,也不能詳細地報道自殺的方法和經過,以免有人模仿。
大家最常舉的典型例子是2003年4月1日,香港藝人張國榮跳樓自殺後,媒體的報道連篇累牘、大肆渲染,結果,從當天深夜到第2天凌晨的9小時內,全香港有6名男女跳樓自殺,當月香港共有131起自殺身亡個案,較前月增加32%。
有幾名死者還留下遺書,清楚寫明其自殺與張國榮輕生有關。
那麼是否就不應該報道自殺呢?就算媒體不報道,在人手一機的現代社會裡,還有網絡記者和社媒傳播消息。
應該做的是在報道時避免美化自殺或簡化死因,關注自殺現象,適度報道來引起各界關注,讓心理學、社會學等方面的專家學者深入分析,找出事件的起因、處理及防範的方法,避免發生更多悲劇。
抗拒幫忙有自殺傾向的人

(ALAMY)
調查也發現,大約三分之一的人,會幫助有自殺傾向者。至於其餘三分之二的人,其中大約七成認為自己無能為力、缺乏相關知識,或擔心自己讓有輕生念頭的人感覺更糟,而抗拒提供幫助。這與2022年的情況沒什麼不同。
其他重要發現還包括:人們對自殺的恥辱感依然存在、教育水平對自殺知識了解沒有影響,以及不同年齡組對自殺的看法存在差異等。
根據調查,2024年的總體「自殺污名指數」(Suicide Stigma Index)為50.20,比2022年的49.98略微上揚。數值越高,意味著受訪者越不願意與他人談論自殺課題或尋求幫助。
調查也顯示,一個人年紀越大,他就越不相信自殺是可以預測的。在21歲以下的受訪者中,超過70%的人認為自殺是可以預測的,而在80多歲的受訪者中,只有43%的人持同樣觀點。

(ALAMY)
新加坡援人機構(SOS)總裁陳弼良告訴《海峽時報》,有必要讓更多人通過SOS等機構開展的自殺預防培訓,學習如何識別一個人掙扎痛苦的跡象。
對自殺話題避而不談、了解不多的人,主要原因是沒有親身經歷過身邊有人輕生。
但是,有直系親屬或親戚試圖自殺或死於自殺的人也說,這方面的知識推廣或教育並不足夠。這個群體也是認為談論自殺可能會讓人有輕生念頭的人當中,比例最高的群體。
鄭如美指出,這表明人們對一個人有輕生念頭缺乏理解,即使是那些有親人面對著同類問題的人。「自殺會留下很多沒有答案,且可能永遠無法解答的問題,也會導致一輩子的困惑、悲傷、憤怒和內疚。」
私人心理健康業者Talk Your Heart Out(意為「說出你的心聲」,簡稱TYHO)聯合創辦人和首席長官阿加瓦(Chirag Agarwal)說,
想要談論自己有自殺想法的人,害怕受到評判或歧視;而想要與幫助有輕生念頭的人,則擔心會讓事情變得更糟,或者不曉得如何以正確的語言展開對話。
「要學習如何傾聽,同情他們的處境和精神狀態,給予對方傾訴的空間,需要好些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