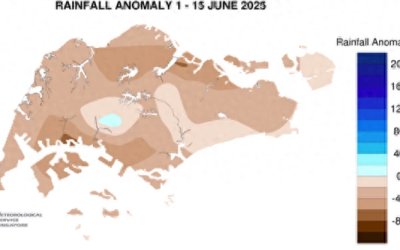直落布蘭雅組屋區的特色是以山為中心
南部山脊全長10公里,登高望遠,南部島嶼盡入眼帘。其中花柏山曾經被列為本地名勝,吸引不少外國觀光客前來打卡。上世紀60年代的本地電影《獅子城》,以及謝賢、南虹年代的港產粵語片,都少不了花柏山的精彩畫面。昔日出國遊玩尚屬夢想的年代,一家子到花柏山上留影,已成為多年以後珍貴的回憶。
花柏山原名直落布蘭雅山(Tulloh Blangan Hills)。「直落布蘭雅」(Telok Blangah)的詞源有不同的說法,馬來語直譯為土鍋灣,可能根據地形來命名。「Blangah」也指休息站,這裡像個避風港,讓從馬來群島隨著季候風來到本地的商船停泊。
19世紀中葉,殖民地政府在山上設置航海通訊旗杆,由工程師Captain Charles Edward Faber率領一群印度罪犯勞工,沿著山腳的天猛公村落開闢上山的小路,完工後花柏山以工程師的名字命名。同一時期,阿卡夫從葉門來到本地,經營白糖、咖啡與香料貿易。20世紀初,整個家族擁有包括山頂別墅在內的近百個房地產。二戰改變了許多人的命運,阿卡夫家族從此元氣大衰。
直落布蘭雅山
直落布蘭雅組屋區於半個世紀前全力發展,跟紅山的五個分區聯合組成5萬多個單位,15萬居民入住的新鎮。這是繼女皇鎮和大巴窯之後的第三個新鎮,特色是以山為中心。亨德申路將兩座山峰一分為二,花柏山的名字保留下來,阿卡夫別墅坐落的華盛頓山頭則易名為直落布蘭雅山。
早晨的直落布蘭雅山人氣旺盛,喜好太極拳和武術的人士濟濟一堂,音樂聲此起彼落。半個世紀前的華盛頓山頭同樣靈氣十足,千佛寺大雄寶殿裝上霓虹燈,絢麗的光芒照亮星空;阿卡夫山莊(Alkaff Mansion)則成為世界佛教社,在山上開辦佛教大學。獨立後不久的新加坡雄心勃勃,於1973年承辦東南亞半島運動會(東南亞運動會的前身),聖火在山上點燃後,由接力隊傳送火炬,奔向甫落成的國家體育場。本地運動員發揮歷年來最佳的戰鬥力,實現賽會亞軍的夢想。千禧年到來前,山莊發展為高檔西餐館,保留昔日富豪的霸氣。

1973年,獨立後的新加坡初次承辦東南亞半島運動會(東南亞運動會的前身),在直落布蘭雅山頂點燃聖火(圖源: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阿卡夫山莊(Alkaff Mansion)浮生多變,現在是一家西餐館
花柏山麓的天猛公村莊
兩百年前萊佛士規劃土地時,將新加坡河口兩岸歸納為行政與商業區,在河畔生活的天猛公阿都拉曼被安置到花柏山下。阿都拉曼的兒子伊布拉欣(Daeng Ibrahim)、孫子阿布巴卡(Abu bakar)都受到殖民地政府的器重,後來成為柔佛皇室。
各個時期都會出現新的傳染病,就如近年來冒起的流感、沙斯和冠狀病毒。根據1848年《新加坡自由報》的報道,在那個人們相信土方,對西醫避之則吉的年代,伊布拉欣已經強制所有直落布蘭雅村民接種天花疫苗。
花柏山麓有一所白牆綠瓦的天猛公回教堂(Temenggong Daeng Ibrahim Mosque),教堂的所在地就是天猛公接待賓客的大廳,墓園所埋葬的都是皇室家屬。

花柏山麓白牆綠瓦的天猛公回教堂(Temenggong Daeng Ibrahim Mosque)
拉丁馬士的愛情故事
花柏山麓還有個拉丁馬士(Radin Mas)馬來甘榜,重建後成為武吉寶美(Bukit Purmei)住宅區,半山腰則保留著拉丁馬士(黃金公主)的聖墓。馬來傳說中,來自爪哇的黃金公主年幼時由逃難的父親帶到本地。公主長大後被王子看上,誰知進行婚禮時,父親遭敵人飛鏢暗算,公主撲身相救,最後在王子的懷抱中死去。
林恩河根據19世紀的報章、村長與回教士的口述歷史來還原現實:印尼姑娘拉丁馬士嫁給荷蘭籍丈夫,跟著夫婿來到新加坡,由天猛公的後人包養為情婦。由於拉丁馬士身份特殊,死後進不了皇室墓園,只好埋葬在半山腰。兩個不同的版本,您會作何選擇呢?
使用煤炭發電的聖占姆士發電廠
天猛公回教堂對面的紅磚百年建築,就是前聖占姆士發電廠的所在地了,這是新加坡第一座發電廠,也是唯一使用煤炭發電的電力廠。發電廠建在海邊的沼澤地上,最大的好處是取之不絕的海水可用作發電機的冷卻用途。此外,這裡靠海、靠火車站,能直接獲得煤炭建材等原料供應。
煤炭發電的年代,停電是司空見慣的,最長的記錄為八個半小時(1948年)。那個雪櫃尚未流行的年代,富裕家庭投訴冰淇淋融化了,總損失約數千元。當時新加坡專業劇場正在維多利亞紀念堂演出,劇組情急之下安排汽車停在劇場門口,利用大鏡子將車頭燈光反射到舞台上。這臨場發揮的創意,讓戲得以繼續演下去。
西北門的黑頭巾
天猛公的年代,英國人已經著手發展岌巴碼頭,來往東西方的客貨輪在此處停泊。日後,岌巴碼頭和岌巴船廠組成海運價值鏈,輪船卸貨後順便入廠維修。由於船隻從本島的拉柏多公園與聖淘沙島之間西北面的水道進出,在海員眼中就像一扇門,華人乾脆將直落布蘭雅沿海地區統稱為西北門。

西北門的岌巴船廠,綠色的島嶼為聖淘沙(圖源:Abdul Razak)
建國的年代,祖籍廣東四邑和東莞地區的「黑頭巾」婦女曾經在船廠貢獻她們的青春。這群婦女居住在牛車水、丹戎巴葛及艾佛頓園一帶,每天早上手挽著流行的竹籃,裡頭裝著乾淨的衣服、飯格和食水,蹲在街邊等候。若工頭包到工程,就用羅厘載她們入塢開工。黑頭巾主要窩在船艙底清理油污,俗稱「洗廊西」。她們蹲在六七層樓底下悶不透風,不見天日的船艙工作,趕工的時候甚至會連熬幾個通宵。由於她們躲在見不到的角落,其堅韌不拔的精神鮮為人知。
船廠旁的書香園地
岌巴船廠旁的世界貿易中心(現新加坡遊輪中心)曾經是中文書愛好者的書香樂園。話說上世紀80年代中,中文報在報業中心的仁定巷舊址舉辦世界華文書展,後來規模越辦越大,改在場地寬敞的世界貿易中心展覽廳,集合華族文化節、書展與國際華文文藝營於一體,締造了華校消失後的輝煌期。

上世紀90年代,世界華文書展在世界貿易中心舉行,吸引許多中文書愛好者(圖源:新加坡國家檔案館)
當時本地30多歲以上的人士當中,有一半乃華校出身,中文圖書的潛在力量不容忽視。那些年我這個快樂的參與者,甚至特意安排工作行程,從世界貿易中心乘坐民間經營的小木船,前往對岸的布拉尼島(Pulau Brani)海軍基地,回程時挪些時間在圖書天地中遨遊。
島嶼的傳奇故事
從前海人跟著天猛公搬家,遷徙至布拉尼島落戶。1967年新加坡成立海軍部隊,先後在直落亞逸灣(Telok Ayer Basin)與絕後島(聖淘沙)設立臨時海軍總部。1974年底布拉尼島海軍基地落成,現代化的新加坡共和國海軍正式啟航。

布拉尼島未興建海軍基地和箱運碼頭前,是馬來人傍海而居的村落
海軍基地啟用幾個月後,附近的毛廣島發生「拉裕事件」(Laju incident)。日本赤軍和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陣線的四名恐怖分子襲擊毛廣島的煉油廠,引爆炸彈後劫持拉裕號駁船。海軍出動新啟用的炮艦,和水警聯手包圍恐怖分子。經過七天談判後,恐怖分子釋放人質,乘坐日航專機前往科威特,隨行的「擔保人」包括時任保安與情報司司長納丹。20多年後,納丹成為新加坡共和國總統。
跟恐怖分子對峙不久後,海軍炮艦投入雷暴行動(Operation Thunderstorm)。那時候每個月數百艘越南難民船路過新加坡,有些船民隨身帶著槍械和手榴彈,有些故意放火燒船,強迫新加坡政府讓他們上岸。由於過境的人數太多了,海軍所能做的是解除船民的武裝,供應物資,修理船隻和引擎,甚至教導船民駕船的技術,讓他們繼續行程。
樟宜海軍基地落成後,布拉尼島由港務局接管。關於那段愛艦、愛島、愛海洋的時光,我最深刻的記憶就是坐在小島岸邊,邊看著夕陽,邊跟老軍人和年輕工程師聊天。兩百米外的聖淘沙高爾夫球場,也能映入眼帘。那就是日據大檢證時期,集體屠殺民眾的殺人場。
絕後島華麗轉身為聖淘沙是個「一念之差」的決定。1960年代末,美國埃克森石油公司同意經濟發展局的條件,在絕後島建設煉油廠。另一方面,吳慶瑞接受經濟顧問Dr Albert Winsemius的看法,認為本地需要一個大型的消閒活動兼旅遊中心,絕後島是最合適的地點。重新談判後,埃克森最終答應將煉油廠設在西部島嶼(現在裕廊島的一部分)。半個世紀前一個臨時更換的決策,使得新加坡出現聖淘沙這個旅遊地標,以及由多個小島填土合成的裕廊島石油化工中心。
七姐誕與中元會
西北門地區最大的僱主就是岌巴船廠了。船廠員工多數是廣東人,跟家人居住在員工宿舍(現聲音停車場一帶)。農曆七月,船廠員工主辦盛大的七姐會與中元會,慶祝活動於七月初四便開始了。由於船廠的財力雄厚,還會搭起戲棚,聘請戲班連演四、五天日場和夜場的大戲。上世紀70年代在西北門出現的粵劇藝人包括香港的鳳凰女、羅家英、林錦堂、林少芬、尹飛燕、阮兆輝、梁漢威等,同台的新馬演員則主要是邵震寰。
戴愷倫的姑丈在船廠工作,西北門演大戲的時候,乾脆將睡床拆了,搬到戲棚前讓一家子坐在床上看戲。耳濡目染下,年幼的戴愷倫喜歡上粵劇,長大後在直落布蘭雅組織自己的家庭,沒上班的時候便到住家附近的戲棚看街戲。戴愷倫最喜歡經典名曲《帝女花》,但在台上唱《帝女花》的壓力很大,表現失常的時候,台下觀眾就會接口唱下去。
歐陽炳文從小就跟著大姐,乘坐巴士到處看街戲,即使遇上測驗考試也不例外。大姐參加會館的粵劇班學唱戲,他在一旁覺得花旦的化妝很漂亮,從此喜歡上扮演花旦的角色。歐陽炳文擅長唱紅(線女)腔,對粵劇的喜好持續至今。
請得起大老倌的戲班,正戲開鑼前都唱一段例戲來展示班底的實力。《六國大封相》乃最常演的開台劇目,其他有《仙姬大送子》《八仙賀壽》等。且聽:「門外雪山頂寶,金盆滿放羊羔。天邊一朵瑞雲飄,海外百仙齊到。先敬丹沙一粒,後敬王母仙桃。彭祖八百壽年高,永祝長春不老。」雖然西北門已四十多年不唱戲了,但見港灣瑞雲飄遊,繼續演繹著長春不老的傳奇。
參考文獻
[1] Michael Yong, 7 things you probably didn』t know about Telok Blangah: Pirates, kings, and a healing spring, CNA, 20 Jul 2019.
[2] The Singapore Free Press and Mercantile Advertiser, 12 April 1849, Page 2.
[3] Victor R Savage, Brenda S A Yeoh, Singapore street names: a study of toponymics. Singapore: Marshall Cavendish Editions, 2013.
[4] 戴愷倫口述記憶,2020年3月27日。
[5] 李國梁,《大眼雞 越洋人》水木出版社,2017年11月。
[6] 林恩河,《美麗的傳說與冷酷的現實 拉丁馬士的故事》,《聯合早報》2019年5月30日。
[7] 林志強,《阿卡夫山莊之塵封軼事》,《塵封軼事 從武吉布朗追溯新華兩百年》2020年2月。
[8] 歐陽炳文口述記憶,2020年12月13日。
(作者為英國皇家造船師學會會士、自由文史工作者)